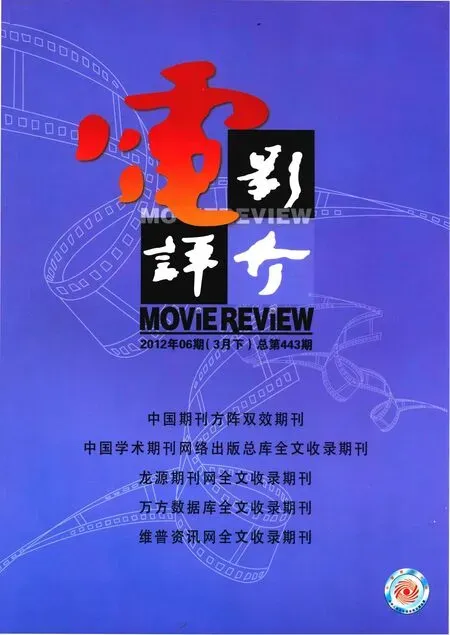冰冷之地與溫暖之花——論巖井俊二的映畫世界
巖井俊二是日本“新電影運動”的旗手,是日本年輕一代導演中的佼佼者。他秉承了日本“菊與刀”的民族性格,以影像清新獨特,感情細膩豐富著稱于世。從怪誕新奇的《愛的捆綁》開始,無論是細膩委婉的《情書》《四月物語》《花與愛麗絲》,還是晦暗深刻的《夢旅人》《燕尾蝶》《關于莉莉周的一切》,巖井俊二都“將渲染情緒、展示心理狀況豐富的想象和聯想、快速蒙太奇、象征隱喻的影像語言、虛幻與現買之間無痕跡的進出的手法等帶進了日本電影,使日本電影面貌煥然一新。”[1]
統觀巖井俊二的一系列作品,可以看出其獨特的個人風格:暢達明快如行云流水,宏大濃郁又詩意雋永。美好,則如溫暖之花;殘酷,則如冰冷之地。而其后蘊藏的則是他一以貫之的細膩唯美的日式特征。
一、美好或殘酷——巖井俊二作品的主題
巖井俊二最關心的是人最本質的東西。他用詩意的鏡頭語言和對情感的細膩把握,表達了他對青春與成長中美好和殘酷的獨特感受以及對生死、記憶及現代都市異化生活的個人化體悟,譜寫出一部部動人詩篇。
(一)青春與成長
提起巖井俊二,大多數人會將他與“青春”相聯系,甚至贊譽他為“歌詠青春的映像詩人”,把其作品稱為“青春片”。 戴錦華教授曾指出,“所謂‘青春片’的基本特征,在于表達了青春的痛苦和其中諸多的尷尬和匱乏、挫敗和傷痛。可以說是對‘無限美好的青春’的神話的顛覆。‘青春片’的主旨,是‘青春殘酷物語’,近似于意大利作家莫里亞克的表述,‘你以為年輕是好事么?青春如同化凍中的沼澤。’”[2]的確,“青春與成長”是巖井俊二作品中不可回避的主題之一。《煙花》中少年的萌動與懵懂,《夢旅人》中年少生命的纖弱,《情書》中青春戀情的蔓延追憶,《燕尾蝶》中青春夢想的破滅,《四月物語》中少女單純浪漫的暗戀,《關于莉莉周的一切》中成長的痛苦與孤獨,還有《花與愛麗絲》中青春的甜蜜或憂傷,青春和成長過程中唯美的詩意、瑣碎的憂愁,以及痛苦和無助,都在巖井俊二的作品中得到淋漓盡致的細膩描繪。
正如村上春樹在《海邊的卡夫卡?序言》中所說,“我們領教了世界是何等兇頑,同時又得知世界也可以變得溫存和美好。”在巖井俊二營造的如詩如夢的意境中,或溫馨,或冷峻,都脫不開對青春期少男少女心理的微妙探詢,讓我們看到真正意義上的青春與成長。
首先,青春期作為人生中最美好的時光,有著唯美和浪漫,有著青檸一般淡淡的芳香。《情書》通過精巧的敘事為人們編織了一段浪漫唯美的初戀故事,把青春期少年的朦朧愛戀和青澀表白融入到清新柔美的視聽語言中,引起人們對青春與愛情的深切感懷;《花與愛麗絲》則是通過朦朧的光影,輕靈的舞姿和優美的舞曲,把少女內心深處最細微、最隱秘的情思,以視覺的形式呈現出來,使影片具有輕靈跳躍的青春氣息和現代感。就青春的美好而言,巖井俊二清新唯美的獨特風格是極具個人氣質的,既不同于歐洲青春片的藝術化——如《天使愛美麗》《天堂電影院》等將青春和成長的思考融于對人性的深度追問之中;也不同于好萊塢青春片的商業化——如《美國派》《歌舞青春》等以戲劇性和時尚感表現青春和成長的明快浪漫。
其次,青春期作為少年向成年的涅槃,必定要經歷迷茫和痛苦,有其殘酷的一面。《夢旅人》中處在自由邊緣的那三個精神異常的孩子,一個莫名其妙地從墻上跌落而死,一個為替朋友贖罪親手開槍結束了自己年輕的生命;《關于莉莉周的一切》更是構筑了一幅以“暴力、欺侮、憂郁、援交、沉迷虛擬世界”為主題的青春畫卷,揭示了成長中的虛幻、迷茫和殘酷的一面。就青春的極端而言,巖井俊二的“青春殘酷物語”也有其獨到之處。相對于日本傳統的青春片(如大島渚《青春殘酷物語》等),其作品更加令我們觸目驚心,因為傳統的主人公常常是毀滅于社會上的黑惡勢力,而巖井俊二的作品已經深入到自我的沉淪,甚至沒有反抗和掙扎;相對于同時期世界其他各地的青春片(如楊德昌《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等),其作品因為“曖昧”的情節與影像處理而更具表現力,正如他自己所說,“楊德昌拍出了一半我想要的東西,另外一半,我自己想做”[3]。
總之,一方面巖井俊二致力于青春和成長過程中美好的情感幻影制造,另一方面他的青春電影也沒有忽略殘酷的現實存在。這里有青少年正在經歷的殘酷歷練,也有成年人對于青春時代的美好回憶,有美好青春的信仰,也有對于這種信仰丟失的抱憾,兩種情感看似矛盾卻又相輔相成地還原了青春的真相。堅持從不同的角度看待青春,這正是巖井俊二電影的獨特風格,真實的青春在他的電影中得到完整的記錄和展現。
(二)生死記憶與現代憂思
生與死始終是一個充滿形而上的哲理意味的命題。巖井俊二曾說:“人總是要死的,該為了死做準備,而現在的日本,根本沒有死的概念,沒有人想這件事,好像死是一件非常不好的事。”[4]他的作品中不乏對于生死的探尋,直白殘酷抑或是含蓄詩意。
《夢旅人》可謂最為直白殘酷的:三個精神異常的孩子將《圣經》印刷日期看作是地球毀滅之日,本就是絕望的表現,而一個從墻上跌落而死,一個把子彈射向自己,一個把子彈射向太陽,則將死亡赤裸地呈現在觀眾面前;《關于莉莉周的一切》少女以飛翔的姿態奔向死亡,少年的刺殺則將對生命的擁有變成奢望。而《情書》則在其淡泊的愛情敘事下,若隱若現的呈現出對于生與死的思考。藤井樹在其父親葬禮結束后看到的冰面上凍死的蜻蜓更是生命的脆弱和死亡的物化,與其父的去世產生詩意而神秘的聯系。《燕尾蝶》中,死亡和毀滅的哀婉,在激情迸發、追逐夢想的奔跑中始終沉緩的流淌,使生和死的主題以一種舒緩的情緒呈現出來,最后達到和諧的詩意境地,正如影片的臺詞所說,“天堂是存在的,當人死去的時候,靈魂飛向天空,在碰到云彩的那一瞬間,就會化成雨點落下來。”死亡造成了永恒的失去,遺留下來的只是無盡的懷念與記憶。尋求生命永恒的唯一辦法便是將生命封存,留待以后的日子慢慢回憶,深深緬懷。
巖井俊二在談其創作時曾說:“我邊回憶自己的中學時代,邊為如何造成一種空氣感,把什么樣的回憶找出來而深深地苦思冥想。”[5]因此,在他的鏡頭下,“記憶的埋葬與鉤沉”顯現出獨特的詩意魅力。《情書》中博子對藤井樹的記憶是缺失的,所以她只有通過女藤井樹的回憶來填補自己記憶的空缺。而就在這種回憶中,卻展開了男藤井樹對女藤井樹的暗戀情節。影片的真正動人之處正在于此,一個人的記憶成為兩個人的回憶,當博子將所有的信還給女藤井樹時,她知道記憶只屬于那些經歷過它的人,而別人分享的只能是回憶。《花與愛麗絲》中,宮本尋找著自己“遺失的記憶”,花與愛麗絲卻編造著越來越多的謊言,漸漸地成了一個自己也拔不出來的美麗記憶,雖然謊言最終被揭穿,青澀的愛情卻就此萌發,這段時光本身也成為了三個令人最美好的記憶。
巖井俊二并沒有止步于對于青春、情感等的描摹,他還具有卓爾不群的社會意識。對現代社會懷有一種深沉的憂思。他認為在現代社會中,緊張的生活已經讓人們逐漸喪失許多寶貴的東西,而人與人之間日益的隔膜造成了人性的毀滅。[6]正如他在《燕尾蝶》導演自述中表示“以寫外國人來寫日本人,寫對日本人精神世界的關注”,“不斷透視帶有成長中弊病的日本的未來”。
《愛的捆綁》中怕失去愛情而瘋狂的萌寶,《夢旅人》中無法與人相處而走向毀滅的可可,《燕尾蝶》中為金錢喪失一切的“元盜”們,他們的悲劇都是畸形的社會所造成的。其早期的電視短片作品如《雪之王》等,則討論的更是些社會化的問題,與季耶夫斯洛夫斯基的《十誡》有幾分相像,力圖為我們展示出在物質社會下人們蒼白羸弱的生命和心靈,人們心底最隱秘的孤獨與憂傷,人們為潛藏的危險感到的恐懼與不安。
二、和風物語——唯美的日式特征
電影藝術有著強烈的民族風格和民族特色,每個民族都有著不同于其他民族的審美特質。日本是一個有著悠久抒情審美特征的民族。“在島國的自然風土的熏陶之下,日本人形成特殊的文化性格和精神結構,培育出崇尚悲哀,幽玄,風雅的氣質,進而成為醞釀日本藝術精神的底流,產生了相應的獨特的日本藝術美的形態。”[7]巖井俊二很好的繼承了日本的美學傳統,而且加入多種新式拍攝手法,用包括畫面、音樂在內的多種細膩至極的形式,營造了物我合一的東方式意境。
(一)細膩至極的形式
作為一名油畫專業出身,又具有多年拍攝MTV、廣告和電視節目經驗的導演,巖井俊二精通各種藝術形式。他的影片在色調等方面都十分出色,加之優美的配樂穿插其中,更產生了一種唯美精致的特質。
首先,畫面是電影的第一要素,巖井俊二電影畫面的色彩構成極具匠心。巖井俊二鐘愛的顏色不止一種,這些顏色被他用于為自己影片的主題上色,這些主題或者是青春,或者是生死,或者是冷冰冰的現實。《情書》中皚皚的白雪、飄動的白床單等所呈現的白色,象征著純潔、高雅和堅貞;《夢旅人》中的橙黃色,以其特有的質感博得了少年們的喜愛,只有那橙色的陽光成了我們唯一忠實的青春目擊者;《燕尾蝶》中灰色無處不在,卻又找不到它的蹤影;《四月物語》中雨中紅傘的紅色,以點取勝,濃郁的紅色奇妙地講述了一段淡如水般的暗戀;《關于莉莉周的一切》中的綠色,用來詮釋青春的無與倫比,是希望和活力的主題色;《花與愛麗絲》中室內的暖黃色和室外藍綠色,跟隨著情緒的起伏將所有關于愛、暗戀、青春和希望都匯聚在一起。
其次,音樂能為影片的整體或局部創造一種特定的氣氛基調,從而深化視覺效果,增加畫面感染力。巖井俊二的作品中音響效果是構成銀幕信息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情書》中的鋼琴,其浪漫和抒情的音質與整個主題的風格非常一致,更成功運用了“電影音樂的最高境界——氣氛音樂”,出色地創造了一種輕柔、縹緲、朦朧的美感;《燕尾蝶》中為了營造整體氛圍,運用了各種主、客觀音樂,有表現動蕩不安的都市搖滾樂,有煥發著溫情的鄧麗君的抒情小曲,還有強烈理想主義色彩和悲劇感的音樂震撼人心;《關于莉莉周的一切》中音樂直接參與了敘事,人物和劇情都受到音樂的支配,“莉莉周”的音樂似乎成為少年艱難成長中的唯一救贖。
(二)東方式的意境營造
“日本電影中特別值得稱道的是它保留的那種含蓄、清淡、質樸、哀傷的東方的意境美,相對平穩的日本歷史,造就了一種特殊的日本美,她們強調在人的各種情感中只有苦悶、憂愁、悲哀才是使人感受最深的。這種日本美己經滲透到日本民族的心理素質中去,因而我們在日本電影中,也常常可以感受到人物情感的委婉含蓄,心理刻畫得纖細深刻,有一種清純而朦朧的藝術美感。”[8]巖井俊二深諳其道。他在其電影中運用詩化、唯美的鏡語和純真、傷感的影調,營造了一個追求物哀、幽玄的東方式意境,表達了一種含蓄綿長、哀而不悲、悲而不傷的感情,擁有一種別具特色的風雅之美,情調之美。
《情書》在回憶與現實的交織中,巧妙地利用了一個誤會,逐漸展開了一段被埋藏了許多年的戀情,通過女藤井樹對中學時光的回憶,抽絲剝繭般剝離出那份原來已經隨著男主人公的死而封存起來的愛情,含蓄而哀婉,刻畫了東方人特有的情感觀。《四月物語》中卯月對山崎的暗戀在雨中借傘的高潮段落中戛然而止,而沒有告訴我們結局。暗戀之美正在于有缺陷,不完整,巖井俊二正是抓住了這一點,將這種不完整擴大化。《花與愛麗絲》中宮本、花及愛麗絲三人之間微妙的情愫,《夢旅人》中可可與卷毛以及《燕尾蝶》中火飛鴻和固力果之間的愛情都因種種原因而錯過了,傳達出淡淡的哀感。
正所謂“情與景會,意與象通”,巖井俊二在其電影中還充分運用了意象化這種東方式的抒情方式。他將自然景物作為意象,將細膩的情感融入自然環境之中,同自然景物之美交融在一起,以一種自然的靈氣創造出一種特殊的氣氛,將人物的思想感情突現出來,形成情景交融的藝術境界。巖井俊二最常使用的是櫻花、白雪等傳統意象,將“瞬息之美”表現得淋漓盡致。《四月物語》和《花與愛麗絲》中洋洋灑灑的櫻花雨,將少女情懷的清瑩透澈表現得細膩入微;《情書》中運用的則是紛紛揚揚的大雪的意象,大雪借由導演的演繹成為來自天國的信使,寄托著生死兩端深深的思念與哀愁。
總之,巖井俊二將內心最細微曼妙的躍動,捕捉意化在視覺之上,營造了追求物哀、幽玄的東方式意境,猶如一幅清俊雋永的水墨畫,又如一首雅致悠遠的唐詩。這既不是空洞的視覺美也非是干癟的抒情,而是兩者交融的和諧美感。
三、結語
總之,巖井俊二用他細膩的手法和詩化的風格為我們證明了電影藝術的超越性和人文關懷在當今消費社會的存在。他“拒接豪言壯語,在最低限的思維中維護(而不是確立)自己的世界”[9]。他是一個既唯美婉約又詭異瘋狂的影像天才,又是一個永遠都游走于主流和另類之間的理想守望者。他對于如溫暖之花般唯美和冰冷之地般殘酷的沉穩把握,猶如銳利的刀鋒之上,菊花花瓣依舊清新不已。
注釋
[1]錢有玨:《走向21世紀的日本電影》,《電影評介》,2000年第6期。
[2]戴錦華:《電影批評》,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63頁。
[3]《日本導演巖井俊二訪談:我懷疑所有的 常 識》,2011-6-12,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20403163/
[4]尹樂:《巖井俊二青春題材電影的影像特質》,《藝苑》,2010年第4期。
[5]錢有玨:《20年代的日本電影四導演訪談》,《當代電影》1998年第3期。
[6]李亦彤:《徹底極端的巖井俊二》,《廣東藝術》,2002年第5期。
[7]葉渭渠、唐月梅:《日本人的美意識》,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73頁。
[8]岳淼:《影視傳播概論與技巧》,廈門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252-253頁。
[9](日)四方田犬彥著,王眾一譯:《日本電影100年》,三聯書店,2007年版,第26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