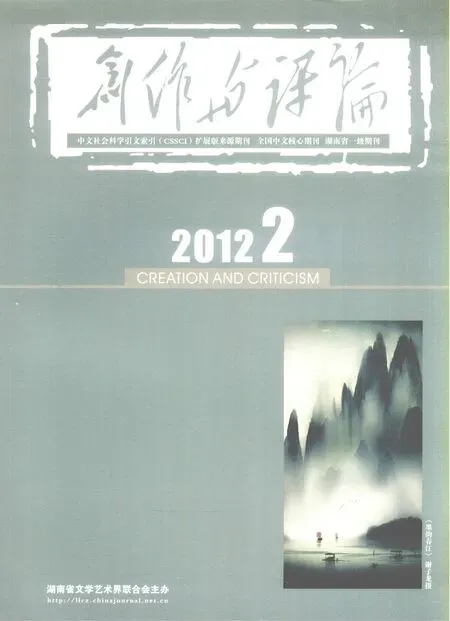失落的童年(紀(jì)實(shí)文學(xué))
■ 何頓
一 陳衛(wèi)平
前幾年開始了打羽毛球。一個(gè)星期兩場,有人邀,再加一場也是常有的事。羽毛球運(yùn)動(dòng)量很大,一場球下來不掉下半斤汗,至少也有二三兩。那汗里當(dāng)然有油,那油就是體內(nèi)的脂肪。假如你跟一個(gè)剛打完羽毛球的人坐在一起暢談未來,暢談了五分鐘后,你基本上想死,那氣味太重了,有點(diǎn)像從豬身上剔下的板油的氣味,讓與你談話的人不想接觸未來。也許是我的鼻子太敏感,屬狗的,八成就是個(gè)狗鼻子。這鼻子害得我時(shí)常懷疑這個(gè)懷疑那個(gè),有點(diǎn)像曹操,疑心重。玩笑話。但有一點(diǎn)是真的,每次我打完羽毛球,第一件事情就是洗澡,然后再干別的。很多人都是我這樣干的,估計(jì)都跟我一樣長著個(gè)嗅覺靈敏的鼻子。
記得有次打羽毛球,打出了小學(xué)同學(xué)。這話不合邏輯,但合情理。那天我和一個(gè)朋友上球館打球,打到半途上,有個(gè)女人走上來,笑著問:“請(qǐng)問你是不是叫何斌?”凡是有人問我叫何斌的,這個(gè)世界上都是我少年和青年時(shí)期的同學(xué)。那時(shí)候我還沒有何頓的筆名。我回答望著我笑瞇瞇的女人說,“我是何斌,你是——?”她要我猜,我盯她一眼,真的看不出她是誰,說我真想不起來。她說:“陳衛(wèi)平,你的小學(xué)同學(xué),我們以前住對(duì)門。”
關(guān)于這一點(diǎn),她說得一點(diǎn)不錯(cuò)。我們小時(shí)候都住在湖南第一師范。她父親是老師,我父親是校長,文革中我父親被打倒,她父親好像也出了點(diǎn)問題,于是都被趕到了一師四宿舍住,住成了對(duì)門。那不是一九六七年,就是一九六八年,反正當(dāng)時(shí)我們都很小。陳衛(wèi)平小時(shí)候蓄一根很粗的辮子,那辮子跟《紅燈記》里李鐵梅的辮子類似,相當(dāng)威猛,一甩,基本上可以把你的鼻子打出血,像馮作家寫的《神鞭》里的那根神鞭,好在那時(shí)候我離她遠(yuǎn),我的鼻子就沒被她的辮子抽出過血。那時(shí)候她愛穿一件紅色的燈芯絨衣,下身穿的是什么就不敢記得了。可能也不是她愛穿,八成家里就只給她做了那件,反正記憶中就是一件紅色的燈芯絨衣。陳衛(wèi)平笑瞇瞇地說:“不記得了?”關(guān)于她臉上的笑,我要說明兩句,那是成年女人臉上的笑,笑得熱情、友好、親切,像領(lǐng)導(dǎo)臉上的笑容。后來果然被我證實(shí),她是某局副局長,官不是很大,但仍是個(gè)官。當(dāng)了領(lǐng)導(dǎo)的人,是要準(zhǔn)備幾種笑容,不準(zhǔn)備那怎么像領(lǐng)導(dǎo)?假如我是領(lǐng)導(dǎo),我也會(huì)準(zhǔn)備幾種笑容,對(duì)于陳衛(wèi)平我也會(huì)像她那樣笑。這個(gè)成熟女人臉上的笑容與我少年時(shí)候認(rèn)識(shí)的小女孩出入很大,那個(gè)陳衛(wèi)平蓄著“神鞭”,這個(gè)陳衛(wèi)平剪著短發(fā);那個(gè)陳衛(wèi)平是個(gè)不愛說話的女孩子,這個(gè)陳衛(wèi)平笑得山花爛漫的,我怎么能對(duì)得上號(hào)呢?但是我不能說不記得,我說不記得那還是同學(xué)嗎?我說記得記得。她的笑容就變得更友好了!這是我需要的,如今是一個(gè)各人都為自己的利益打算盤的世界,笑容于是就變得很可貴。假如我當(dāng)時(shí)說我不記得,她的笑容就會(huì)凝固,一凝固就沒有后面的一大群小學(xué)同學(xué)見面了。
陳衛(wèi)平說:“去年我們搞了一個(gè)小學(xué)同學(xué)聚會(huì),有人問起你,但沒人知道你的電話,找不到你。”我笑,想真要找我是找得到的,只是沒有人認(rèn)真找,認(rèn)真找還怕找不到么?我又沒出國,更沒飛上天。有同學(xué)在聚會(huì)上提到了我,于是有同學(xué)敷衍說:“啊,找他不到。”估計(jì)是這樣。我說:“那是的,我有很多年沒跟小學(xué)同學(xué)聯(lián)系過。”陳衛(wèi)平問我:“小學(xué)同學(xué)里你還記得哪個(gè)?”我脫口而出,“彭立中。”彭立中的父親救過我的命。這可不是寫小說,而是真的!我入小學(xué)前,六歲的時(shí)候我與彭立中去一師菜地的塘里舀青蛙的兒子——小蝌蚪,不幸落入塘中,是他父親趕到(他父親當(dāng)時(shí)是一師范的花匠),用糞瓢將我舀上來的。實(shí)際情況是這樣的,他父親把糞瓢插入水中,我攀住糞瓢的一端,他父親就把我拉了上來,拉上來就按我的肚子,把積壓在我肚子里的水?dāng)D出來,然后給我做人工呼吸,使我掙脫了死神的懷抱。這樣的人我當(dāng)然是第一個(gè)記得!她說:“還有呢?”我說:“楊湘漢。”小時(shí)候,父親被打倒,打成當(dāng)權(quán)派、走資派和叛徒。當(dāng)權(quán)派和走資派還能接受,“叛徒”一詞卻怎么也無法接受。因?yàn)橛幸粋€(gè)甫志高被雙槍老太婆一槍打死了,甫志高就是叛徒,《紅巖》里的,少年的我們都知道。那時(shí)候我們還玩過這個(gè)游戲,凡是被扮演叛徒的人,都被我們一頓猛揍。既然是“叛徒”的崽,那基本上就是被打入“冷宮”的,我就調(diào)皮,因?yàn)椴徽{(diào)皮不行,狗崽子,不調(diào)皮就會(huì)被別人欺負(fù)得更加厲害,一調(diào)皮就講狠,一講狠就要打架,一打架就有人來我家告狀,一告狀我那個(gè)父親就惱怒,他一惱怒我就要挨打。這是連鎖反應(yīng),一環(huán)連一環(huán)的。有天放學(xué),我回家,就見一個(gè)半小時(shí)前被我暴打過的同學(xué)的母親牽著兒子怒氣沖沖地從我家出來,我那個(gè)“叛徒”父親躬身相送。我一見,心里大叫一聲“不好”,拔腿就跑。
那應(yīng)該是冬天,因?yàn)樵谖业挠洃浝锬翘焱砩衔矣掷溆逐I,我就想起了楊湘漢。差不多是半夜了,我走到楊湘漢家的門口,敲門,門開了,是楊湘漢的母親。楊湘漢的母親一見我那副模樣,就知道我犯了錯(cuò)誤不敢回家。她說:“我楊湘漢已經(jīng)睡了。”我饑腸轆轆地望著楊湘漢的母親。她說:“你還沒吃飯吧?”我點(diǎn)頭,她就炒了碗油炒飯給我吃,還煎了個(gè)雞蛋。那雞蛋在我記憶里黃燦燦香噴噴的,讓我目光放亮。要知道,在那個(gè)物質(zhì)匱乏的年代,她為我煎一個(gè)雞蛋,楊湘漢就要少吃一個(gè)雞蛋啊。那天半夜,是她把我送回家的,從冬瓜山走到青山祠,少說也有五華里。她還要一個(gè)人走回去呢。好在那個(gè)年代,地痞流氓都不敢亂說亂動(dòng)。那天晚上,我在毛主席像下跪了一個(gè)多小時(shí)。父親沒打我,因?yàn)闂钕鏉h的母親說,重在教育,不要打人。父親讓我面對(duì)毛主席像認(rèn)識(shí)錯(cuò)誤,認(rèn)識(shí)了一個(gè)多小時(shí),膝蓋都“認(rèn)識(shí)”痛了,父親才讓我上床睡覺。這便是我記得楊湘漢的原因。假如不是陳衛(wèi)平,這些少年時(shí)代的記憶都丟在記憶的倉庫里封存了,可能永遠(yuǎn)也不會(huì)去翻動(dòng)。陳衛(wèi)平的出現(xiàn),這些少年時(shí)的記憶就掀開了,帶一點(diǎn)塵土味兒。
二 楊湘漢
楊湘漢是我小學(xué)時(shí)玩得最多的同學(xué),他住在長沙市南區(qū)的冬瓜山,我少年時(shí)候如果去冬瓜山,就是去楊湘漢家找他玩。少年時(shí)候的楊湘漢個(gè)子高大,講義氣,玩在一起等于是“武裝”自己。現(xiàn)在他還講不講義氣,不得而知。楊湘漢的母親非常好,給我留下了極好的印象,不光是那次送我回家,讓我免遭父親一次暴打。還因?yàn)槟鞘莻€(gè)善良的婦女,對(duì)楊湘漢的同學(xué)都好。我問:“楊湘漢也來了?”陳衛(wèi)平說——仍然是一臉友善的笑:“他來了,你還記得哪個(gè)?”有一個(gè)女孩子的名字從我嘴里蹦了出來,那種蹦簡直就是一顆石頭飆到車玻璃上似的,只差玻璃碎了!我說:“王愛英。”陳衛(wèi)平說:“王愛英?同學(xué)聚會(huì)時(shí)她來了,她還是那樣子。”這是陳衛(wèi)平說的原話,又說:“她沒什么變化,還是小時(shí)候那樣子。”我說:“真的嗎?”后來證明,王愛英不是我小時(shí)記憶里的那樣子,三十多年都過去了,不可能還是“那樣子”。陳衛(wèi)平與王愛英接觸得多,感覺不到王愛英的變化,我與王愛英三十多年沒見了,就能感覺到。三十多年,金子都會(huì)沾灰或生一種類似銹的東西,要拋光才能重新閃亮,何況人。我這樣說,并非是王愛英變丑了,而是人老了。這是沒辦法的,歲月就是這樣從我們這代人身上毫不留情地淌過的。
我這人婚姻念頭動(dòng)得早,說出來不怕你們笑話,我十歲時(shí)就想到了結(jié)婚。我懂事得可能早了一點(diǎn),差不多屬于“窮人的孩子早當(dāng)家”那一類,跟李鐵梅說不定還是表兄妹。那時(shí)候看到別人結(jié)婚,心就癢,就想到了自己要結(jié)婚。記得十歲那年,我和另一名叫周建輝的小學(xué)同學(xué)于某個(gè)晚上到勞動(dòng)廣場上玩,也不知是玩什么,那是夏天,兩個(gè)孩子沒事就跑到勞動(dòng)廣場上瞎玩。瞎玩中也不知是他引起的話題還是我引誘的話題,兩人開始討論班上的女同學(xué)誰最漂亮。他想了想說:“趙子琴最漂亮。”我說:“王愛英最漂亮。”周建輝反駁說:“我覺得趙子琴最漂亮。”我問周建輝:“為什么你認(rèn)為趙子琴最漂亮呢?”周建輝說:“我就是認(rèn)為趙子琴最漂亮。”我說:“我還是認(rèn)為王愛英最漂亮。”那時(shí)候,在我心里,男人長大就是二十歲,我就想我還要等十年才能與王愛英結(jié)婚就心里沒底,于是望著天空說:“還要等十年。”那時(shí)候,王愛英在我眼里能歌善舞,聲音又甜,全世界似乎只有她是最迷人的女孩,自然便是我童年時(shí)候夢(mèng)想的妻子。
王愛英現(xiàn)在是我另一小學(xué)同學(xué)劉鋼鋒的老婆,劉鋼鋒人非常好,很重同學(xué)情,同學(xué)們聚會(huì),他是組委會(huì)的主要成員。那天我在飯桌上把我十歲的時(shí)候與周建輝同學(xué)在勞動(dòng)廣場上說的話告訴同學(xué)們時(shí),他笑得最開心。王愛英也很愉快,采訪我道:“那你高中畢業(yè)后又沒來找我呢?”事實(shí)上我小時(shí)畢業(yè)后就離開了湖南第一師范,他們還在一師附小繼續(xù)讀書,讀那種“戴帽”初中。我父親因當(dāng)時(shí)是“叛徒、當(dāng)權(quán)派和走資派”,我媽怕我沒有初中讀,因?yàn)橐粠煹脑旆磁僧?dāng)時(shí)就成功地阻擋了我大姐讀高中。我媽怕一師的造反派不讓我再上學(xué)了,就在我小學(xué)畢業(yè)前夕將我轉(zhuǎn)到了她所在的新興路小學(xué),我是在新興路小學(xué)畢業(yè)的,進(jìn)了長沙市十七中學(xué)。陳衛(wèi)平、王愛英、劉鋼鋒、彭立中等卻是在一師附小讀的初中。我記得王愛英是因?yàn)槲疑倌陼r(shí)候特別喜歡她,第一次天真地動(dòng)婚姻念頭確實(shí)是動(dòng)在她身上。不過當(dāng)時(shí)動(dòng)得并不色情,那時(shí)小,還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生的,只知道男人女人都要結(jié)婚。不結(jié)婚,打單身,在當(dāng)時(shí)那個(gè)社會(huì)是很沒面子的事。
動(dòng)過那種念頭,當(dāng)然就記得王愛英。至今,我仍然能看見自己坐在勞動(dòng)廣場上煩惱的傻樣,愣著一雙單眼皮小眼睛,一時(shí)想這樣一時(shí)想那樣。那時(shí)的我經(jīng)常惹父母生氣,因?yàn)闀r(shí)常有大人怒沖沖地牽著孩子來我家告狀,告得我父親怒發(fā)沖冠,只差憑闌處了,岳飛的詞,臨時(shí)借用。小時(shí)候,我最怕的人是我父親,我們家六兄妹,他最煩躁的兒子當(dāng)然是經(jīng)常有人跑來告狀的我。在我眼里,父親力大無比,怒吼時(shí),頭發(fā)都豎了起來。話說回來,我盡管怕父親,還是要在外面“橫”,背著個(gè)黃書包,像個(gè)小混蛋。這是因?yàn)槟悴换斓埃瑒e人就對(duì)你混蛋。我又不喜歡被別人欺負(fù),那就索性還是我自己混蛋好些。陳衛(wèi)平很高興,說:“除了王愛英,你女同學(xué)還記得哪個(gè)?”從我記憶的島嶼上,又蹦出一個(gè)女孩,她矮矮的,嘟著嘴,很不高興我這時(shí)候才想起她,她說:“余軍。”這話好像不是我說的,是余軍自己跑到我腦海里說的,只怕還發(fā)了點(diǎn)氣。陳衛(wèi)平興奮了,“余軍?你還記得余軍?”
三 余軍
余軍在我的記憶里特別深,深得與我的少年無法分開,只要想起一師附小的日子,余軍就會(huì)游到我腦海里來。一個(gè)小姑娘,正直、喜歡跟我們男孩子玩,一張娃娃臉,于我的記憶里總是笑,趕也趕不走。自己都說不清,怎么就那么記得她!把她排在第四位蹦出來,可能有點(diǎn)委屈她。早一向見面,看見她,我差不多要哭了,不是我修煉得到堂,眼淚怕是要奪眶而出的。她的變化是我沒想到的,王愛英的變化,猶如陳衛(wèi)平所說,“還是老樣子”,就是說霸點(diǎn)蠻還是認(rèn)得出的。余軍卻不認(rèn)得了,完全不是我記憶里那個(gè)敢于站出來說“要不得”的那個(gè)小姑娘了。那個(gè)小姑娘的那句話讓我感動(dòng)得熱淚盈眶,讓我呼啦一下就痛哭流涕,還讓我像《智取威虎山》里的小常寶一樣居然吐出了“要報(bào)仇”的惡語。
記得一九七零年元旦前夕,一師范搞了臺(tái)慶祝元旦的文藝晚會(huì)。真的是晚會(huì),與一師的中專生一起慶祝元旦。我們附小的小演員上臺(tái)演《沙家浜》,代表新四軍的郭繼光一亮相,我們就熱情地鼓掌,在掌聲中匪兵們紛紛啊呀一聲“斃命”了。一師的中專生上臺(tái)唱《打虎上山》,楊子榮在《智取威虎山》里唱的,那聲音那唱腔那亮相的動(dòng)作,惹得我們小學(xué)生在禮堂里拚命鼓掌,手掌都鼓腫了,窗玻璃都被我們的掌聲攻擊得顫抖得十分厲害。在我們少年的眼里,一句話:確實(shí)唱得好!革命樣板戲演完了,殺氣騰騰的忠字舞也跳得差不多了,忽然一個(gè)大男人走上臺(tái)來,一聲喊:“把當(dāng)權(quán)派、走資派、叛徒何戈心等反革命分子押上臺(tái)來。”臺(tái)下的學(xué)生一下變得很肅靜了,都憋著氣,不動(dòng)。就見我父親的雙手被綁在身后,勾著腰第一個(gè)走上臺(tái),那可不是楊子榮做出騎馬的姿勢(shì)噔噔噔地上臺(tái),也不是李玉和提著紅燈邁上舞臺(tái),而是像地主老財(cái)樣被押上臺(tái)。在老電影里,這種場面的通常結(jié)局是將被工農(nóng)紅軍槍斃。跟著后面還有兩個(gè)“壞人”,三個(gè)人站成一排,我父親級(jí)別最高,自然站在中間,勾著頭和腰,面對(duì)著臺(tái)下的學(xué)生,一副讓我目瞪口呆的可憐巴巴相。
天啊,我就坐在臺(tái)下呢,那時(shí)候我讀小學(xué)三年級(jí),是個(gè)既懂事又不懂事的小孩子。同學(xué)們都知道臺(tái)上那個(gè)站在中間的手被綁在后面的男人就是我父親。父親的身前掛著塊牌子,牌子上寫著“叛徒、當(dāng)權(quán)派、走資派何戈心”。我們班上和隔壁班上,有好幾個(gè)一師的子弟,那一刻,他們都回頭看我。那目光肯定是同情的,當(dāng)然也有幸災(zāi)樂禍的。我當(dāng)時(shí)拚命忍著不哭,要?jiǎng)澢褰缇€,要立場堅(jiān)定。我是生在新社會(huì)長在紅旗下的。這些話,這些亂七八糟的思想就在我可憐巴巴的大腦里翻滾、打架,刁得一啊、土匪甲啊土匪丙啊都在我腦海里東倒西歪,就剩下一個(gè)郭繼光,泰山頂上一青松,一個(gè)亮相動(dòng)作支撐著我,讓我睜著兩只眼睛,卻拼命忍著不哭,剛剛看了革命樣板戲,受了革命教育的,對(duì)壞人壞事應(yīng)該仇恨,怎么能哭臉呢?一哭臉,那是站在什么立場上呢?
這時(shí)候,有一個(gè)造反派沖我父親身上踹了一腳,還用膝蓋壓著我父親的背,似乎想站到我父親背上去。我父親咧著嘴,當(dāng)然有點(diǎn)疼,不然他老人家咧嘴干嗎?那個(gè)造反派之所以這樣做,是想表示自己是最革命的。我也很革命,我沒哭,甚至臉上都沒露出同情,心里卻一派慌亂,仿佛有一群老鼠在我心田上亂竄。但我真的沒哭,目不斜視地盯著,因?yàn)槲遗峦瑢W(xué)們說我不堅(jiān)強(qiáng)。那個(gè)年代,為了表示自己是真的可以與“壞父親”劃清界線,我表現(xiàn)出了病態(tài)的堅(jiān)強(qiáng)。這一點(diǎn)也不奇怪,是你,你在那個(gè)左得一塌糊涂的年代,你也會(huì)表示堅(jiān)強(qiáng)。可是余軍的一句話打垮了我的堅(jiān)強(qiáng)!余軍坐在我前排,她回頭看了我一眼,只說了三個(gè)字“要不得”。就是這三個(gè)字把我的堅(jiān)強(qiáng)擊潰了。余軍無疑是同情我的,她說的“要不得”是針對(duì)那個(gè)造反派在我父親身上擂著,繩子拉來拉去,而發(fā)出的同情和感慨。一句要不得,惹得我眼淚水沖破了淚泉的閘門,一涌出來那就收不了場,索性哭了,嗚嗚嗚嗚嗚,轉(zhuǎn)背就跑出了禮堂。蹲在禮堂外面哭著,外面黑黑的,又冷,北風(fēng)那個(gè)吹,雪花那個(gè)飄,自己都覺得自己成了“何喜兒”。禮堂里卻燈火輝煌。我咬牙切齒,嘴里說我長大了一定要報(bào)仇。隔了會(huì),周老師出來了,說:“何斌,你要與你父親劃清界線。”我說:“我不曉得。”周老師說:“不要哭臉,你這樣做只能讓壞人高興。”我當(dāng)時(shí)并不知道壞人是誰,我只知道這個(gè)世界上只有一個(gè)好人,那就是我的女同學(xué)余軍。因?yàn)樵谖腋赣H在臺(tái)上挨批斗,讓我感到極其難堪和孤力無助時(shí),她居然站到了我一邊,說了三個(gè)字“要不得”。
很多年過去了,很多少年時(shí)候的同學(xué)跟我說過的話都忘光了,但余軍說的這三個(gè)字,我三十多年里都沒忘,而且永遠(yuǎn)會(huì)記下去。文革中,同情我的人很少,那沒辦法,那個(gè)年代誰會(huì)同情一個(gè)“叛徒、當(dāng)權(quán)派、走資派”的兒子?我父親于解放前是廣州中山大學(xué)畢業(yè)的,他在大學(xué)里時(shí)接受了馬列主義的影響,一畢業(yè)就回家鄉(xiāng)搞革命,參加了湘南游擊隊(duì)。湖南和平解放前夕,他被捕了,但他沒有叛變,后來搞清了,我父親確實(shí)沒有叛變。但是在那個(gè)亂搞的年代,被捕過那就有問題,有問題就是叛徒。這就是那個(gè)年代的邏輯!我就是叛徒的崽,叛徒的崽當(dāng)然就不招人喜歡,也就沒有什么人喜歡我同情我。余軍是唯一在文革中同情過我一回的,這也是我一直記得她的原因。陳衛(wèi)平說:“余軍也來了,我有她的電話。”我很高興,余軍我還真想見一面,我說:“是嗎?哪天你約他們一起吃頓飯吧?”陳衛(wèi)平說:“沒問題,我來約。你還記得誰?”我想了想說:“凌輝。”陳衛(wèi)平覺得奇怪,我怎么會(huì)記得凌輝,她問我:“凌輝你也記得?”我說:“我記得我讀小學(xué)三四年級(jí)時(shí),她是班長,她曾把我叫到教室外面,數(shù)我的缺點(diǎn),手指都扳爛了,扳來掰去,扳出我有二十四條缺點(diǎn)。”
四 凌輝
我記得凌輝那時(shí)是我們的班長,班長凌輝可不是一般人,是我們周老師的得力助手,周老師即使不在,她也能把一個(gè)班的同學(xué)管徹底。我是幾個(gè)在班上搗點(diǎn)小蛋的男同學(xué)中的一個(gè),還有點(diǎn)故意跟她對(duì)壘,因她是妹子,就不怕她。凌輝可不是一般女孩,她是那種敢于與壞人壞事作斗爭的女孩。她性格潑辣,目光犀利,因有老師給她撐腰,就什么都敢管。假如是解放前,那一定是個(gè)劉胡蘭,解放四村長大的女孩子,壞人見得多了,怕誰?假如你講話,她敢沖上來批評(píng)你講話;假如你上甲課干乙事,她就走過來很堅(jiān)決地把你的乙事奪去,就像黃世仁從楊白勞手里奪走喜兒一樣,而且還要批評(píng)你。她批評(píng)起人來,讓你覺得自己基本上不是人,是搗蛋鬼,是壞蛋。
記得一九七零年那個(gè)元旦晚會(huì)后,我就完全徹底地告別了“上進(jìn)”。有一個(gè)那樣的父親,你表現(xiàn)好也是白表現(xiàn)好,你表現(xiàn)再好,同學(xué)和老師都是視而不見的。就是那年元旦以前,我真的非常積極,一個(gè)學(xué)期里寫了三份盼望加入紅小兵的申請(qǐng)書,交給周老師。一放學(xué),無論是哪個(gè)組搞衛(wèi)生,我都留下來協(xié)助那個(gè)組的同學(xué)搞衛(wèi)生,想到雷鋒對(duì)待同志是春天般的溫暖就一臉春天般的笑,還帶點(diǎn)討好,很熱情地把桌椅擺得整整齊齊。一張桌子歪了,我會(huì)“撲”上去搬正。有同學(xué)不愿意倒垃圾,我就主動(dòng)去倒,拎著垃圾桶,走在路上都覺得自己是毛主席的好孩子。上課真正做到了把手放在后背,腰干挺得筆直,眼睛一眨不眨地瞪著老師。這樣做,只有一個(gè)目的,就是加入紅小兵。那個(gè)元旦晚會(huì),我記得有許多同學(xué)都加入了紅小兵,其中就有趙子琴和楊湘漢。令我氣憤的是,我親眼看見楊湘漢同學(xué)搞衛(wèi)生時(shí)跑了,他這種勞動(dòng)態(tài)度還可以加入紅小兵?趙子琴同學(xué)搞衛(wèi)生時(shí)玻璃都沒擦干凈就背起書包溜了,她也成了紅小兵!我這個(gè)天天表現(xiàn)好的要求自己嚴(yán)格的同學(xué),怎么就沒資格加入呢?我真的灰心失望了,覺得老師并沒有像她在教室里說的,一視同仁。
我一垮,那就很顯形,立馬就不搞衛(wèi)生了,不但不協(xié)助別的組搞衛(wèi)生,輪到自己這一組搞衛(wèi)生,也跑。上課再也不是筆直地坐著,不想學(xué)“泰山頂上一青松”了——那樣坐其實(shí)很累,可見青松筆挺地立在懸崖上,也不容易。成了坐沒坐相站沒站相的《沙家浜》里匪兵甲或匪兵乙,只差叼根煙了。作業(yè)也不交了,也不聽課,上課就玩“油板”或折疊“子彈”,準(zhǔn)備下課時(shí)有充足的子彈打彈弓仗,主要是打隔壁班上的同學(xué)。這樣做,自然引起了凌輝班長的憤怒。有天,不記得起因是什么,她把我叫出教室說:“何斌,你出來一下。”我出來了,她把我叫到走廊上,就開始數(shù)落我的缺點(diǎn):“你看你,你上課講小話、做小動(dòng)作,屁股扭來扭去,不交作業(yè),把某某女同學(xué)的書丟到地上,不搞衛(wèi)生就跑,擦玻璃就只安排你擦的窗戶沒擦干凈。”凌輝同學(xué)越說越氣,繼續(xù)數(shù)落我:“還有,數(shù)學(xué)課你畫飛機(jī),圖畫課你睡覺,還搶趙子琴同學(xué)的筆,搶胡艷燕同學(xué)的橡皮擦子,拿彈弓打女同學(xué)的頭,還把‘油板’帶到教室里來玩。你看你,你表現(xiàn)太壞了。”她數(shù)到二十四條后,再也數(shù)不下去了,就說:“你有二十四條缺點(diǎn)。你沒有一點(diǎn)優(yōu)點(diǎn),何斌,你應(yīng)該聽老師的話,重新做人,不然你將來很危險(xiǎn)你曉得嗎?”
我被凌輝同學(xué)數(shù)落得心里一陣陣發(fā)涼,就不敢還嘴,這也是我第一次不敢對(duì)一個(gè)女同學(xué)還嘴。我怎么有那么多缺點(diǎn)?二十四條缺點(diǎn)?按毛主席他老人家說的三七開,我的三七在哪里?我就沒一條優(yōu)點(diǎn)?我的優(yōu)點(diǎn)到哪里去了?原因是有的,嘴里沒說心里想到了,為什么像趙子琴、楊湘漢那樣沒我表現(xiàn)好的同學(xué)都加入了紅小兵,而不批準(zhǔn)我加入紅小兵?既然加入不了紅小兵,還表現(xiàn)好干什么?
那應(yīng)該是讀小學(xué)四年級(jí)時(shí)候的事。那時(shí)候的冬天真的很冷,地上不光下雪,還不顧一切地結(jié)冰,屋檐上吊下來的冰錐少說也有尺把長,讓我們這些在夏天里想吃冰棒又沒錢買的小學(xué)生,很興奮地踮起腳尖去舔,舔得你不由得不打寒噤。那時(shí)候我家早已從一師大宿舍搬了出來,住到了青山祠的街上,青山祠居委會(huì)為了宣傳毛澤東思想,掛了好幾個(gè)高音喇叭,有線廣播總是很無情地播放著:北風(fēng)那個(gè)吹,雪花那個(gè)飄……讓少年的我們感覺就更冷。那天被凌輝班長數(shù)落一通后,回家,我穿著厚厚的棉襖一點(diǎn)也不覺得暖和,勾著腰,縮著脖子,像電影《白毛女》里的楊白勞穿過黃世仁的屋場樣,因欠債心虛,心里就疑惑,我有這么多缺點(diǎn)?二十四條?我就沒優(yōu)點(diǎn)的?
五 馬寧
陳衛(wèi)平見我還記得一些同學(xué)便鼓勵(lì)地問我:“你還記得哪個(gè)?”我正想說趙子琴和符艷燕,陳衛(wèi)平見我口里有點(diǎn)猶豫,便搶在我前面拋出馬寧,問我:“你還記得馬寧么?”我腦海里那一刻只有兩個(gè)女同學(xué)——趙子琴和符艷燕,再就是羽毛球館和那幾個(gè)打著羽毛球的陳衛(wèi)平的同事,沒有馬寧,便搖頭說:“不記得。”陳衛(wèi)平表示吃驚,“馬寧你不記得?馬寧噯,”她簡直不相信,于是煩躁地說:“你不記得馬寧?”我說:“不記得。”陳衛(wèi)平啟發(fā)我的記憶說:“就是那個(gè)住在妙高峰下面的馬寧,他說你們小時(shí)候經(jīng)常玩在一起。”我搞亂了,妙高峰下面我有點(diǎn)模糊。妙高峰上面我倒是很清楚,因?yàn)槊罡叻迳厦孀≈业膬蓚€(gè)姓劉的同學(xué),一個(gè)叫劉國奇,一個(gè)叫劉國華。
劉國奇是正宗的同班同學(xué),小時(shí)候不怎么開口說話,但打架很兇,不出手時(shí)蠻好,一出手就出重拳,打得你流鼻血,因而得仰起頭止血。我就被劉國奇打得流過一次鼻血,所以我記得劉國奇。劉國華我更是能記得,少年時(shí)我們是甲班,他在乙班,但他喜歡跟我玩,一是我那時(shí)候愿意破罐子破摔,其次我們彼此欣賞,彼此見面就笑,都把牙齒笑得一顆顆暴露出來。一下課,他就跑到我們班的教室外面找我,對(duì)我笑,笑得跟貓記一樣——很友好。劉國華的臉本來就短,一笑,就更短了。劉國華有一個(gè)哥哥,少年時(shí)是我們崇拜的偶像,敢打架,不怕事,兇起來稱得上好漢。我聽劉國華自己形容他哥哥說:“我哥哥用扁鐵打過某某某,打得對(duì)方的腦殼流好多血。”他哥哥敢用扁鐵砍人,我很佩服。
妙高峰有兩個(gè)出入口,一個(gè)在書院路上,一個(gè)通向由義巷。馬寧住的那棟兩層的舊紅磚樓房,就在妙高峰的末端,再向前走一步,便是由義巷。那棟紅磚樓房是解放前,有錢人建的公館,解放后,充了公,住了好幾戶人家。陳衛(wèi)平十分奇怪,說:“馬寧你都不記得了?就是讀小學(xué)三、四年級(jí)時(shí),從北京轉(zhuǎn)來的同學(xué),講一口普通話的。”我說:“哦,你是說他?有點(diǎn)印象。”陳衛(wèi)平說:“他說你們以前玩得好。”我想不起來道:“玩得好?那沒印象。”但那天回到家,躺在鋪上,我想起來了。馬寧真的是我們讀小學(xué)三四年級(jí)時(shí)轉(zhuǎn)來的,小時(shí)候長得很好,一張臉很干凈,不像我們這些在青山祠和由義巷長大的孩子,不怎么注意衛(wèi)生。馬寧轉(zhuǎn)來時(shí)個(gè)子不高,穿得比我們好,說一口標(biāo)準(zhǔn)的普通話。那時(shí)的長沙冬天經(jīng)常下雪,一下雪地上就泥濘不堪,記憶中馬寧有一雙皮棉鞋可以踏雪。我們的鞋子,一入雪,襪子就濕了,冰冷的,冷得走路時(shí)腳趾都緊緊地勾著,無論跑到哪家,第一件事就是脫下鞋子,把腳很堅(jiān)決地伸到火爐上猛烤,烤得熱氣騰騰,自然還臭氣熏天,把一旁的大人熏得紛紛逃竄。待把腳烤干,又塞進(jìn)鞋底已經(jīng)透濕的鞋子,跑進(jìn)雪地里,又開始忘我地打雪仗。打到一身冷了,又往家跑,烤火、烤腳,烤暖了又出來再戰(zhàn)。由義巷里住著一個(gè)同學(xué),叫周建輝。周建輝家的對(duì)門就是南區(qū)少年之家。那時(shí)候跑到南區(qū)少年之家打雪仗,打得滿身是雪,是冬天里我們這些住在少年之家附近的同學(xué)最開心的事情。
馬寧當(dāng)然和我們一起玩,這個(gè)說普通話的小孩,穿得比我們好,記得他冬天里還有一件大衣穿,個(gè)子又比我們矮一點(diǎn),像個(gè)文明人,人也比我們老實(shí),我們就沒去挑釁他。記憶中,雪球落到他身上,他就文明地一笑,不努力還擊你,這樣你即使是野孩子也不好再下手。我們是小小少年時(shí)也講規(guī)矩和道理,該出手時(shí)就出手,打不贏就抱頭鼠竄,但不欺負(fù)不還手還笑的人,因?yàn)槲渌珊汪斨疃疾黄圬?fù)這樣的人,我們就也不欺負(fù)。
這就是記憶中的馬寧,也許這個(gè)馬寧在我貧乏的記憶里,與其他幾個(gè)聽話又表現(xiàn)好的孩子搞混了,但錯(cuò)也錯(cuò)不到哪里去。畢竟同過學(xué),又畢竟放學(xué)后一起回過家,還畢竟他對(duì)我笑的時(shí)候,發(fā)出的是普通話的笑聲。那笑聲在我的記憶里,就是好聽。陳衛(wèi)平那天興致很高,嘴里裝了一大把同學(xué),她把馬寧說完就拋出張明,她說:“張明你應(yīng)該記得吧?張校長的兒子。”我說:“張明,記得。我記得他。”
六 張明和劉鋼鋒
面對(duì)陳衛(wèi)平同學(xué)一臉的期待和熱情,我腦海里跳出一個(gè)男孩,他單瘦,白凈,說話聲音不高,少年時(shí)常抿著嘴,看人時(shí)用正眼看,不像我們斜著眼睛瞟,且像個(gè)有教養(yǎng)的孩子。我父親在湖南第一師范被打倒后,張明的父親接替我父親主持一師范的工作。讀小學(xué)時(shí),張明沒和我在一個(gè)班,按說不會(huì)玩到一起,但都是一師子弟,就認(rèn)識(shí)。張明小時(shí)候不跟我玩,可能是嫌我長得不好,他跟一個(gè)小名叫“強(qiáng)伢子”的人玩。那個(gè)強(qiáng)伢子比我們高一屆,強(qiáng)伢子的父母是文革中調(diào)入一師的,我跟他玩得不多。一師現(xiàn)在面朝書院路的那塊地,在文革中是塊菜地,一師在那塊菜地上建了棟紅磚平房,強(qiáng)伢子就住在那棟平房里,張明也常出現(xiàn)在那棟平房前,我的記憶里,張明總是與那棟平房和強(qiáng)伢子聯(lián)系在一起。
張明有兩個(gè)姐姐,二姐姐比我們高一個(gè)班,大姐姐比我們大幾歲。張明的大姐在我的印象里很漂亮,個(gè)頭不高,但長得很美,是少年時(shí)我見到的姐姐里讓我覺得長得好看的姐姐。后來他大姐怎么樣和現(xiàn)在他大姐怎么樣,我一概不知。那時(shí)我們是小孩子,他大姐經(jīng)過我們身邊時(shí)是不看我們的——盡管我們都偷偷地打量她,而且大膽地記住了她。我后來長大了寫小說,第一次使用“輕盈”一詞,腦海里就跳出了張明的大姐。記憶中,張明的大姐走路就很輕盈,姿勢(shì)也好看。記得有次在一師的什么地方玩,她大姐從我們幾個(gè)孩子前面經(jīng)過,張明叫了聲“大姐”,我這才知道張明有一個(gè)很漂亮的大姐。張明的父親胖胖的,個(gè)子不高,戴副眼鏡,很知識(shí)分子和很干部相,走過時(shí),沒聲音,不像某些大人,人還不見,腳步聲就先來了。張明的父親走到面前來了,我們才發(fā)現(xiàn)一個(gè)知識(shí)分子模樣的大人一下子占滿了我們的眼球。我告訴陳衛(wèi)平,少年時(shí)候我跟張明玩得不多,因不在一個(gè)班,還因他是校長的兒子,我是“叛徒”的兒子,玩在一起別扭,就沒玩。陳衛(wèi)平說:“張明現(xiàn)在很胖,你看見他,可能認(rèn)不出他了。”后來見面,我果然就沒認(rèn)出張明,那么胖,胖得臉上肉兒有些不情愿地鼓脹,這把他應(yīng)該有的帥勁擠到我找不到的地方去了,好像一杯茶,你不斷地兌開,就把茶味沖淡了似的。
陳衛(wèi)平說:“劉鋼鋒你還記得么劉鋼鋒?”我迅速在腦海里查找,沒找出一個(gè)叫劉鋼鋒的小學(xué)同學(xué)來。陳衛(wèi)平就提醒我:“隔壁班上的,不是我們班的。”我吐了口氣,說:“難怪,你說劉鋼鋒,我就努力搜索班上的同學(xué),想了半天都沒想出來。你說是隔壁班上的,我倒是還有點(diǎn)印象。”陳衛(wèi)平接著說:“他后來參了軍,轉(zhuǎn)業(yè)后在公安系統(tǒng)工作,現(xiàn)在是王愛英的老公。”我大驚,“王愛英的老公是劉鋼鋒?”劉鋼鋒在我的記憶里比較模糊,但不是完全沒有。我記得隔壁班上確實(shí)有個(gè)叫劉鋼鋒的少年,那時(shí)候他長得比我好,也比我高,白白凈凈一張尖臉,跟我的小學(xué)同學(xué)楊湘漢樣穿得比較干凈,不調(diào)皮,待人很情真意切。那時(shí)候他來我們班玩是不是為了王愛英,只有他自己知道。少年時(shí)候我們?cè)嬖谝黄穑m玩在一起的時(shí)間并不多,但拚命搜索還是能搜索出一個(gè)模糊的劉鋼鋒影像。不像楊湘漢和彭立中,不要陳衛(wèi)平提起,兩個(gè)兒時(shí)的同學(xué)就沖破記憶之門,一躍,自己蹦了出來,鯉魚跳龍門也不過如此,目光炯炯,毫不客氣,只差在我腦門上拍一下了。
陳衛(wèi)平一心要從我腦海的倉庫里挖一個(gè)班的同學(xué)來,以此來考查我的記憶,就像領(lǐng)導(dǎo)干部考查即將提拔的人一樣。“你還記得哪個(gè),何斌?”她審視著我,看我的記憶力是不是能及格,我說:“趙子琴和符艷燕。”陳衛(wèi)平比較滿意了,看著我笑,只差說“你行吧”那樣的話了。她根本就不打算還打羽毛球的樣子望著我,說:“趙子琴和符艷燕你都記得?”她給我打分說:“可以吧。”我終于聽到了來自于我小學(xué)同班同學(xué)表揚(yáng)我的話,一時(shí)把我騙到了從前,覺得自己可以面對(duì)毛主席像,舉起單薄的右臂,揩一把清鼻涕,宣誓加入紅小兵了,就低調(diào)說:“只是記得一點(diǎn)。”
七 趙子琴和符艷燕
趙子琴是個(gè)溫柔的女孩,不是凌輝,也不是余軍,更不是王愛英。讀小學(xué)的時(shí)候,趙子琴雖沒跟我同座,但曾坐在我后面過,只要一掉頭,就可以看見她那張臉。記憶中,她那張臉像只六月的桃子,紅得好看,雙眼皮眼睛,目光沉靜,不是那種調(diào)皮或好奇的目光。在讀小學(xué)時(shí),班上有兩個(gè)女孩長得漂亮,一個(gè)是王愛英,一個(gè)是趙子琴。王愛英比趙子琴愛玩,下了課就玩跳繩或玩女孩子在那個(gè)年代玩的東西。趙子琴卻坐在座位上,凌輝、符艷燕或其他女同學(xué)會(huì)主動(dòng)走上來找她。我讀書時(shí)心里裝著玩,就丟三拉四,上課常常忘了帶鉛筆或橡皮擦子,趙子琴的文具盒里什么都有,我回頭拿就是了。她人好,不拒絕幫助同學(xué)。記得那時(shí)候我從不帶削鉛筆的刀,鉛筆用鈍了,就掉頭找她文具盒里的鉛筆刀。她的鉛筆刀的“處女”用,有幾次都是我。因?yàn)樗龝?huì)強(qiáng)調(diào):“我還沒用過頭次的。”老師見我老是回頭打擾趙子琴,就把她調(diào)到我前面一排坐。沒用,上課時(shí),我如果沒帶橡皮擦或鉛筆,就踢她的椅子,踢得很干脆,慢了還不行,假如她還不給我我就扯她的辮子。趙子琴不會(huì)發(fā)氣,她不是那種愛發(fā)氣的姑娘。她會(huì)把我要的東西給我。這就是我記憶中的趙子琴。一個(gè)好姑娘。有一首歌,《同桌的你》,應(yīng)該把這首歌送給她。
陳衛(wèi)平說:“趙子琴現(xiàn)在在湘潭,她有點(diǎn)不幸。”不等我開口,陳衛(wèi)平又低聲說:“她換了兩次腎,用了六十萬。”我瞪大了眼睛,“真的?”陳衛(wèi)平說:“她老公對(duì)她很好,在治病上,趙子琴的老公對(duì)她十分用心,照顧她,關(guān)心她,真的是個(gè)好男人。”我好半天都無語。陳衛(wèi)平說:“趙子琴也參加了同學(xué)聚會(huì),她胖了。為了治病,她呷的藥里含激素,激素使她發(fā)胖了。”陳衛(wèi)平又說:“她在湘潭,同學(xué)聚會(huì)叫她不方便。”我忙點(diǎn)頭,說:“她身體不好,叫她從湘潭跑來,那太麻煩她了。”我想象不出趙子琴今天的模樣,但突然有一句話從我記憶的深處蹦了出來,那句話是:“慢點(diǎn)著”。每次我踢她的凳子或扯她的辮子,問她借東西,她總是這么回答我:“慢點(diǎn)著。”聲音不高,但我能聽見。我轉(zhuǎn)而問符艷燕:“符艷燕現(xiàn)在在哪里工作?”陳衛(wèi)平說:“符艷燕在寧波,她現(xiàn)在是寧波市教育局局長,在小學(xué)同學(xué)中搞得算好的。”我首肯道:“當(dāng)局長了,當(dāng)然算好的。”
符艷燕在我腦海里的形象其實(shí)很模糊,還真想不起她在班上的樣子,能想起來的是冬瓜山的一個(gè)場景。記得那時(shí)候我去楊湘漢家玩,在路經(jīng)一處平房時(shí),我看見了符艷燕。那時(shí)候符艷燕、楊湘漢和王愛英家相隔不遠(yuǎn),就是前后棟的樣子。符艷燕家住的那棟平房格外破一點(diǎn),在山坡上,她家的門前就栽著樹,什么樹不記得了。那天我看見符艷燕站在門前漱口,她也看見了我,我們沒說話。當(dāng)時(shí)我想她才起床。在一師附小讀小學(xué)的幾年里,我不記得我跟符艷燕說過話。她好像不能吸引我,我也不能吸引她,她玩她的同學(xué),我玩我的同學(xué)。記得她,恐怕是那次她站在家門前漱口的原故,那應(yīng)該是某個(gè)星期天的上午,不是四五月就是九十月,不冷不熱的天氣,因?yàn)橛洃浿形覀兌紱]穿棉襖,也不是穿襯衣。還有那棵樹,有點(diǎn)歪,離她家也近。后來冬天我去楊湘漢家玩,看見那棵樹,那棵樹的葉子全掉了,結(jié)了冰,冰吊下來有半尺長,風(fēng)冷冷的,沒人,就有點(diǎn)凄涼。
這其實(shí)就是我記憶中的符艷燕,與那棵樹和那棟破平房糾纏在一起,讓我不由得回憶起小學(xué)四年級(jí)時(shí),危老師教我們唱的《聽媽媽講那過去的事情》,那首歌感情充沛卻怨聲載道。危老師踩著風(fēng)琴,踩得噗哧噗哧響,唱一句,我們就在下面學(xué)唱一句,就有破屋子和凄涼的樹在我眼里晃悠。符艷燕當(dāng)時(shí)很瘦,個(gè)子在女同學(xué)中卻算高的,記得她是班上的體育委員,干部。那時(shí)我像個(gè)小農(nóng)民,一看見干部就臉露尊敬,一尊敬就索性不理。陳衛(wèi)平同學(xué)問我還記得誰,我說了周建輝,陳衛(wèi)平同學(xué)有點(diǎn)困惑,因?yàn)樗悬c(diǎn)記不得周建輝了。她說:“周建輝?我們班上有個(gè)周建輝?”我說:“有的,不騙你。”好像我曾經(jīng)是個(gè)專門騙人的騙子似的。她說:“那我沒印象。”我就幫她回憶,地點(diǎn)、時(shí)間一一提供給她,還把周建輝的模樣描述給她聽。我說:“回憶起來沒有陳衛(wèi)平?”陳衛(wèi)平一片茫然說:“周建輝、周建輝?”她拍拍腦門,說:“這名字好熟的。”我說:“他姐姐是做裁縫的。”她又拍下腦門,這一下好像把記憶倉庫的大門拍開了,“你這樣說,我又有點(diǎn)印象。”
八 飄呀飄呀的周建輝
很小的時(shí)候,老師為了我們的安全起見,每天放學(xué)都叫我們排路隊(duì)。同學(xué)們就按回家的方向排路隊(duì),一邊唱歌一邊走。女孩子都認(rèn)真唱歌:毛主席啊/您是燦爛的太陽/我們像葵花等等,男孩子卻笑笑嘻嘻,你踢我一腳,我反身推一下你的肩什么的。我們這支“路隊(duì)”從一師附小出發(fā)時(shí)有十幾個(gè)同學(xué),經(jīng)過妙高峰和一師大宿舍,拐入由義巷時(shí)便只剩了我和周建輝。我們兩個(gè)人住得近,到了周建輝家,周建輝一走,路隊(duì)就沒有了,再走幾步,我就進(jìn)了青山祠一號(hào)。周建輝家我常去,原因是周建輝住在南區(qū)少年之家正對(duì)門,那時(shí)候南區(qū)少年之家是不關(guān)門的,整日有孩子進(jìn)去玩,玩蹺蹺板或攀著雙杠練臂力,要不就在沙坑上翻跟頭或摔跤。冬天里就跑進(jìn)去打雪仗。腳打濕了,襪子濕透了就沖進(jìn)周建輝家烤腳。周建輝的奶奶和母親如果在烤火,見我們跑來,會(huì)皺著眉頭逃開,因?yàn)槲覀儠?huì)把自己的濕腳烤得熱氣騰騰,而熱氣里總是有比鮮花味道次一點(diǎn)的腳臭。
周建輝家是城市貧民,我始終沒弄清楚周建輝的父母是干什么事的,但有一點(diǎn)我知道,周建輝家是私房,他父親經(jīng)常對(duì)破舊的房子修修補(bǔ)補(bǔ)。他不大搭理我和周建輝,輪到他搭理周建輝時(shí),基本上是罵人。而逢這時(shí)候我就開溜。我小時(shí)候常上他家玩,是周建輝小時(shí)候比較聽我的,我說:“周建輝,去楊湘漢家玩罷?”他就點(diǎn)下頭,跟著我去。我說:“周建輝,我們?nèi)ヒ粠煼蹲津序邪桑俊彼矔?huì)跟著我去。周建輝小時(shí)候長得很可愛,他有點(diǎn)小個(gè)性,但不會(huì)跟我發(fā)脾氣,我叫他到哪里去他總是跟著,一邊走一邊蹦,嘴里還念著什么。這就是我記憶里的周建輝,一個(gè)愿意用大量的時(shí)間跟我玩的同學(xué)。他生氣了,最多是不吭聲。他高興了會(huì)蹦跳。真是這樣。他們家前有一棵槐樹,槐樹一到陽歷三月份就開滿了一串串白花,白花很小,花中有一顆綠芯。有年他家門前的槐樹開了很多花,他望著槐花對(duì)我說:“我奶奶說,槐花可以吃。”我就問他奶奶,他奶奶說:“可以吃,過苦日子的時(shí)候,大家沒飯吃就摘槐花吃。”我們就從他家搬出梯子,爬上槐樹摘槐花吃。一串槐花往嘴里一放,用牙齒半咬著,將花莖扯出,于是就有一口清香和淡淡的甜落入牙縫中。吃了,以為會(huì)拉肚子,結(jié)果什么也沒拉。
童年時(shí)玩得最好的伙伴是彭立中,我和彭立中是在幼兒園玩起的,兩個(gè)孩子經(jīng)常違背老師的意愿,睡到一張床上,主要是我擠到他床上睡,那時(shí)我父親是一師的校長,幼兒園是一師的幼兒園,老師就睜只眼閉只眼,隨我們?nèi)ァI钊氲叵耄倚r(shí)候調(diào)皮是從幼兒園開始的,是幼兒園的老師放縱的,就因我父親是校長,阿姨們管我時(shí)就有點(diǎn)猶豫。周建輝是我家從一師大宿舍搬到青山祠后,少年時(shí)玩得最多的同學(xué),那時(shí)候我在大人眼里是“狗崽子”,他也愿意跟我玩,這也是我很記得他的原因。畢業(yè)了,初中不在一所學(xué)校,就沒玩了。
九十年代中期,我的長篇小說《我們像葵花》和《就這么回事》,分別被杜憲和張藝謀買了影視改編權(quán),報(bào)紙和電視就紛紛宣傳,周建輝在電視里認(rèn)出了何頓就是他的小學(xué)同學(xué)何斌。那段時(shí)間我住在九中,我母親就常來九中。一天,母親來了,提著菜,告訴我,她在菜場里碰見了我的同學(xué),那同學(xué)說他早一向在電視里看見了我,想找我玩。我問母親是誰,母親說:“他姓周,住在南區(qū)少年之家對(duì)面,他姐姐是做裁縫的。”我說:“是周建輝,你怎么不帶他來?”母親說:“我怕他影響你寫作。”我說:“影響什么啊,他是我小學(xué)時(shí)候最好的同學(xué)呢。”母親就笑,“我怎么知道?!”我后來去過周建輝家住的地方,那里已成了一師的宿舍,周建輝家搬走了,搬到哪里去了我不知道。這讓我想起鄧麗君唱的《小路》,歌詞很切合我此刻的心:天上的云到處地飄/飄到哪里不知道/你不要像天上的云/飄呀飄呀飄得不見了……人生就是云,一朵朵的云,在地上走的云,所以有人形容某人說“他在社會(huì)上飄”,誰也不知道自己將飄向哪里,都基本上是飄呀飄呀飄得不見了。
九 聚會(huì)
在秦皇食府同學(xué)見面時(shí),我問及過周建輝的下落,都搖頭,都不知道他飄到哪里去了。他們說,同學(xué)聚會(huì)時(shí),兩個(gè)班的同學(xué)有一百多,到了七八十,還有三四十個(gè)同學(xué)找不到。劉鋼鋒給了我一張同學(xué)的合影,合影后面有人名和手機(jī)號(hào)碼。很多張臉我都無法辨識(shí),不是故意的,而是有限的記憶本來就沒去記他們。但照片上,有兩個(gè)女同胞我還記得:李美芬和焦雪平。原因是我一度跟她們的弟弟玩得好。李美芬的父親是一師的軍代表,焦雪平的父親在我父親倒臺(tái)后,也任過一師的校長。她有個(gè)弟弟,小時(shí)候挺喜歡跟我玩。焦雪平很小的時(shí)候就戴眼鏡,她在班上不出“煙絲”。我們這代人小時(shí)候說誰不引人注目就是說誰不出煙絲。李美芬有一雙大大的眼睛,小時(shí)候她那雙眼睛就很大,看人時(shí)有點(diǎn)羞澀,對(duì)她還想多掏點(diǎn)記憶,卻掏不出來了。能記得她也是與她弟弟玩得好,她弟弟少年時(shí)喜歡跟著我畫畫,我常常帶著她弟弟去湘江邊上畫船和柳樹,要不就坐在一師的紀(jì)念館下畫遠(yuǎn)處的風(fēng)景。
我打了李美芬的手機(jī),她很驚訝,也很高興。我告訴她,十二月八日上盛世芙蓉吃晚飯。六點(diǎn)鐘。我又打了焦雪平的手機(jī),焦雪平?jīng)]接。但焦雪平還是來了,是王愛英通知她來的。這一天我?guī)Я藬?shù)碼相機(jī),就是為了聚會(huì)時(shí)能與同學(xué)們合個(gè)影,免得飄到哪里又不知道了。如今的人,見面親親熱熱,轉(zhuǎn)身就忙自己的去了。拍點(diǎn)照,是幫助你記住他或她。那天是我生日,我特叫老同學(xué)與我一起過生日,大家有老感情,聊天就聊得很熱烈,玩笑燕子一樣飛來飛去,就相當(dāng)輕盈。吃飯時(shí),我說去唱歌。彭立中就打電話聯(lián)系場子,他說某賓館的老總是他朋友,他經(jīng)常上某賓館唱卡拉O K。我將同學(xué)的身影都攝入我的相機(jī),一行人就去唱歌。楊湘漢的歌唱得好,聲音有點(diǎn)專業(yè),記得他小時(shí)候是不唱歌的,可見人總是會(huì)變。劉鋼鋒唱得也不錯(cuò),愛唱軍人歌曲,他當(dāng)過兵,有軍人情結(jié)。馬寧的歌也唱得有意思。看來這幾位男同學(xué)都是愛進(jìn)卡拉O K廳的。女同學(xué)里,王愛英最活躍,什么歌,撿起麥克風(fēng)都能唱,這與她少女時(shí)候有點(diǎn)一脈相承。陳衛(wèi)平和焦雪平分別也唱了幾支歌,我仔細(xì)聽了聽,都唱準(zhǔn)了,記得陳衛(wèi)平小時(shí)候是不唱歌跳舞的,一天到晚背著書包,心事重重的樣子搞著學(xué)習(xí)。現(xiàn)在也會(huì)唱歌了,用長沙老話說,當(dāng)然是超發(fā)了。我笑著鼓勵(lì)李美芬唱歌,李美芬在王愛英的帶動(dòng)下勉強(qiáng)唱了一首。余軍和凌輝,無論我怎么勉勵(lì),硬是不唱。
唱歌期間,彭立中要了好幾瓶紅灑,兌了雪碧,放了話梅,喝起來就有種甜。碰杯、敬酒、唱歌,都很開心。十二點(diǎn)鐘,彭立中叫來服務(wù)生,拆開了蛋糕。蛋糕是陳衛(wèi)平和張明、王愛英三個(gè)人買來的。他們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就買來了蛋糕。點(diǎn)燃蠟燭,關(guān)了燈,要我許個(gè)愿,再吹滅蠟燭。那天,在那個(gè)卡拉O K包房里,我只許了一個(gè)愿:愿同學(xué)們都好。一口氣吹滅了蠟燭,生日快樂之歌便從音響和我同學(xué)的嘴里一起唱了出來。他們望著我,我也望著他們,就覺得這個(gè)世界于這一刻十分美好,友誼沸騰了,開水開了樣,讓我牢記!
買單時(shí),彭立中掏錢包,問好多錢。我說我來,錢包都掏到手上了,彭立中瞟我一眼說:“怎么,看兄弟不起?”一句話,說得我很感動(dòng)。與彭立中的關(guān)系,前文已經(jīng)說了,幼兒園時(shí)就玩起的。少年時(shí)候,我們沒東西玩,就玩蛐蛐。彭立中的母親當(dāng)年在一師的食堂工作,每天凌晨四點(diǎn)鐘起床,彭立中待母親一走,自己就爬起床,跑到我家窗前吹口哨。我不醒來,他就堅(jiān)決地吹,直把我吹醒為止。往往天還沒亮,兩個(gè)孩子就去一師的菜園或山坡下捉蛐蛐,因沒有手電,就用紙卷成筒筒,包著電池,拿根銅絲,一頭扎著燈泡,一頭系一塊銅片,一接,燈泡就亮了。就靠著這種土辦法捉蛐蛐。捉了蛐蛐就拿回來與別的孩子的蛐蛐打架,打贏了,那天就特別快活。打輸了,第二天一早,倆人又天不亮就去捉,立志要捉只更惡的蛐蛐。這就是我和彭立中的童年和少年。
走出來,街上一股冷風(fēng)吹得我一噤,就見王愛英和焦雪平都把圍巾圍了起來,陳衛(wèi)平和彭立中都縮了下脖子,劉鋼鋒和馬寧忙一臉正經(jīng)地扣著棉襖扣子,余軍、凌輝把衣領(lǐng)豎起來遮風(fēng)。我笑笑,對(duì)諸位同學(xué)說:“今天我的生日過得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