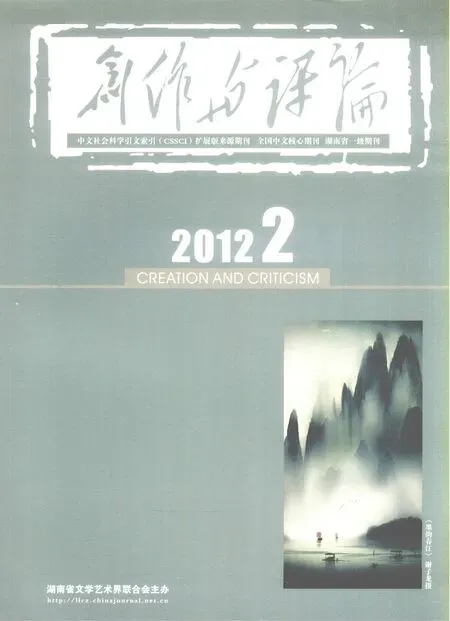從“奇觀”到“日常”*——畢飛宇《推拿》底層敘事的意義
■ 明飛龍
問世于2008年并于2011年獲得第八屆茅盾文學獎的《推拿》延續了畢飛宇一貫的寫作風格,它以細膩綿密的細節描寫、內斂飽滿的敘事語調、靈動曼妙的藝術手法,在展現身處社會底層的盲人推拿師的生存境況與精神世界的同時,也彰顯出一種豐沛沉郁的審美內涵。而就其底層敘事來說,它有別于當下流行的那些以“苦難”為關鍵詞的的底層敘事,它為底層文學書寫提供了一種新的敘事立場,對底層文學的發展來說,有不可忽視的意義。
一
對“底層”的書寫是文學史中常見的主題,因為文學離不開對苦難的關注。尤其是新世紀以來,隨著底層寫作思潮的興起,那種“對一切有關底層平民生活模態的敘述”的“底層敘事”顯得異常活躍,一大批表現底層民眾生活和命運的作品呈現于文壇。這些作品有的是呈現底層人物物質與精神生活都深陷苦難的生存狀態,作者對生活矛盾不回避、不粉飾、不遮蓋,把慘烈殘酷乃至血腥的生存場景赤裸裸地揭示出來,比如方方的《奔跑的火光》、孫惠芬的《民工》、陳應松的《馬嘶鳴血案》等。有的逼直地展現社會的不公及社會制度的不健全對底層人物帶來的嚴重傷害,揭示出底層人物的悲慘命運大多是社會現實所致,比如曹征路的《那兒》、《豆選事件》、胡學文的《行走在路上的魚》等。有的深入解剖人性的黑暗,呈現人性的劣根性對底層人物帶來的災難,呼喚一種健全人性的回歸,比如劉慶邦的《神木》、《臥底》、《穿堂風》等。這些作品基本上是緊緊貼近時代的脈搏,把當下階層化日益加劇,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社會嚴重不公等社會現實揭示出來,充滿對社會現實的批判,對底層人民的同情。對底層群體苦難生存狀況的積極表達,表達了現代知識分子的良知和責任。
但是,這些作品在充分展現底層人物生存困境的同時,在敘事藝術上存在一定的缺陷,有的論者指出:“底層文學書寫出現了內容上的奇觀化、主題上的欲望化、情節設置上的偶遇化模式。內容的奇觀化主要體現為對獵奇感的追求,這一方面表現為對底層生活的陌生化領域和獨特生活經驗的挖掘,如荒山野嶺、礦山礦難、民工生涯、風月生涯、國企破產、逼良為娼等邊緣場所邊緣人生成為通行的表現場域;另一方面則是在這些場域中發生事情的夸張化,具體表現為對苦難的獵奇和夸張轉化為殘酷與悲慘的比賽。”①這在底層文學中是一個不可忽視的現象,比如在《馬嘶鳴血案》中,九財叔和“我”僅僅因為二十塊錢的緣故而連殺七人,最后九財叔連“我”也不放過,而其中九財叔打架,被電槍擊中,連殺七人的場景,被作者敘述得鮮血淋漓,驚心動魄,彌漫著血腥的暴力。比如在《奔跑的火光》中,農村婦女英芝忍辱負重,為的是過上幸福的生活,但生活的美夢卻一次次被撕成碎片。丈夫毒打她、虐待她,婆婆輕賤她、刁難她,英芝不得不一次次逃避,一次次抗爭,但都是枉然,最后在走投無路之際燒死丈夫,也毀掉了自己。這些過程也被作者展現得異常慘烈。比如在《家園何處》中,那位農村女孩在包工頭的引誘下失身,繼而又被包工頭轉給別人玩弄,久而久之,那女孩也就習慣了賣身生涯,對自己的墮落沒有一點抗爭的跡象。在底層文學中,類似的作品很多,它們缺乏堅實的敘事邏輯,不顧人物的內在掙扎與精神變遷,缺乏一種對底層現實困境的真切反映,沉浸于對人物性格的極端化描寫,把殘酷、苦難與墮落推向極致,給讀者展現一種“奇觀”,而不太體驗底層人物的日常生活常態,“寫‘男底層’便是殺人放火、暴力仇富,寫‘女底層’便是賣身求榮、任人耍弄,不僅人物命運模式化,故事情節粗俗化,而且人物性格也是扁平的,一律大悲大苦,凄迷絕望,鮮有十分豐饒的精神質感。”②這是因為對底層人物那種極端化與絕對化的“奇觀”式的生存狀態的表現是相對容易的,因為它蘊含著先在的道德判斷,作者不太需要進行深入的內在精神世界的挖掘。而日常生活的呈現需要作者的想象力與理解力,需要對生活的肌理及其內在的發展邏輯有扎實的推進,對人物內在精神需求進行精細摹寫與展示,把人物心靈世界的豐富性與復雜性揭示出來,讓生活自身呈現人物的命運,而不能僅憑故事的精巧與奇詭來推動小說的演進。正如有的論者指出:“在當前關于底層生活的小說中,大多作家關注的是社會、經濟、政治等方面的問題,卻鮮有見人對底層人的心靈世界進行深入挖掘與呈現。而關注人的心靈,正是作家獨擅勝場、應該大顯身手的地方,在這方面,我們的一些作家做得還很不夠,他們仍只限于粗線條地勾勒,或者寫作‘問題小說’,還沒有能夠真正進入底層人的內心。”③在“苦難”成為底層敘事關鍵詞的底層文學中,以日常生活為核心的底層敘事就有了別樣的意義。畢飛宇的《推拿》呈現了這種意義。
二
第八屆茅盾文學獎給《推拿》的頒獎詞中有“在日常人倫的基本狀態中呈現人心風俗的經絡”這樣一句話,可以說很好地概括了小說的藝術特征之一,那就是在日常生活中講述故事,在日常生活中呈現人物,在日常生活中提升境界。而對日常生活的描摹與展現,即在于對世態人情的深入洞察。畢飛宇曾說:“對小說而言,世態人情是極為重要的,即使它不是最重要的,起碼也是最基礎的,這是一個基本的東西,是小說的底子……我覺得世態人情是一個不可或缺的拐杖。這根拐杖未必是鋁合金的、未必是什么高科技產品,它就是一根樹枝。有時候,就是這個不起眼的樹枝,決定了我們的行走……任何時候,小說只要離開了世態人情,必死無疑。”④緣于此,畢飛宇不是以居高臨下的同情眼光來打量那生活在現實邊緣的底層人群——盲人推拿師,把重點放在“日常生活”而不是“底層苦難”上,家庭、股票、房子、戀愛、結婚、以及“沙宗琪推拿中心”里糾結纏繞的世態人情。通過對他們在日常生活中敏感、細膩、繁復而又獨特的內心感受的敘述,讓讀者看到他們正常的人生,體會到他們在現實生活中的無助與無奈、痛苦與悲傷,同時也感受到他們的夢想與尊嚴、甜美與幸福,以及他們在黑暗世界中相濡以沫的情懷。畢飛宇呈現出了那個底層人群世界鮮為人知的曲折、隱秘與幽微,同時,我們還可以體會到作者那種最大程度地貼近盲人內心世界,盡力在黑暗世界中提煉光芒的努力。由此,盡管《推拿》給我們呈現一個陌生的世界,但我們不會對此產生一種“奇觀”感,而是一種日常生活的自然流露。
《推拿》沒有底層敘事中那種常見的奇異跌宕的情節與強烈尖銳的矛盾沖突,作者對筆下的人物不是“哀其不幸”也不是“怒其不爭”,只是以一種平和的理解與寬容,在緩慢的敘事節奏中把他們呈現在讀者面前。畢飛宇采用一種屏風式的結構,讓王大夫、沙復明、小馬、都紅、小孔、金嫣、徐泰來等一個個出場,在一個個人物的出場中,一幅“盲人推拿師群像圖”也就在我們眼前徐徐展開。在展開過程中,畢飛宇又設置多種關系把相關人物勾連起來,最后在尾聲中又把全部人物匯集在一起而收束全篇,小說結束了,“盲人推拿師群像圖”也在我們腦海中清晰地立了起來。他們每個人都有自己鮮活的形象,他們的形象都是在內在的生活邏輯中推演出來的,而不是象征符號的概括,更不是“奇觀”的展示。我們可以看到主要人物王大夫是這樣呈現在我們面前:他對“家”充滿著復雜的情緒,親密又疏離,他在“對不起”父母的心態中長大,而作為補償的弟弟,王大夫雖也嫉妒他,但卻很快轉化為對他的溺愛。弟弟結婚時不希望他回去參加婚禮,怕影響形象,他賭氣匯款兩萬元,并決定與弟弟斷絕關系。然當他帶著女友回家后,便立即原諒了他。后來不成氣的弟弟又欠下賭債,王大夫本想不管,但他最后還是決定替弟弟還債,并獨自面對債主的威逼。但最后帶錢回家看到弟弟那種無所謂的態度及債主那種冷靜的逼壓,他用菜刀自殘以表達自己的憤怒以及心酸、痛苦與掙扎。此時,王大夫那種有情有義、寬容、血性、擔當又不失匪氣的形象便浮雕般地凸現出來。這種凸顯沒有發生在極端的環境中,也沒什么你死我活的沖突,一切都在繁雜的日常中展開,彌漫著日常氣息。金嫣在偶然間聽到泰來的故事便千里追尋心中的愛情,而她來到泰來身邊后表達愛情的方式也是日常的。她很希望泰來能親口對她說“我愛你”,但在得知泰來的自卑后,還是她說出了“我愛你”。都紅的自尊與獨立,小馬的純粹與癡迷,張一光的荒唐,沙復明的執著,張宗琪的自閉,小孔的潑辣,季婷婷的寬慰,等等。他們那鮮活而獨特的形象毫無例外都是在日常的疼痛與歡欣中站立在讀者眼前。當我們讀完小說后,腦海里異常清晰的是他們那種“人”的形象,而不是“盲人”形象。把這個處于現實生活邊緣的底層人群作為“人”來寫,而不是作為“盲人”來寫,讓他們在正常人的日常生活中演繹自己的平凡人生,而不是在他者的眼光中呈現黑暗世界的另類“奇觀”,這是《推拿》中不動聲色卻奠定大局的基調。
日常生活的描寫關鍵在于細節的刻畫。從《哺乳期的女人》到《平原》,我們可以看到畢飛宇是一位在細節刻畫中長袖善舞的作家。但《推拿》對他來說仍是一種挑戰,因為他要面對的是一個盲人的世界,從盲人感受世界及表達對世界的認識來看,對一個正常人的表達來說是一種局限,這種局限對呈現細膩綿密、且與敘事對象的內心世界相契合的細節來說,無疑是一種障礙,然也正是這種障礙考驗著作家的藝術功力及其作品所能抵達的境界。畢飛宇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這種障礙,他那種在細節處見功力的手段在《推拿》中展現得異常精彩和結實。其中,心理描寫最為精妙,他施展開對人物心理的大力“推拿”,把握住人物心理經絡中最敏感的部位,推、拿、提、捏、搓、揉,乃至不惜撕裂,把盲人沉默的內心展現得纖毫畢現,把那黑暗的世界呈現得格外豐饒。
其最精彩之處是小馬在孤獨中冥想:“小馬整天抱著這臺老式的時鐘,分分秒秒都和它為伍。他把時鐘抱在懷里,和咔嚓玩起來。咔嚓去了,咔嚓又來了。可是,不管是去了還是來了,不管咔嚓是多么的紛繁,復雜,它顯示出了它的節奏,這才是最緊要的。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它不快,不慢。它是固定的,等距的,恒久的,耐心的,永無止境的。”“小馬就此懂得了時間的含義,要想和時間在一起,你必須放棄你的身體。放棄他人,也放棄自己。這一點只有盲人才能做到。健全的人其實都受控于他們的眼睛,他們永遠也做不到與時間如影隨形。與時間在一起,與咔嚓在一起,這就是小馬的沉默。”小馬在孤獨中尋到了一種理解時間、理解世界的方式,他對時間的感知已經比健全人更加深刻。時間,是日常生活的基本內容,而對少年小馬來說,他的日常生活就是理解時間與世界的關系,他在這種對“咔嚓”聲的想象與感知中,枯燥與沉寂變成了一種遼闊與博大,這是一個真實的世界,也是一個超越的世界。其他的細節描寫也同樣精彩,比如王大夫回家替弟弟還賭債時,看到弟弟也在家等他,“王大夫的血當即就熱了起來,有了沸騰和不可遏制的跡象”。拿起菜刀,在“規矩”的逼債面前,在自己身上劃了兩刀,畢飛宇連用四十個短促的、連續的、斬釘截鐵的,猶如進入無物之陣的“王大夫說”來呈現王大夫那血性的形象。再比如,小說中描寫王大夫和小孔抽空“相好”后穿衣服的細節,如果盲人不是按通常的習慣和次序按部就班地放衣服,他們的生活次序就會變亂。這看似可有可無的一筆,卻有力表現了盲人愛的艱難,日常生活的艱難。這些細節描寫顯示了作家對盲人日常生活精細入微的洞察力與想象力。
在眾多的底層文學敘事中,鮮有《推拿》這樣的作品在人物的日常生活細節中花費這么多筆墨,因為瑣碎繁雜的日常比那戲劇化的場面和極端化的想象更難把握。這來自于作家對日常生活的理解,畢飛宇筆下的日常生活,是有溫度、有氣息、有血有肉的,有光澤度、有尊嚴感的。“畢飛宇在《推拿》中寫出了盲人對溫暖對尊嚴尤其是對尊嚴的強烈渴求,這集中體現在都紅身上。當她的大拇指受傷后,認為自己再也不能做推拿了,她不顧別人的好心勸告及老板沙復明愛情的挽留:“不能欠別人的。誰的都不能欠。再好的兄弟姐妹都不能欠。欠下了就必須還。如果不能還,那就更不能欠。欠了總是要報答的。都紅不想報答。都紅對報答有一種深入骨髓的恐懼。她只希望赤條條的,來了,走了。”尊嚴書寫,是理解《推拿》的一個關鍵詞,也是畢飛宇在《推拿》中竭力表達的一個主題:“我一直渴望自己能夠寫出一些宏大的東西,這宏大不是時間上的跨度,也不是空間上的遼闊,甚至不是復雜而又錯綜的人際。這宏大僅僅是一個人內心的一個秘密,一個人精神上的一個要求,比方說,自尊,比方說,尊嚴。”⑤這種對尊嚴的理解,是畢飛宇建立在對世間生命理解的基礎之上:身處社會底層的盲人也是人,也需要正常人的尊嚴,他們不是我們窺視、同情、憐憫的對象,他們是我們理解、尊重的對象。看待他們應該是如小說結尾所說的那種“最普通的、最常見的、最日常的那種目光”。正是用這種目光看待那些處于社會底層的盲人,畢飛宇在小說中有的是體貼和理解,同時,也沒有拔高他們,更沒有為他們唱勵志的贊美詩。因為他對他們有著清醒的認識,能認識到作為盲人的局限。這是一種誠實而嚴肅的寫作態度,這種態度是對對象的尊重,也是對自己的尊重。這種態度能使作品與底層文學中那些“傳奇故事”區別開來。
毫無疑問,盲人是這個時代最底層的底層,在那些熱鬧的媒體中,我們很少看到他們的身影、聽到他們的聲音,即使偶爾看見,也大多是可憐與苦難的符號。他們是我們社會的盲區,基本上消失于我們的世界之中。然而,在《推拿》中,我們不會感受到那種苦難的場景,不會以為他們是在底層苦苦掙扎的人群。這同樣是因為作者的寫作態度。畢飛宇在《推拿》中遠離了自上而下的同情和高高在上的悲憫,他展現在我們眼前的是一個正常人的世俗世界與平凡人生,他用其敏捷的心智和平等的眼光,給我們描繪了黑暗世界的光亮和日常生活的尊嚴。而這種寫作態度,這種觀察世界的眼光則能夠為那些以農民工、下崗工人、失學少年、拾荒者、發廊女或其他類型的殘疾人等同樣身處社會邊緣的底層人群為敘事對象的底層敘事提供了一種值得借鑒范式,這個范式的核心就是從“奇觀”回到“日常”,給敘事對象以平等、理解和尊嚴。我們不否認同情和憐憫,但要警惕那種把同情和憐憫當成施舍的心態,因為這直接關系到作家的創作。這是底層文學創作的一個關鍵問題,也是不斷推延的中國當代文學的一個關鍵問題。
如果說新世紀以來的底層文學有“知識分子立場敘事”“階級立場敘事”“民間立場敘事”三種敘事向度,那么《推拿》為我們提供了第四種敘事向度,那就是“人性立場敘事”。畢飛宇在《推拿》序言中說:“我們就這樣處在飛奔的路上,帶著我們的表情。我一點也不擔心風馳電掣,——再快的速度也不能把我們的表情扔出窗外,因為表情在我們的臉上。它從容,鎮定,最終會回溯到我的心靈。”可以把畢飛宇所說的“表情”理解為平等和尊嚴,這也就是“人性立場敘事”的關鍵詞。盡管《推拿》在藝術上還不是很完美,小說書寫的盲人感知到底還是大多可以推斷出來的常人常情,還是缺乏那種特殊經驗所具備的穿透力,有輕微的矯情與隔膜之感,但這不是畢飛宇才華的限制,而是每一個正常人自身的限制。但畢飛宇畢竟用他的睿智和技藝給我們展現了一個豐饒的黑暗世界,在平淡中可見動人,在世俗中顯現溫文爾雅,避免了把這個底層人群寫得扁平化,而是寫出了這個底層群體生活內部的各種真相,及他們的生存意志和精神稟賦,激活了他們內心深處尊嚴意識的同時,讓他們在精神上獲得了某種完整。同時,作者還擺脫了那種底層文學中常見的過度冷漠甚至尖刻的敘事,字里行間散發出人性的溫暖。而關于“平等”“尊嚴”則不僅僅是一個寫作問題,更是一個現實問題,因為我們國家身處底層的人民有數以億計。因此,《推拿》對正在進行的底層敘事來說有其不可忽視的價值。
注 釋
①白浩:《新世紀底層文學的書寫與討論》,《文藝理論與批評》2008年第6期。
②洪治綱:《底層寫作與苦難焦慮癥》,《文藝爭鳴》2007年第10期。
③李云雷:《2007:底層文學的理論與實踐》,《文藝理論與批評》2008年第1期。
④畢飛宇:《文學的拐杖》,《雨花》2007年第 11期。
⑤畢飛宇:《〈推拿〉的一點題外話》,《當代作家評論》200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