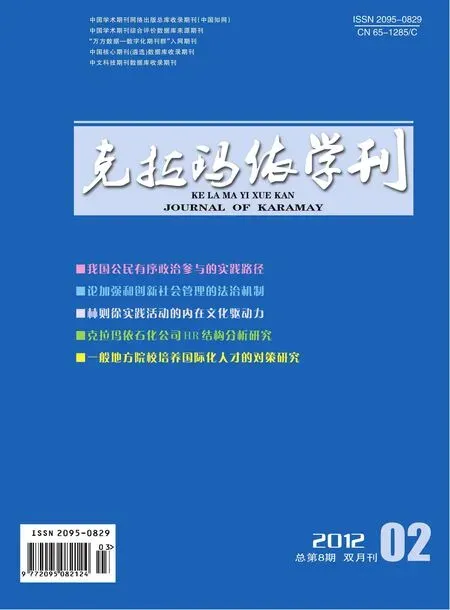論《竇娥冤》的思想傾向及其悲劇價值
荊連蓮
(獨山子第一中學,新疆獨山子833600)
我國元代偉大戲劇家關漢卿創作的《竇娥冤》,堪稱元雜劇之極致。本文從劇作的思想傾向與悲劇價值兩方面來透析作品,揭示出作品的真正意義所在。
一、《竇娥冤》的思想傾向
《竇娥冤》是關漢卿在東海孝婦的民間傳說和當時有關戲劇創作的基礎上,結合元代的社會現實,寫出的一部激動人心的悲劇。《竇娥冤》的思想傾向主要是通過主題思想、審美理想和作家的男權本質三方面體現出來的。
(一)《竇娥冤》的主題思想
對于《竇娥冤》的主題思想,論者多是從對黑暗勢力的揭露、批判和對竇娥反抗精神的肯定、歌頌兩方面來闡述的。對于前一方面,筆者持相同的觀點。雖然關漢卿并不認為整個吏治黑暗,因為還有“圣主”的好官,但是作品中涉及官吏枉法、衙門冤屈好人、草菅人命、地痞無賴猖狂橫行、高利貸盤剝盛行,這些卻都是元代存在的社會現象。所以說,該劇對黑暗勢力的揭露和批判是異常尖銳的。“衙門自古向南開,就中無個不冤哉”就深刻揭露了當時的官吏昏聵、統治黑暗。楚州太守桃杌便是集貪官、兇官、昏官于一身的典型代表。他的做官原則是“告狀來的要金銀;若是上司當刷卷,在家推病不出門。”這哪里是秉公而斷、為百姓辦事?純粹是敲詐勒索,殘害百姓,欺下騙上,為所欲為。他的斷案主張是“人是賤蟲,不打不招”。從桃杌身上,我們窺見了元代吏治的黑暗。也許有人會說,不是有“圣主”的好官肅政廉訪使為竇娥平反冤獄嗎?是的,劇尾肅政廉訪使竇天章是為竇娥冤案昭雪,但這也更恰如其分地揭露了元代吏治的黑暗,因為這是竇娥鬼魂多次爭取而來的。作為“隨處審囚刷卷,體察濫官污吏”的肅政廉訪使,當他拿起竇娥冤案的文卷,看到“一起犯人竇娥,將藥致死公公。……”還沒細看,見“與老夫同姓;這藥死公公的罪名,犯在十惡不赦,俺同姓之人也有不畏法度的。這是問結了的文書,不看它罷,將這文卷壓在底下,別看一宗咱。”這哪是“隨處審囚刷卷,體察濫官污吏”?如果遇到同姓就不看,如果“問結了的”也不看,那他還有什么可“審”可“察”的呢?要不是竇娥的鬼魂三番兩次將他壓下的文卷重新翻上來,并在他面前訴說冤情,那么,這樁冤案恐怕要永遠石沉大海了。可見,這竇天章也是昏庸無能的。從整個劇本來看,表現的都是作者對元代吏治的批判和不滿。
劇本揭示元代吏治的黑暗是事實,但是有些論者說《竇娥冤》表現的是對封建制度的反抗,竇娥因此具有反抗精神。對這一說法,筆者認為對作品思想境界有拔高之嫌。因為關漢卿受時代所限,不可能把人民的悲慘遭遇歸結到制度問題,他也不可能達到這個思想高度。
三折【一煞】你到是天公不可期,人心不可憐,不知皇天也肯從人愿。做甚么三年不見甘露降,也只為東海曾經孝婦怨,如今輪到你山陽縣。這都是官吏每無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難言。
一句“這都是官吏每無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難言”道出了作者對元代吏治的不滿。作家憎恨貪官污吏,憎恨他們所把持的官府對人民的殘酷迫害,但他并不能擺脫封建統治階級的思想束縛,他只是希望在封建法制的范圍內,改良社會弊端,而并沒有設想過用革命暴力去推翻黑暗的統治。關漢卿有這一政治態度一點也不奇怪。馬克思主義認為:“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這就是說,一個階級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物質力量,同時也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著物質生產資料的階級,同時也支配著精神生產的資料,因此,那些沒有精神生產資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統治階級支配的。”①關漢卿在《竇娥冤》中所反映的政治愿望,恰好說明“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著這位封建社會的下層知識分子。在封建社會里,農民和其他下層群眾深受貪官污吏及其爪牙的壓榨,對這類直接騎在他們頭上的家伙恨之入骨。但是,由于農民的小農經濟的地位和政治閉塞等等條件的限制,他們往往相信皇帝,以為皇帝能夠為他們主持公道,把解除他們冤枉的希望寄托在“奉旨”而來的“清官”身上。所以,關漢卿在《竇娥冤》劇尾安排了肅政廉訪使出現。但劇作《竇娥冤》只是反映出對吏治的不滿,并沒有反映出對封建制度的反抗與否定。
對竇娥的反抗精神,學術界論者多數持肯定頌揚態度。且來讓我們看一些論者對第三折中主人公竇娥被押赴法場時所唱的【滾繡球】的不同評價:“她從罵官府,進而罵天地,她對封建統治者宣揚的一切秩序都表示了否定”;②“竇娥的反抗性格在這里達到了高峰,她所反抗的包括從天地到鬼神,從官府到張驢兒這一切象征的和實際的統治力量,竇娥的這段詛咒標志著她的覺醒,說明她不是對封建社會的個別現象,而是對封建社會的根本秩序開始懷疑”;③“她詛咒世界上的一切,連封建社會中被認為最公正無私的日月、鬼神、天地都否定了”,④于是論定關漢卿塑造了一個“具有強烈反抗精神的英雄人物形象”、⑤一個“敢于面對慘淡人生,同命運決斗的勇士”⑥……然而從作品整體聯系看,女主人公果真否定了天、否定了地、否定了封建制度嗎?筆者認為,當然不是!她既不是反抗封建制度的“英雄”,也不是同命運決斗的“勇士”。她的腦海里根植的是對命運的順從、對公理不公的掙扎、對天地的信任臣服的思想,而天地象征著封建制度。可以說,她是封建社會里自覺地捍衛封建制度的衛士。她處處以封建禮教約束自己,遵循著“三從四德”的規范。她立誓盡心盡力侍養婆婆,全心全意為丈夫守節。她絲毫沒有掙脫命運的打算,她認命了。她對自己三歲喪母、七歲被賣、十七歲成婚、二十歲亡夫的不幸命運已經不抱任何希望了。抵債,童養媳,寡婦守節,向債主盡孝,這些在她的思想里都是對命運的順從,并會盡自己所能去遵循。她認為自己“八字該載著一世憂”,“前世里燒香不到頭”,嚴重的宿命論束縛著年輕的寡婦竇娥。隨著戲劇沖突的展開,她指天罵地,發出悲愴的呼喊。這是一種對現實絕望的呼救,是對自己冤屈的血淚的控訴,是對現實無可奈何的掙扎。這不是什么階級意識的覺醒,而是出于求生欲望的本能抗爭。在這里,她沒有否定天、否定地,相反的,她在掙扎中仍然相信天地的威力,向天地發出了三樁“無頭愿”。這說明她相信正義在天、公理在天、道義在天。混濁人世善惡不分,公道不彰,而唯有頭上“湛湛青天”,才能昭示她的深仇奇冤,其結果是“感天動地”,三樁超自然的誓愿一一實現。因此,如果說竇娥對現實進行過反抗的話,那是生命遭受虐殺前的自發的反抗,是人處于掙扎境況下的本能反應,是含不白之冤無處申訴的絕望的抗爭,是對“復盆不照太陽暉”的黑暗現實的憤怒的控訴,不是對社會和自己的叛逆行為具有理性認識的那種反抗。竇娥冤獄最后的平反昭雪,也是其父竇天章一手完成的,而竇天章在第四折中,以朝廷命官“肅政廉訪使”的身份,手持上方寶劍出場,代表的是封建制度。可見,竇娥依循的仍舊是封建制度,她并不具有反抗精神。試想,如果她不捍衛封建制度,而是一個反封建制度的勇士、英雄,那她被殺的事實也是必然的,她也就無冤可言了。而她感到冤,其實質也是以封建禮教要求自己,以封建禮教捍衛自己的權利,所以,她不是反封建的勇士、英雄。魯迅先生對劉和珍等烈士精神贊揚為“真的勇士,敢于直面慘淡的人生。”他們在向舊世界的沖擊中,被反動派殺害了,他們才是真正的勇士、英雄,他們喊過冤嗎?沒有!而關漢卿為自己的劇本赫然書上“感天動地竇娥冤”七個大字的正名,非常清楚地標示了劇本的主題,同時也顯示了人物性格的社會性質。竇娥與劉和珍等反抗人物絕非同一類型。只有像竇娥這樣一個恪守封建道德規范,最后又被這個畸形的社會殺害了,才是感天動地的冤!就像竇娥的鬼魂向父親提出質問一樣:我走的路,哪一步不是遵循了王法的規范,家法的訓飭呢?得到的結果卻是:
四折【雁兒落】我不肯順他人,倒著我赴法場;我不肯辱祖上,倒把我殘生壞。
【梅花酒】本一點孝順的心懷,倒做個惹禍的胚胎。
在這血淚凝成的控訴中,多么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統治的虛偽性!多么明顯地揭示了竇娥“感天動地冤”的真實本質!一個虔誠的恪守那個社會一貫標榜的道德規范和法律規范、思想行為從未越過雷池一步的弱女子,一個善良、貞孝且又剛直不阿的苦命寡婦,一個對生命只知道奉獻、不求所取的小人物,結果反被扼殺了。這才是冤,天地奇冤!這是冤的實質、悲慘的真諦,也是《竇娥冤》為悲劇的體現。
《竇娥冤》正是通過竇娥被封建禮教、貪官污吏、流氓惡痞戕害致死的悲慘遭遇,再現了元代社會真實黑暗的一面,揭露和批判了吏治制度的腐朽,這是本劇最根本也是最進步的思想內涵。
(二)《竇娥冤》的審美理想
《竇娥冤》的另一個思想傾向體現在關漢卿對戲劇創作的審美理想上。這主要體現在作家安排三樁誓言和劇尾竇娥鬼魂申冤的幻想節上,體現了美與善的結合、虛與實的結合、悲與喜的結合。
一切文藝作品都是一定生活在作家頭腦中的反映,作家的世界觀對作品的思想傾向有很大影響。人類總是在斗爭中進步成長,與自然界斗爭,與不合理的社會現象斗爭。斗爭失敗了,便產生了悲劇。有正義感的作家,相信自己的斗爭方向是正確的,斗爭結果必定是勝利的,所以在暫時失敗后,仍能讓讀者看到未來勝利的曙光。《竇娥冤》是一部現實主義作品,它忠實于生活的現實,讓主人公擔當非擔當不可的悲劇命運,深刻逼真地反映出現實生活的畫面。作者不愿讓竇娥的死毫無聲息、毫無希望、毫無震撼力。所以,作者在創作《竇娥冤》中又帶有浪漫主義色彩,將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有機地結合在一起,突出劇作的感染力。《竇娥冤》中關于三樁誓言和鬼魂告狀的描寫,就是浪漫主義手法的具體運用。在第三折中,竇娥的控訴表現了她對命運的不滿與憤慨、對社會秩序的不滿與憤慨:
【滾繡球】有日月朝暮懸,有鬼神掌著生死權。天地也,只合把清濁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盜跖顏淵:為善的受貧窮更命短,造惡的享富貴又壽延。天地也,做得個怕硬欺軟,卻元來也這般順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為地?天也,你錯勘賢愚枉做天!哎,只落得兩淚漣漣。
之后,竇娥又提出了血濺白練、六月飛雪、三年大旱三樁誓言,以示自己的冤屈、不滿及憤慨,這就把竇娥的委屈含冤的掙扎、無奈的精神提高到感天動地的高度。
【耍孩兒】我不要半星熱血紅塵灑,都只在八尺旗槍素練懸!
【二煞】若果有一腔怨氣噴如火,定要感得六出冰花滾似錦!
【一煞】你倒是天公不可期,人心不可憐,不知皇天也肯從人愿。做什么三年不見甘霖降,也只為東海曾經孝婦怨;如今輪到你山陽縣!這都是:官吏每無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難言。
這三樁誓言一一實現,寫得很有層次。鮮血飛濺潔白的布練,是直觀的,色彩強烈,表現出竇娥冤氣沖天;繼而六月飛雪,頓時千里冰霜,萬里雪飄,掩蓋了竇娥的尸體,更彌漫了冤的意味、悲的氣氛,說明天地也給予表現竇娥冤屈的事實和充滿同情的悲涼,不忍竇娥露尸于野;三年大旱則更是把感天動地的力量擴大延伸,那不僅是希望個人的冤屈得到伸張,而且還希望上天能夠懲治邪惡。竇娥的冤屈已經直指貪贓枉法、草菅人命的昏官污吏。這些是作者浪漫主義的想象,然而他卻表現出了被壓迫人民足以驚天地、泣鬼神的力量,來展示其不滿、無奈、憤恨的弱小掙扎。這種浪漫主義手法不僅進一步豐富了竇娥的形象,而且寄托了作者的理想,反映出人民群眾對吏治的憤怒。這也是一種虛實結合、符合廣大人民群眾的心愿、使人的心境達到一種憤怒力量的釋放,表現了關漢卿的一種審美理想。
另一個表現審美理想的是作家安排的竇娥鬼魂申冤的第四折。對此,有些論者認為是敗筆。筆者認為,《竇娥冤》的結局反映了劇作家懲惡揚善的善學理想,是戲劇情節發展的必然。縱觀關漢卿的戲劇創作,總有一個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美好結局。其戲劇矛盾沖突的結果,往往被歸到善惡兩種力量的斗爭。在《竇娥冤》中,“為善的受貧窮命更短,造惡的享富貴又壽延”,在作家看來,這種善惡顛倒的現象是極不公平的。于是作家讓竇娥的鬼魂“剔燈”、“翻交卷”,在父親面前申訴了冤情。竇天章在審案時,張驢兒不承認喝了毒藥,作家又讓鬼魂出場,與張驢兒對質。正是在竇娥鬼魂的“折辯”下,才使這樁冤案得以澄清[1]。劇本的這些矛盾沖突的展開和斗爭的結局的設置,已經明顯地看出作家的審美的傾向:正義必勝,邪惡必懲。
同時,《竇娥冤》的鬼魂出場的結局反映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心理和觀眾的審美習慣。元朝統治下的中國,社會太黑暗了,政治太腐敗了,需要揭發,需要控訴。但誰來揭發?誰來控訴?在劇作家看來,非“鬼魂”出場不可。因為作為“現實主義的戲劇作家關漢卿,冷靜地觀察到人民在無可奈何之中,只能把申冤的意愿寄托在上天與鬼魂”身上,同時,作為浪漫主義的戲劇作家關漢卿,更強烈地感覺到“神鬼不容”、人神共怒的藝術處理,“最能體現人民要澆清天下冤枉,殺盡天下濫官的意愿”,⑦于是因勢利導,自然而然地創造出竇娥“鬼魂”重現、申冤報仇的非現實情節場面。這些非現實情節場面的藝術創作,是劇作家依據生活邏輯,通過想象或綴合而擬構的“現實生活中并非實有、而在情理中又必然存在或應該存在的人生圖畫”,⑧它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人們視野方面的缺憾,使人能“在頭腦中見到無法親自觀察、體驗的事物和情景”⑨因而能以一種藝術的真實為讀者所理解,而不用是否符合科學的精神去批判它。劇中鬼魂的出現,引導和推動了劇情的發展,符合我國戲劇觀眾的那種“含淚的笑”的心理愿望。王國維在《〈紅樓夢〉評論》第三章《紅樓夢之美學上之價值》中談到我國悲劇之所以用這種“含淚的笑”的結局,是因為“吾國人之精神,世間的也,樂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戲曲小說,無往而不著此樂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終于歡,始于離者終于合,始于困者終于亨,非是而欲饜閱者之心,難矣”。⑩可以說,王國維這句話揭示出《竇娥冤》鬼魂結尾的真諦,表現了一個民族獨特的心理要求。在元代的現實生活中,像竇娥這類人物是決不可能獲得像戲劇中那樣大快人心的圓滿結局的。理想與現實發生矛盾,于是作家就在戲劇末尾,用這種超現實、超自然的力量,揚善懲惡,以實現在現實中無法實現的理想。由此我們可以認識到,關漢卿塑造竇娥鬼魂的意圖,不是在引導人民把希望寄托在虛幻的鬼魂身上,也不僅僅是為著生前的斗爭,而是通過放任鬼魂按人之常情行事,促成這一冤獄的平反,以表達作家懲惡揚善的正義必勝、邪惡必懲的審美理想,由于其符合廣大人民的心愿,在一定程度上能使觀眾得到心理的滿足。在這種合乎生活邏輯和人民愿望的基礎上,在適當的場合讓鬼魂上場,是無可厚非的,甚至是創作必需的。觀眾和讀者決不會相信那是宣揚宗教迷信的陰魂,而總是愿意認為那是活生生的報仇雪恨的人。正如魯迅先生對《哈姆雷特》中的鬼魂形象所評價的那樣:“將來呢,恐怕也未必有人引《哈姆雷特》來證明有鬼,也未必有人引《哈姆雷特》而責莎士比亞的迷信……”(《且介停雜文·以眼還眼》。可見,作品中安排的三樁誓言與鬼魂申冤的幻想情節,體現了美與善的結合、悲與喜的結合、虛與實的結合,表現了關漢卿的審美理想。這無論在現在還是將來,都能給人以啟示、以鼓舞。[2]
(三)關漢卿的男權主義思想本質
《竇娥冤》講述的是封建社會中一個弱女子被黑暗勢力所吞噬的故事。在故事背后,劇作家讓觀眾與讀者從內心深處自覺地捍衛“三從四德”的封建禮教,自覺成為封建禮教的捍衛者。他的男權主義思想在作品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展現。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指出:“母權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失敗。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權柄,而妻子則被貶低,被奴役,變成丈夫淫欲的奴隸,變成生孩子的簡單工具了。”婦女的這種被貶低、被奴役的社會地位,幾乎被排斥于社會之外,她們受夫權、父權、政權的支配,理學家又在他們身上套上了貞節的枷鎖,而所有這一切的封建理念,也影響著關漢卿的思想,可以說,在關漢卿的思想里有著根深蒂固的地位,這在《竇娥冤》里也有具體的體現。竇娥只是關漢卿傳播他的這種封建禮教思想的媒介,他在借竇娥之口說出封建社會男權至尊無上的地位。
《竇娥冤》主要描繪的是封建社會里一個再嫁之婦可能遭受到的、殘酷的、無人性的、血淋淋的現實。這里再嫁之婦不是“我一馬難將兩鞍鞴,想男兒在日,曾兩年匹配,卻教我改嫁別人,其實做不得”的竇娥,而是在面對死亡和再嫁的抉擇時,選擇了后者的蔡婆婆。竇娥所遭遇的一切,都是因為蔡婆婆有了再嫁之心,她僅僅是替婆婆受過,替婆婆有再嫁意識而受懲罰。在張驢兒父子上門之時,竇娥曾對蔡婆婆說:“婆婆,你莫要背地里許了他親事,我也連累做不清不潔的。”在張父與蔡婆婆發生感情之后,竇娥曾嘲弄蔡婆婆并說婆婆“可悲!可恥!”“多淫奔,少志氣”。在那個講求“三從四德”的時代,作為一個兒媳婦,她是不能也不該對婆婆說出這樣嘲弄近似破口大罵的不孝言語,而“冤屈有天大”的弱女子竇娥卻做到了。她那具有驚心動魄的言語產生了驚心動魄的力量,原因就是作者賦予了她至高無上的封建力量。她時刻擁有這個力量,也步步遵循這個制度,她是忠實的捍衛者和信徒,因而才擁有了嘲弄、辱罵婆婆的資本。當她在公堂上被“打得我肉都飛,血淋漓”時,當她呼號“這無情棍棒教我捱不的”時,當她埋怨“婆婆也,須是你自作下,怨他誰”時,哪個觀眾都會痛感到,那個社會再嫁的可怕和不可為。“勸普天下前婚后嫁婆娘每,都看取我這傍州例”宣揚的正是對有再嫁之心的人的懲罰警示!這不能不說,作家關漢卿有深刻的封建道德禮教的思想觀念。實際上關漢卿是借竇娥之口來履行他夫權的權利,借竇娥形象道德說教和道德宣傳,再現其男權主義思想。
在竇娥之魂在向竇天章陳述冤屈的時候,竇天章明明知道蔡婆婆沒有丈夫,但聽說女兒犯了“藥死公公”的罪行,卻依然是怒斥女兒的十惡不赦。這不是作者疏漏所致,實際上是體現了作者對父權的維護。因為竇天章是竇娥的父親,所以竇娥的鬼魂才有機會在父親面前辯白自己的冤屈,但這個機會也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竇娥的鬼魂再三“翻案卷”才有了控訴的機會,而在這個機會的獲得前還得受父親的斥責、謾罵。“我當初將你嫁與他家呵,要你三從四德:三從者,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四德者,事公姑,敬夫主,和妯娌,睦街坊。今三從四德全無,鏟地犯了十惡大罪。我竇家三輩無犯法之男,五世無再嫁之女;到今日你辱沒祖宗世德,又連累我的清名。你快與我細吐真情,不要虛言支對。若說的有半厘差錯,牒發你城隍祠內,著你永世不得人身,罰在陰山永為餓鬼。”其實這段話也是作者在借竇天章之口,表明自己的婦女意識,維護其父權意識。因為他有關于“三從四德”的十分強烈的表述欲望,他已經不滿足于借竇娥之口來表達他的男權意識,而是急于要用自身的男性性別來壓制女性。只有這樣,他才能痛快淋漓地剖析自己的心聲,所以作者才設計竇天章怒斥竇娥的情節,借竇天章之口發表他的男性宣言。
桃杌不分青紅皂白對竇娥的一頓毒打這一情節,實際上也是對封建父權的維護。在封建社會里,“呈控子孫忤逆不孝,司法機構是不會拒之,不受理的,同時,也不要求呈控人提供證據”,“如果法官追問子女究竟誰是誰非,便等于承認父母的不是,而否認父權的絕對了”。忤逆不孝,父權制官府都不可能去核實,甚至誰是誰非都不會追問,更不用說“藥死公公”的罪名了。這也是竇娥故事在流變的過程中,女主人公無一例外地都被官府處決的原因。所以在蔡婆婆沒有出面澄清與張父的關系時,竇娥挨桃杌的拷打是正常的,也是合理合法的,因為他們都是父權制的代表。父親將七歲竇娥抵于蔡婆婆還債,也流露出作者對封建社會至高無上的父權的肯定。父親聽女兒申辯的原因,也只是因為他在意竇家的名聲,這不能不說是竇娥的悲劇。張驢兒捏造了這個殺公公的罪名,完全揭示了竇娥作為父權制下女性的悲慘命運,也在無意識中自然流露出劇作者的男權思想本質。
在男權制度下,張驢兒父子有恃無恐的表現不僅僅因為他們是潑皮無賴,還根源于其性別優勢。在封建社會的男權制度下,男性做什么都是天經地義的、合情、合理、合法的,特別是在欺凌、壓迫婦女這一方面,似乎他們有了通行證、免死牌。就像凱特米利特在《性的政治》中所說的,盡管“女性類似階級的地位在階級的范圍內極易產生混淆”,但“主要的社會和政治區別,其基礎……不是財富和地位,而是性別”。張驢兒對竇娥的苦苦相逼,從這一個角度來說,實際上是男權社會中,男性階級對女性階級的一種支配心理與占有心理。男性之間更是結成同盟,自覺地維護男性欺凌女性的特殊權利。像張驢兒行賄于桃杌,以蔡婆婆的財力與物力,完全有可能比張驢兒更有機會買通官府,而使張驢兒被懲罰。但是,事實卻恰恰相反,竇娥受懲罰死了,張驢兒卻越活越滋潤了,這不能不讓讀者深思與反省:究竟是什么力量使竇娥走上了死亡的道路呢?這不能不說封建社會男權在作怪,是男權才讓竇娥蒙上了不白之冤。可見,封建社會中男權的強大和不可忤逆性。竇娥作為一個弱小的女性,在那個社會里只是受男性支配、玩弄的一個“物品”罷了。
竇娥的悲劇,表面上看是竇娥拒絕再嫁張驢兒引起的,但實際上蔡婆婆選擇再嫁張父才是悲劇的源頭。如果蔡婆婆自己不心甘情愿地再嫁,不與張父產生感情,那么張父不會死,張驢兒也不會以誣賴竇娥來挾制竇娥,竇娥也不會上公堂,更不會走上死亡之路,蒙了不白之冤。這一切的一切,都是因為蔡婆婆再嫁張父引起的。作者借竇娥替婆婆受再嫁引起的罪及所受的懲罰,來勸告警示世間的女子:“勸普天下前婚后嫁的婆娘每,都看取我這般傍州例”。《竇娥冤》的基本矛盾不再是竇娥與官府間,也不再為竇娥與張驢兒間,而是竇娥與蔡婆婆之間一個要嫁一個要守的基本沖突。如果兩人都守或都嫁,那便不會有悲劇發生了。正是因為蔡婆婆要嫁竇娥要守,竇娥才受了不該受的苦,有了感天動地的冤情。作者關漢卿闡述的是一個再嫁之婦所引起的感人肺腑的悲慘故事。“感天動地竇娥冤”,實際是作者宣揚男權思想的武器,體現男權思想的本質。
二、《竇娥冤》的悲劇價值
“即列于世界大悲劇中亦無愧色”?的《竇娥冤》有它獨特的悲劇價值。魯迅先生曾在《魯迅全集》第一卷中說過:“悲劇將人生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這句話包含著悲劇本質的精髓:一是悲劇表現的是“人生有價值的東西”;二是這種“人生有價值的東西”發展最終極的是“毀滅”。他充分強調了悲劇本質精髓,就是通過“毀滅”的終極方式來肯定“人生有價值的東西”。[3]被毀滅的價值越大,其悲劇性就越強,悲劇意義價值所在也就越大。[4]《竇娥冤》中,竇娥的毀滅就是一種感人肺腑的悲涼毀滅,是一種感天動地的無奈毀滅。我們不僅看到了竇娥毀滅的價值,同時也看到了《竇娥冤》作為悲劇存在的價值。
那《竇娥冤》中“人生有價值的東西”是什么呢?從劇作中可以看出,這種有價值的東西就是竇娥這個小人物恪守封建倫理道德規范,對生活充滿希望的不懈追求。當她被父親抵債時,她恪守的是封建父權制度,將希望寄托在丈夫身上,希望過上幸福生活;當丈夫死去,她成了寡婦并遇到張驢兒逼婚時,她恪守的是封建貞孝的論理道德規范,為丈夫守節,為婆婆盡孝,將希望寄托在來世;當發生人命大案時,她恪守的是封建的政權制度,將希望寄托在官府,希望官府可以還她清白。這些希望的實現,從更深層次看,實際上都是對封建制度的遵守和維護。竇娥時刻都把封建倫理道德規范作為座右銘。她為了追求孝道和貞節的倫理道德,最終付出了生命的代價。這實際是竇娥成為悲劇人物的內在原因。在官吏枉法、衙門冤屈好人、草菅人命,地痞無賴猖狂、高利貸盤剝、童養媳制度盛行的外部因素的催化下,封建制度將竇娥一步步推向了死亡,最終將其吞噬與毀滅。這種“毀滅給人看”是拿三樁誓言的實現來展示其冤屈之極至的。它讓人們產生了痛苦、憐憫、悲愴、憤怒的情感,而這種獨特的苦痛情感構成了悲劇的價值。在宣揚遵循孝道貞節的封建社會,而一向也遵循、維護這一倫理道德的竇娥卻被其毀滅了,不能不說冤啊!這才是真正的將“人生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任何一位觀眾,只要真正地被悲劇人物的行動及其崇高精神所吸引,他一定會沿著悲劇作品所設置的方向,將自己的思想情緒和道德判斷傾注其中。當你在為之悲傷、為之悲痛的同時,你的思想情感就會出現一個瞬間超越的感覺。你就會在精神上獲得自由,而且使內在情感和整個精神狀態受凈化。這就是悲劇的價值所在,讓你的情感精神獲得自由、凈化的同時,還要受其感染,終其反思,使物質生活和精神世界升華到一定的程度,陶冶情操。悲劇的價值本質也就在于這種超越性,而《竇娥冤》把這種悲劇價值反映得淋漓盡致。
作為一部有深刻思想內涵的悲劇,《竇娥冤》成功描繪了一幅有著強烈時代精神的社會生活畫面,不愧為認識元代社會的一面鏡子。它的內容是豐富多彩的,情感是悲痛交加的,所展現出的價值是無可估量的。王國維的“即列于世界大悲劇中亦無愧色”的評價是毫無夸張的。
注釋:
①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A].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②北京大學中文系1955級集體編著.中國文學史(第三冊)[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5.
③湖南師范大學中文系古代文學教研室.元明清文學史稿[M].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1986.
④吉林大學中文系中國文學史教材編寫小組.中學文學史稿·元明部分[M].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59.
⑤作家出版社.元明清戲曲研究論文集[C].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
⑥李修生,李真渝,侯光復.元雜劇論集上集[M].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85.
⑦⑧⑨趙澤學.竇娥“魂”解讀[J].黔南民族師專學報,1996,(1).
⑩王國維.紅樓夢之夢學價值[M].北京:東方出版社,1998.
?瞿同祖.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M].北京:中華書局,1981.
?王國維.王國維遺書(第15冊)[M].上海:上海古籍書店,1983.
[1]林啟柱.關漢卿及其《竇娥冤》雜劇的再評價[J].渝州大學學報(社科版),2001,(5).
[2]張麗生.《竇娥冤》與《哈姆雷特》中的鬼魂形象比較[J].鹽城師專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5,(1).
[3]王慶芳.《竇娥冤》的審美價值[J].孝感學院學報,2001,(4).
[4]林化杰,孫宗欣.略論竇娥形象的悲劇價值[J].臨沂師專學報,19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