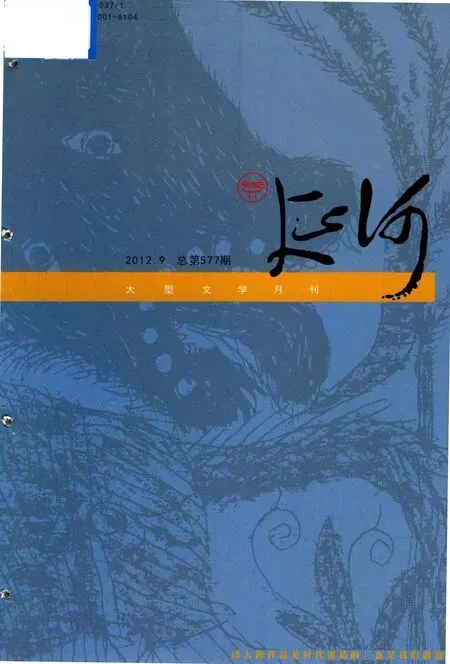沈浩波的詩
沈浩波
飛翔與邁克爾·杰克遜
聽說女人會飛
當男人用狠命的勞作
淬煉她的身體
翅膀就會撐破肋骨
蓬松的羽毛
掠過柔軟的發際
男人是不會飛的
我見過吸食毒品的人
也親自嘗試過
以為自己在飛的男人
活像被人生追殺的逃犯
在邁克爾.杰克遜死后
我補課似的
看了他很多演唱會的影像
并深深為之感染
一個渴望飛翔
并永在試圖飛翔的男人
在他的歌聲和舞蹈中
把嗓音
修改得和天使一樣
把身體
鍛造成一片柔韌的羽毛
但他依然飛不起來
我因此愛他
飛翔一般起舞的倒影
少女賦
如果沒有親身經歷
生活中
細小的常識
往往被我們忽略
比如你家客廳
電視正對面的墻上
高高掛著
你父親的遺像
每次我走進
心里都咯噔一下
為什么要掛在這里呢
輕吻你的耳垂
我問
“我希望父親
能陪我
看看電視
他生前
從不陪我。”
然后
你問我
“你知道為什么
被抽耳光時
鮮血總是從
嘴角流出來嗎?”
我一楞
還真沒想過
“小時候
父親經常揍我
他抽我耳光時
嘴唇狠狠撞擊牙齒
鮮血就會流出來”
黑絲賦
首先是黑絲
然后才是女人的腿
然后才是
被豐腴的大腿
托舉著站立
的女人
醉意來得突然
如同一劍穿心
我還沒有來得及
感受疼痛
便已一頭墜入
那一雙
黑色的絲襪
來成都之前
我將自己
關閉在冬天的房間
看窗外的世界
如同一只螞蟻
看到一頭完整的大象
如果你知道
北京的冬天
近乎殘忍的漫長
一場又一場白雪
差一點就
取消了整個春天
你就不會
對我突然的放縱
感到意外
我說的冬天
不僅僅是天氣
或者
我凍僵的身體
我反復對著
不幸坐到我對面
穿黑絲的女人表白
事實上她幾乎
就是我的一個朋友
“我本來只把你當作女哥們兒
你為什么突然
穿上了黑絲”
如果只說一次
兩次
或者三次
那將意味著
幽默?
調情?
或者挑逗?
可是我說了整整一個晚上
如同一架
肉做的復讀機
這對那個美女
一點也不公平
酒鬼在歌頌
她腿上的黑絲
而黑絲
穿在她的腿上
大腿向上延伸
一直到姣好的臉龐
可是
這跟我有什么關系
再深刻一些
就需要愛情了
而我只是
想表達一些什么
不是情欲
真的不是
清醒使人麻木
理智令人絕望
大酒如春雨
澆灌進
我的胸膛
黑絲如綠韭
在雨水中生長
緊緊
套在
女人腿上
黑色的
春天
成都開滿鮮花
玉蘭賦
當她綻放
天鵝般
托舉著向上
世界
才有真正的花朵
仿佛是從
寒冬的
暮光之獄
出走的
一群修女
潔白的身體
掙脫黑色長袍
迸涌而出
耀眼
如緊張的燈
收斂著
情欲
托舉起
全身的重量
碎片般的心
簇擁著
向上
沉默的歌聲向上
脆弱的靈魂向上
渺茫而凌亂
草籽般的希望向上
一樹白色的玉蘭
開在春天的城市
如同開在
沙漠上
美腿賦
師姐
你潔白
長腿的船槳
輕輕搖曳
將這沉悶的初夏
攪成一池碧波
令我心亂如麻
腳步輕盈
神情莊重
代表神秘的組織
找我談話
我的種種陰謀和罪行
因反動而燥熱的心
被你輕輕
捏在手心
頎長、光潔的雙腿
懸吊在
世界——
你小巧的秋千上
這是屬于你的美腿的夏天
這是屬于我的心亂的下午
你雙腿耀眼的白光
令我不再關心
祖國和我的理想
只想抱住并且親吻
招供出所有同伙和陰謀
當一個可恥的叛徒
以上一切
可惜只是虛構
國家安全局的美人
此番翩然而來
陪一個朋友
找我談件小事
但是師姐
我的情欲
已如不可遏制的海浪
拍打向你美麗雙腿的船槳
更恐怖的是
你不僅勾起了我的欲望
還勾引起了
我按捺已久的
那顆造反的心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
請讓你的組織
派你前來
狂熱的夏天
大白腿的美人
穿上你的裙子
帶上你的手槍
彈孔在我的胸口綻放
鮮血如同火焰燃燒
我在微笑中看到
你潔白的雙腿
如冰雪消融
如你在落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