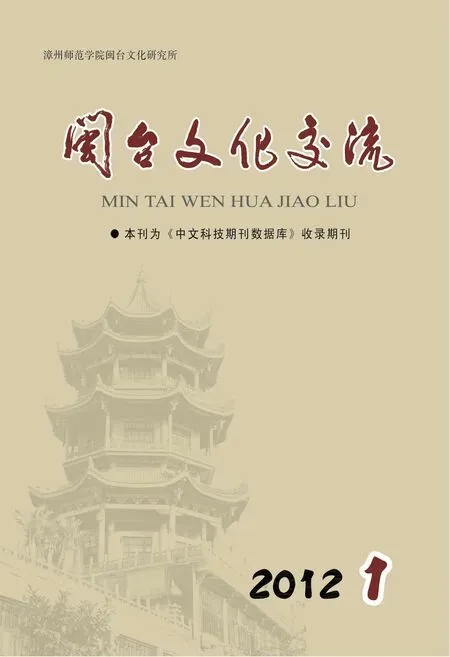經學園地里的一顆大樹——臺灣著名學者林慶彰教授經學研究述評
林祥征
中國是一個文明古國,其光輝燦爛的傳統文化,已經成為人類的寶貴精神財富。隨著時代的進步,人們比任何時候都需要發掘傳統文化的寶庫,以吸取更多的智慧和力量。在寶島臺灣就有一位在經學園地辛勤耕耘并結出豐碩成果的知名學者,他就是現為臺灣 “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研究員、臺北大學古典文獻研究所合聘教授、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兼任教授林慶彰先生,他自1975年跟隨大陸到臺灣的屈萬里教授學習經學起,至2007年12月的三十年間,在經學、目錄學、和文獻學等方面成績卓著,蜚聲中外。出版專著12部,主編編輯55部、翻譯日本經學著作2部、論文285篇。林氏的授業弟子陳恒嵩、馮曉庭二位博士認為三十年是觀察人生成就的重要指標,編成《經學研究三十年——林慶彰教授學術評論集》(臺北:樂學書社2010年10月)一書以諸祝賀。書中收錄經學評論38篇,文獻學評論17篇,媒體報導34篇。附錄一:節錄對林氏著述的評價;附錄二;林氏自述有關治學和經營 《國文天地》的文章;附錄三;林氏著作目錄。該書為林氏三十年來治學的珍貴記錄,也是觀察臺灣學術的一個窗口。
一、有關經學研究的幾個側面
(一)對經學歷史規律的探尋
林氏在研究清初學者的群經考辨中,發現自先秦、兩漢、隋唐、宋元、至明末,在這兩千年的經學發展過程中,每經歷數百年之后,必有一個批判思潮的出現。魏晉時期是對漢代經學的批判;晚唐至北宋時期,是對漢唐經學的批判;晚明至清初,是對宋元新經學的批判。這種每隔一段時期就會出現的批判思潮,都以恢復經典中的圣人真意為最高的準則,并成為經學發展演變的關鍵時期。對這種周而復始學術思潮,林氏稱之為 “回歸原典遠動”。我們有了這種新的認識,對經學史上的問題就可看的更透。唐代韓愈推動的古文運動,其表現形式是文章學的問題,如果看到其實質是 “回歸原典遠動”的一部分,就可認識到其深層的目的在于復興中華文化。清中葉乾嘉考據學派,前人褒貶不一,有人認為是 “中國哲學精神的逆轉”“清代考據學使中國哲學走上歧途”,甚至認為 “是一種無聊的紙上功夫”。如果我們運用林氏的理論,就能明白乾嘉學派對儒家經典的訓詁和考證只是一種手段,探求孔門真義才是其治學的根本的目的。對具有 “回歸原典”運動的明末清初的辨偽思潮也會有更深刻的體認。
林氏 “回歸原典”說是受了孔恩(Thomaskum)1962年出版 《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中的 “新典范”理論的啟發而提出來的,說明林氏研究的開放性,再次說明中外文化交流是促進文化發展的重要一環。林氏還認為從戰國時代到漢初,對經典的注釋很簡單,西漢中葉到東漢很繁瑣;東漢到魏晉很簡單,南北朝到唐朝很繁瑣;宋朝很簡單,元明兩朝又繁瑣。所以整個經學史上對經典的注釋就是簡——繁——簡——繁這樣的循環。這個規律的總結,對我們認識經學史上的注經形態也有所幫助。規律是事物之間的內在聯系,并決定著事物的發展方向。林氏對經學史規律的總結,有助于經學史的研究,也反映林氏宏觀把握能力。
(二)清理經學史的發展脈絡
皮錫瑞 《經學歷史》說:“凡學不考其源流,莫能通古今之變,不別其得失,無從獲從入之途。”所謂 “考其源流”就是清理歷史發展的脈絡,在經學史上,宋代充滿懷疑精神的思辨學風是很突出的,影響也很大,那么這種思潮從何而來?林氏在《唐代經學的新發展》一文中,論述了唐中葉之后政治與學術的變化之后指出,其一,唐代后期經學逐漸拋棄注疏學的典范,而以己意說經;其二,開始懷疑漢人傳經的可靠性,成為宋代疑經改經的先聲;其三,學者為伸張王權,研究 《春秋》學,強調君臣之義;其四,李翱、韓愈表彰 《中庸》、《大學》、《論語》、《孟子》 等書, 以建構中國哲學心性論的理論,并成為宋理學立論的基本典籍的理論依據。這就為宋代疑經改經的懷疑思潮找到源頭,朱熹 《四書集注》的學術來源也可得到更明確的解釋。
前人在認為明代學術荒疏沒成就可言的情況下,誤以為考據學是清代特有的建樹。林氏 《明代考據學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3年7月)一書分析了楊慎、梅 、應麟、陳第、方以智等學者在考據學方面的成就,說明了在朱熹學的籠罩下,已有了重視古注疏、恢復漢學傳統的學術方向。為清儒引為驕傲的辨偽、輯佚、名物考證、音韻、訓詁等學術領域,早在明中葉以來已有相當的發展,這就說明了明代考據學早已成為清代考據學的先導,從而把我國考據學的產生推前了一百五十年。
(三)學術觀點的突破
1、關于朱熹 《詩經》學的評價
林氏《朱子對傳統經說的態度——以朱子 〈詩經〉著述為例》一文認為朱熹對《詩經》的詮釋有個轉變過程,轉變之后的朱熹對 《詩序》大加攻擊,以為去 《序》才能得 《詩經》本義。可是在后出的 《詩集傳》中,卻大部分沿襲 《傳》《箋》關于詩旨與訓詁的成說,有新見的只是 “淫詩說”和對 “興”義的探討。其結論是朱熹的創見并不多,經林氏的重新研究,看來朱熹是宋學集大成說,《詩集傳》是 《詩經》學史上第三個里程碑說等都得重新檢討。
2、打破三百年的陳說
明朝嘉靖年間,出現了轟動一時的《子貢詩傳》和 《申培詩說》,由于托名為經學史上的名人,內容又不同于前人的詩說,轟動一時,讓當時一些著名的學者也信以為真。后經清儒毛奇齡、朱彝尊、姚繼恒等人的考證,認為是嘉靖時進士豐坊所偽作。林氏 《豐坊與姚士粦》一文,認為 《子貢詩傳》有刻本與抄本兩種,抄本為豐坊所偽撰,而刻本則為王文祿所改定。今所流行的刻本多為王文祿改定本。至于《申培詩說》則是王文祿抄襲豐坊之父豐熙《魯詩正說》而成,也與豐坊無關。林氏這個打破三百年成說的新見解,表現了著者相當高的考證功力,而這正是當代年輕學者所缺乏的。
明中葉后出現許多偽書,被后人視為明代學術空疏不實的重要證據,林氏則認為明代作偽者大多不滿于宋明經學另求出路,借助偽書以復興漢學。手段不足為訓,但對漢學的復興與發展,具有推波助瀾的功效。這種把問題放在學術大背景的思路,以及辯證思維的成功運用,由此該說被學人評為 “最為中肯的評價”
此外,林氏在 《群經辨偽學》(臺北:文津出版社1990年10月)中采用了以經書為經,以時代和人物為緯的建構模式,突破了以學者為單元,以學者及其著作的時間為順序的慣常建構模式,也有一定的價值;另外,對經學史上的大章句與小章句、師法與家法提出自己的新見解;對明代 《五經大全》與清代陳奐的研究,已引起臺灣學者的關注,并沿著他的研究方向繼續前進。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出林氏經學研究的優長在于創新,在于開拓性。皮錫瑞《經學歷史》有句名言:“凡學皆貴新,唯經學必專守舊”這是違反科學發展規律的。林氏的研究告訴我們,在知識爆炸的信息時代,思維能力很重要,誰學會創造性思維并運用于工作中,誰就能獲得成功。
二、經學研究目錄的編纂與經學文獻的整理
在臺灣編纂目錄既沒有經費,又不能評職稱,所謂 “愚者不能為,智者不肯為”。三十年來,林氏卻樂此不疲,耗去許多精力與心血。由他主編的有 《經學研究論著目錄》1912~1987)(臺北:漢學研究中心1989年12月)等6部經學研究目錄;與他人合作的有 《晚清經學研究文獻目錄1912~2000 年》(臺北:“中研院” 文哲所籌備處1995年月)等3部。另有具有理論與操作價值的 《專科目錄的編輯方法》(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1年4月)和 《學術資料的檢索與利用》(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3年3月)兩書。林氏在目錄上的貢獻,被學者譽為 “是我國工具書發展史上的一大里程碑”、“為天下人做學問”。他所編的目錄的特色是:1、過去臺灣、大陸所編的目錄各管各的,互不通氣。而林氏的目錄不僅兼收大陸,還視野擴大到香港、新加坡、日本和歐美。2、除專書外,兼收論文,若一書有各種版本,不同的出版社、出版年月、頁數等都一一著錄。3、臺灣戒嚴時期,出版社往往把大陸的出版物改頭換面,林氏一一加以恢復。由于體例完備,資料豐富,成為臺灣專科目錄的典范。他的 《日本研究經學論著目錄 1900~1992》(臺北:“中研院”文哲所籌備處1993年10月)《日本儒學研究書目》(合編,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8年7月)出版后,日本荒木見悟教授感慨地說:“讓一個外國學者來為我們編目錄,我們日本人感到很羞愧。”
在經學文獻的整理方面,林氏也有優異的成績。由他整理的文獻12部,與他人合作的有3部。其中 《點校補正 〈經義考〉》(臺北:“中研院”文哲所籌備處,1997年6月~1999年8月),全書三百卷,林氏為點校這部經學巨著的計劃主持人,并參與編審及 《點校說明》、《點校凡例》的編寫,該著的整理可謂完成了一個浩大的學術工程。《姚際恒著作集》(臺北:“中研院”文哲所籌備處1994年6月)和 《姚際恒研究論集》(合著,臺北:“中研院”文哲所,1996年5月)的告罄,既完成了顧頡剛當年未能完成的事業,又為姚際恒和清代經學研究提供了更為充足的資料。林氏還把視野擴大到海外,翻譯安井小太郎等著《經學史》(合著,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1996年10月)和松川健二編 《論語思想史》(合著,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 2006年2月)和翻譯日本學者經學論文10多篇。為經學海外學的研究開辟新的天地。他在文獻整理方面的特色是:1、有一整套嚴格(包括標點符號)的工作規范;2、體例完整,每部點校本都有 《點校說明》、《點校凡例》、《前言》和 《附錄》等項目,另有 《朱彝尊〈經義考〉研究論集》(合編,臺北:“中研院”文哲所籌備處2000年9月)等資料匯編與點校本配套,在 《姚際恒著作集》的整理中,林氏做了許多勾沉工作,為學者提供研究的方便;3、作為文哲所經學研究的領航者,他為經學研究和整理制定工作計劃,其中有 《經義考點校補正》計劃、 《姚際恒著作集》編輯計劃、清乾嘉經學研究計劃、清乾嘉揚州學派研究計劃、晚清經學研究計劃等。為推動研究的完成,他舉辦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到大陸考察經學遺址。為了更好地完成計劃,他邀請大陸、日本學者參與其中。1992年他與大陸賈順先教授合作完成 《楊慎研究資料匯編》(臺北:“中研院”文哲所籌備處192年10月)是最早開展與大陸學術交流的先行者之一。
林氏在經學研究的成績是多方面的,而且令人驚奇。可以這樣說,他已經登上當代經學研究的高峰。這除了智慧和勤奮的因素外,與他正確的治學道路有關,說明目錄與古籍整理是經學研究的基礎工程,只有基礎打好了,才能建造學術高樓。當今學術界有一股浮躁之風,不肯在基礎上下功夫,投機取巧,嘩眾取寵,甚至造假。“鄰壁之光,堪借照也”,聰明人偏下笨功夫,不是也值得學習。
三、一個為理想而奮斗的文化志士
筆者在閱讀林氏著作時,有兩個地方感觸很深:其一,他在 《清代經學研究論集》(臺北:“中研院”文哲所 2002年8月)中寫道:“1932年,日寇進犯上海,發生一二八戰役,張金吾編輯 《怡經堂續經解》隨涵芬樓之藏書四十余萬冊,全部化為灰燼。這是經學研究的大不幸,也是中華文化的一大損失。”這種對傳承中華文化的珍貴古籍遭受日本侵略者焚毀而痛心疾首的情感,反映了一個中華兒女的良知,一個為傳承中華文化而奮斗的文化戰士的形象呈現在我們面前。大陸有個教授在網上發表 《狗入的國學》一文,說 “國學狗屁,一錢不值。”這種無知與林氏相較,相差何止千里?其二,臺灣有個關注國民教育,研究傳統文化脈動的雜志叫 《國文天地》,曾獲得臺灣出版界的金鼎獎。后因各種原因,不得不宣布停刊。1988年3月,林氏與13位大學教師一起接下這份重擔,并寫下《我們的理想和期望——〈國文天地〉的再出發》一文,談及他們不因重重困難而畏縮的理由之一是,有隋代靜琬與咸豐年間的丁申、丁丙兄弟和 《牛津大字典》的編輯者等為文化理想而奮斗犧牲的志士仁人作為他們的精神支柱。其實林氏不也是一位為了文化理想而奮斗的志士嗎?他在“臺獨”甚囂塵上的時候,在文章中透露著對他們排斥中華文化的不滿;他編輯 《日據時期臺灣儒學參考文獻》(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2000年10月)等文獻,有著弘揚在日本侵略者統治下 堅持民族文化精神的意圖;在臺灣戒嚴時期,他沖破禁令到大陸采購大量書籍,回臺后成立以傳播中華文化為宗旨的 “萬卷樓圖書公司”;大陸開放后,他以 《國文天地》社長的身份與中華書局 《文史知識》編輯部進行學術交流,并發表 《發揚傳統文化,兩岸共譜新曲》的會議紀要;他是中國詩經學會的顧問,并常到大陸做學術講座,為海峽兩岸的學術交流做了許多實事;他創刊的 《經學研究論叢》是世界上唯一的經學研究的刊物。大陸學者新近開始更多地關注經學研究:北京清華大學彭林教授成立經學研究中心,姜廣輝教授等編寫 《中國經學思想史》,四川大學舒大剛教授積極投入經學和經學史的研究等。香港新近召開經學探討會,編輯 《香港研究經學目錄》,也有著林氏經學研究的影響。新近林氏正積極編寫 《中國經學史》,我們期待他的成功。蘇格拉底說,世界上最快樂的事,莫過于為理想而奮斗。這正是林氏三十年如一日,對傳統文化做出重大貢獻的原因所在。
“智山慧海傳真火,愿隨前薪承后薪”,被東吳大學學生評為 “熱門教授”的林氏,為了經學研究后繼有人,在東吳大學開設“中國經學史”課,編寫了 《學術論文寫作指引》(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1996年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