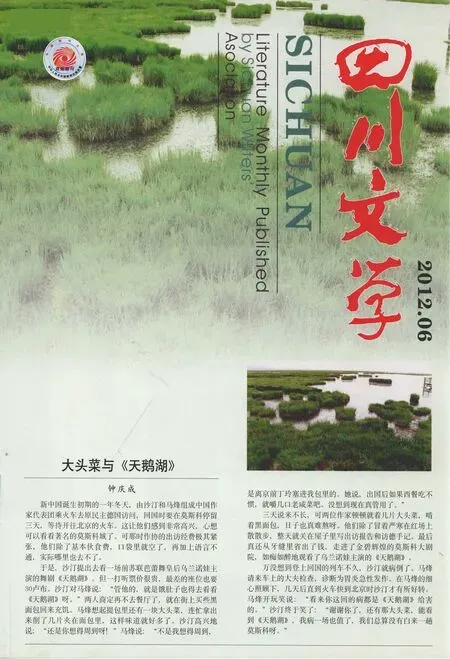是粗話還是抒情詩
□徐迅雷
約翰·馬歇爾·哈倫肯定沒有想到,在他擔任大法官的最后一年,也就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年,有一個小案件會為他贏得巨大的聲譽。
1971年的時候,越戰(zhàn)尚未結(jié)束,反戰(zhàn)漸入高潮。2月22日這天,美國最高法院的議事廳,就一句罵人的話導(dǎo)致的一起案件展開了一場庭審辯論。那個叫保羅·羅伯特·科恩的年輕人,當初吊兒郎當?shù)卮┝艘患A克,上面寫著“fuck the draft”這樣一行粗話——他當時只是穿著這件衣服在洛杉磯法院的走廊里晃蕩了一圈,表示一種不滿和抗議,結(jié)果就成了被告,一審被判有罪。
科恩把案件上訴到最高法院。主持庭審的是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沃倫·伯格,他是美國第15任首席大法官,任期從1969年6月至1986年9月。他是從前任厄爾·沃倫首席大法官手上接過接力棒的。兩個人名字里都有“沃倫”,但擔任首席大法官16年之久的厄爾·沃倫更為著名,他在1953年至1969年擔任首席大法官期間,美國最高法院做出了很多著名判例,涉及種族隔離、民權(quán)、政教分離、逮捕程序等等;2006年,厄爾·沃倫曾被美國一份權(quán)威期刊評為影響美國的100位人物之一,名列第29位。因為厄爾·沃倫,“沃倫法院”這個名字家喻戶曉;同時,也沒有人再懷疑最高法院的權(quán)威性、公正性。無論此沃倫還是彼沃倫,他們恪守美國憲法的法律精神是一樣的。而此刻,沃倫·伯格面對的“科恩粗話”一案,似乎有些微妙,因為庭審現(xiàn)場有一群修女在座。
“fuck the draft”這句粗話,翻譯成中文就是:“去你媽的征兵”。draft在這里就是征兵的意思。當時的大背景很清楚:美國人越來越討厭越戰(zhàn),越來越反對這場曠日持久的戰(zhàn)爭。“去你媽的征兵”就是一句反戰(zhàn)的粗話。但因了這句話,科恩被加利福尼亞州法院判處破壞和平罪。
包括約翰·馬歇爾·哈倫在內(nèi)的最高法院9名大法官,就“科恩粗話”案進行表決,結(jié)果是5票對4票,推翻了對科恩的有罪判決,理由是:原判侵犯了原告在憲法第一修正案下的表達自由。著名的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最核心的內(nèi)容就是“國會不得立法限制言論、出版自由”。“第一修正案”實在是很“古老”的法條了,它于1789年9月25日提交給各州批準,1791年12月15日獲得通過,迄今已過去了221年。同樣,中國的憲法也有這樣的規(guī)定,就在現(xiàn)行憲法的第三十五條;我們屬于“后發(fā)優(yōu)勢”,不用什么第幾“修正案”,就直接寫進憲法文本里去了,只是不同時期歸屬于哪一條有所不同而已。
5比4的表決結(jié)果,可見對“科恩粗話”一案大法官們意見分歧很大。對于此案的最重要的法庭意見書,就是大法官約翰·馬歇爾·哈倫起草的——準確地說,是約翰·馬歇爾·哈倫二世起草的。因為還有一個完全同名同姓的約翰·馬歇爾·哈倫,這個老哈倫是小哈倫的祖父,曾于1877年至1911年出任大法官,這兩人是最高法院唯一的祖孫法官。
哈倫二世在1955年至1971年擔任最高法院大法官,他大部分時間是與厄爾·沃倫同事,他在“沃倫法院”時期,所寫的意見書多次與法院主流意見不符,從而被稱為偉大的異議者。在美國廷斯萊·E·亞布洛教授所寫的《約翰·馬歇爾·哈倫》一書中,副標題就是“沃倫法院偉大的異議者”(漢語譯本由法律出版社在2004年1月出版)。而同樣,他的祖父老哈倫,也被稱為那個時代的偉大異議者。
小哈倫在任期的最后一年,遇上了這起“科恩粗話”案。他最初對該案的第一印象,是“看起來不太合乎邏輯,以致無法找到適用于我們法律的方法”;而且,親自主持審理該案的首席大法官沃倫·伯格,甚至反對最高法院將有限的時間資源用在這類案件上(見《約翰·馬歇爾·哈倫》一書第407-409頁)。但既然接手了,這些大法官就認真對待。意見分歧和爭議,主要有兩點:一是科恩所表現(xiàn)出來的是一種行為,還是一種言論?二是假如是一種言論,那么第一修正案所保護的“言論”,是一切言論,還是有所限制?在司法實踐上,當然只有法官才有權(quán)判定“科恩粗話”是屬于“行為”還是屬于“言論”。法官的認知有差異,最后只能票決。
此外,有意思的是最初科恩被捕的起因,是粗話中的“fuck”含有“性侵犯”;而哈倫法官則特別強調(diào)科恩這個表達行為所具有的政治性。
哈倫隨后為這個并不起眼的“偶然小事件”起草法庭意見書,沒想到的是,他寫出了一個載入美國司法史的輝煌評論,其中非凡的名言就是——“一個人的粗話可能是另一個人的抒情詩”!這句話的中文翻譯有多種版本,而我覺得這個翻譯是最明白最精當?shù)摹_@句“fuck the draft”——“去你媽的征兵”,當然是一句粗話,可這句粗話對于廣大的反對越戰(zhàn)、不想被征入伍去充當炮灰的年輕人和他們的父母來講,還真是一句說出了他們心里話的“抒情詩”。美國公民其實普遍守法,全身上下都塞滿了法治意識,但他們同樣全身上下都洋溢著自由意志。作為公民的他們,長期以來就有著“不服從”的傳統(tǒng)。美國19世紀作家、哲學(xué)家亨利·戴維·梭羅,在瓦爾登湖生活期間,因為“不服從”、因為反對黑奴制、拒交“人頭稅”而被捕入獄。與散文集《瓦爾登湖》的散淡相比,他的論著《論公民的不服從權(quán)利》更顯犀利和深刻。
小人物科恩的被捕,與大作家梭羅的入獄相比,影響力當然不一樣。但憲法面前公民權(quán)利是一樣的。小人物有小人物表達的方式,梭羅恐怕就寫不出科恩那樣的“抒情詩”。哈倫在法庭意見書中為科恩的自由表達辯護,他寫道:“表達自由作為憲法權(quán)利,在我們這個擁有眾多人口和高度分化的社會,不失為一劑良藥。這一權(quán)利的創(chuàng)設(shè),正是為了能解除政府設(shè)置在公共討論之上的諸多限制,為了能將何種觀點應(yīng)當發(fā)表的決定權(quán)最大限度地交回到每個人手中。”
發(fā)表觀點的決定權(quán),最大限度地交回到每個人手中,這就是對鉗制“表達自由”的反動。美國憲法和其他許多國家憲法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它主要是限制政府權(quán)力的,而不是強調(diào)公民守法的。而要限制政府權(quán)力,公民的表達就是很重要的方式。對于用“粗話”來表達的科恩而言,其最本質(zhì)的問題是:罵的對象是誰——是公民雇用的政府,還是具體的公民個人?
現(xiàn)如今,美國公民罵政府或者罵總統(tǒng),都已是常態(tài)。只要公權(quán)力一出格,百姓肯定要群起而抗議。這天一位網(wǎng)友在微博上給我轉(zhuǎn)了這么個“微段子”:“移民入籍美國要考公民常識,移民局問:美國是法治國家,‘法治國家’是什么意思?中國人會回答:公民必須守法,但美國移民局的標準答案是:政府必須守法。”這就是不同制度環(huán)境造成的思想差異,而思想差異正是文化差異中最重要的一種。
哈倫還說:“我們希望,表達自由最終能創(chuàng)造一個更加有力的公民社會和更加優(yōu)良的政治制度;我們相信,不可能有其他任何方式能與美國政治制度所賴以憑靠的個人尊嚴和選擇相適應(yīng)……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如此這般時常充斥著刺耳雜音的社會氛圍,并不意味著軟弱無能,而恰恰是力量的體現(xiàn)。”這話已是非常通透,公民社會其實就是一個多元的、嘈雜的社會。民主的一個本質(zhì)表現(xiàn),就是人的自由個性的覺醒和展現(xiàn)。牢騷太盛者,恰恰用不著“防腸斷”。有人說得好,“抱怨是最低成本的抗議,牢騷本身就是建設(shè)性,表達不滿就是一種推動”。沒有公民個人的自由,就沒有國家和社會的安寧和穩(wěn)定;沒有公民個人的尊嚴,國家的政治制度就不可能被尊重。而那些整齊劃一、思想單一、貌似純潔、不容“多說一句話多走一步路”、甚至弄得鴉雀無聲的家國社會,大抵是專制獨裁長期控制之下所形成的。
哈倫從事律師職業(yè)時,他被稱贊為“律師中的律師”;在成為大法官,退休與去世時,他又被稱贊為“法官的法官”。如今再讀哈倫的法律意見書,就會感覺到那深邃的法理,那蕩漾的正氣,令人敬嘆!哪像俺們這里,一些所謂的“法學(xué)家”,誰給錢就給誰出具“法律意見書”,法律的文字,輕易就成了斂財?shù)墓ぞ摺?/p>
一個人的粗話,可能是另一個人的抒情詩;同理,一個人的粗話,更可能是他自己的抒情詩。而一個人的堂皇之話,則可能是另一群人的災(zāi)難;同理,一個政府的冠冕之話,則可能是全體民眾的災(zāi)難。
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圖圖主教曾說:“一旦人們下決心爭取他們的自由和人權(quán),即使是最尖端的武器,即使是最嚴厲的政策,也無法阻止他們。”如今我們可以進一步說:即使是最強權(quán)的司法,也無法阻止他們。
約翰·馬歇爾·哈倫二世生于1899年5月20日,1955年3月17日至1971年9月23日任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退休3個多月后,在1971年12月29日辭世。被稱為“最高法院研究者必讀之作”的《約翰·馬歇爾·哈倫——沃倫法院偉大的異議者》一書,記錄了葬禮當天的情形:成百上枝支紅玫瑰裝飾著教堂的白色內(nèi)壁,“作為哈倫的家”。哈倫逝世后,尼克松總統(tǒng)稱他為“20世紀的偉人之一”。而為了表示對約翰·馬歇爾·哈倫一世的尊重,哈倫指示在他墓碑上,將名字中的“馬歇爾”只用一個M來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