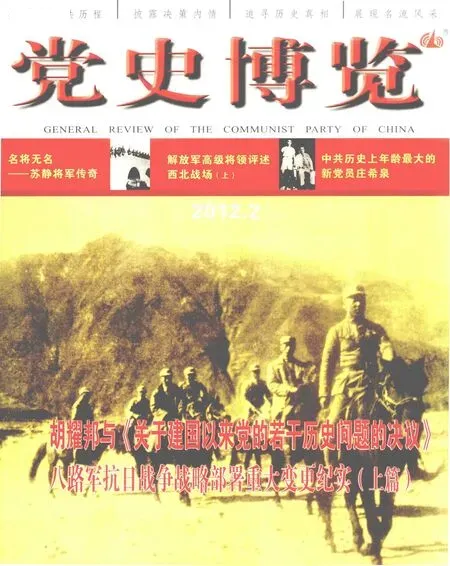名將無名——蘇靜將軍傳奇
■ 葉暉南
名將無名
——蘇靜將軍傳奇
■ 葉暉南
蘇靜,開國中將。一生傳奇,但知道他的人卻不是特別多。著名作家張正隆在他的大作 《槍桿子——1949》一書中評價蘇靜時說得貼切:名將無名。
蘇靜,原名蘇孝順,1910年12月21日出生在福建省龍海縣 (今龍海市)海澄鎮六口碑村一個普通農民的家庭里。4歲那年,其父為了生計,遠赴緬甸,家里只有祖父依靠著一點點薄田和一條破船艱難度日。生活雖然清苦,但祖父卻堅信一個道理,男兒要立足于世,非有文化不可。于是,一家人咬緊牙關供蘇靜上學。當他以優異的成績小學畢業后,祖父又不惜舉債讓蘇靜上了位于漳州的省立第八中學。在這所中學里,他第一次接觸到共產黨人,并在黨的影響下開展革命活動。1930年,蘇靜考入漳州第二師范學校繼續深造。正因為如此,當他1932年參加紅軍時,紅一軍團政治部主任羅榮桓稱他是 “文化人”,并根據他本人的意愿安排其到紅一軍團司令部通信科當科員 (參謀)。
長征中走路最多的人
1934年5月,紅一方面軍進行整編,蘇靜調到紅一軍團司令部作戰科當科員,不久又調到軍團偵察科任參謀,其職責是負責繪制軍團的行軍路線圖和謄稿、刻蠟版、油印等工作。1934年10月,中央紅軍因第五次反“圍剿”失利,被迫走上了漫漫長征之路。蘇靜所在的紅一軍團一路成為全軍的開路先鋒,而蘇靜則是先鋒中的先鋒。由于偵察參謀的職務所在,蘇靜在長征中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為整個軍團探路。部隊行軍打仗每到一地,別人都住下休息了,他卻不能歇息,要馬上出發,帶上幾名偵察員,朝軍團首長定下的下一站,沿路偵察。這項任務不僅艱辛,而且危險。漫漫長征路,大部分時間是行走在高山大川中,在伸手不見五指的夜里,到處潛伏著毒蛇猛獸,沿途還可能有土匪民團的襲擊騷擾。偵察回來,要立即把行軍路線上的地形地貌、道路橋梁一一畫在圖上。他在紅軍中文化水平相對較高,人又極為細致認真,畫出來的圖清晰、規范,軍團首長林彪、聶榮臻等對他的工作向來感到滿意和放心,并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聶榮臻在回憶錄中就說過這樣的話:“紅軍過草地,蘇靜同志在前面開路是有功的。”
除了開路當先鋒以外,蘇靜還利用自己的文化知識和觀察能力解決部隊在行軍作戰中碰到的難題。紅軍長征一路走來,敵人的飛機就像趕不走的蒼蠅,天天在紅軍行軍隊伍的頭頂盤旋、轟炸、掃射,給紅軍帶來不少傷亡。如何才能把敵人空襲的損失降到最低的限度?細心的蘇靜開始觀察敵機的行動規律,試圖找到一套躲避敵機空中打擊的辦法。他后來說:“飛機有時飛得很低,真是欺負人。我冷靜地觀察飛機投彈的位置與彈著點的距離,總結出躲避炸彈的經驗,并告訴戰友們。”掌握了敵機規律,也就找到了對付的辦法,這對減少部隊傷亡起了不小的作用。
據紅一方面軍的行軍記錄統計,從1934年10月踏上長征路,到1935年10月勝利到達陜甘蘇區的吳起鎮,轉戰11個省,一共走了二萬五千里。但蘇靜走的長征路可遠不止這些。部隊每到一地休息了,他卻帶上幾個偵察員又出發了。按照軍團首長的意圖,向下一個目標探索前進,先摸清道路,偵察敵情,然后找好下一個宿營地,再返回部隊駐地,精心繪制成地圖。待完成了所有的任務后,已經是下半夜了。倒頭睡上幾個小時就得爬起來跟著部隊向新的目標前進。在長征中,他一共繪制了幾百張行軍路線圖。別人走了一遍的長征路,他要先偵察走個來回,再跟著走一趟,走的距離是別人的三倍。
對友軍的真誠與反算計
由于蘇靜在偵察工作上干得相當出色,1937年1月他升任偵察科科長。1937年7月,抗日戰爭全面爆發,9月下旬,八路軍東渡黃河,進入山西打擊日軍。抗日戰爭的爆發,使國共兩黨重新聯合起來共同對付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如何對待友軍,是一件政策性和策略性都很強的事情。
1938年2月,日軍進攻晉西南。八路軍一一五師分兵一部阻截敵人,以保衛黃河河防。3月2日,林彪率部向敵后運動,進行到隰縣以北千家莊附近時,突然傳來一聲槍響,林彪中彈落馬。此時,蘇靜帶著偵察排就跟在林彪的身后,見發生意外,趕緊把林彪扶到路邊的溝坎下隱蔽,同時命令警衛員立即到后續部隊處找醫生。
堂堂八路軍的師長在國民黨閻錫山的防區內被擊傷,非同小可。第二天,師政治部主任羅榮桓安排林彪去后方后,立刻把蘇靜找來,要他到國民黨防區去調查此事。國共雙方過去打了十年內戰,彼此之間都存戒心,搞得不好,一點火花就可能點燃一場大火。蘇靜去了閻錫山的防區,對整個槍擊事件作了細致的調查,并進行了實事求是的分析,最后得出結論,這是一次誤傷事件。初春時節,天氣尚冷,林彪在行軍時,披了一件在平型關戰斗中繳獲的日本呢子大衣。閻錫山部的一個警戒分隊哨兵誤認為是日軍的軍官,就打了一槍。蘇靜本著實事求是的精神把調查結果作了匯報,從而避免了誤會。
槍擊事件過去沒幾天,又發生了一件大事,二戰區的國民黨軍總司令部無線電密碼被日軍破譯,國民黨軍卻一無所知。一天,衛立煌帶著他的司令部剛剛到達大寧,日軍就偷偷地圍了上來。這一情況被八路軍一一五師偵知,羅榮桓和代理師長陳光當即命令蘇靜帶一個營去掩護衛立煌。蘇靜騎上馬一口氣追趕了5公里路,才把衛立煌追上,向他通報了敵情。衛立煌還沒來得及轉移,日軍就已經在第二天發起了圍攻。當時衛立煌身邊沒有多少部隊,全靠八路軍一個營的兵力拼死抵擋。在沖出包圍后,蘇靜命令留下一個連斷后。這個連在白兒嶺據險死守了一天,英勇抗擊800多日軍的輪番進攻。衛立煌望著遠處山梁上硝煙彌漫,火光沖天,惋惜道:這個八路軍連隊完了!不想,這個連隊雖然付出了一定的傷亡代價,但完成阻擊任務后整建制地撤了回來,還給衛立煌帶回一堆繳獲的戰利品。
真心對待友軍并不意味著完全放松警惕。一一五師進入晉西后,二戰區的國民黨軍以國共合作的名義派了一個聯絡參謀帶上電臺來到師部。來者不善,八路軍既要同友軍搞好配合,又要防止友軍在暗中偷偷算計自己。羅榮桓和陳光經過商量,決定派蘇靜去負責同友軍打交道。蘇靜同這名聯絡參謀周旋了一段時間,心中已然有了底。原來這名參謀除了負責溝通兩軍的聯絡外,也負有刺探八路軍情報的任務。心知肚明的蘇靜于是來了個將計就計,白天同國民黨參謀虛與委蛇,時不時“無意中”說漏了嘴,泄露出一些八路軍的情報。到晚上,蘇靜沾上枕頭就安然入睡,當他鼾聲漸起之際,那個參謀便打開電臺,一人念報文,一人敲發報鍵。躺在被窩里的蘇靜則把這一切都記了下來。二戰區國民黨軍的密碼就這樣輕而易舉地被我們搞到了手。
一個蘇靜等于十萬兵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國共雙方隨即為爭奪東北展開了激烈的較量。11月中旬,蘇靜跟隨羅榮桓到達沈陽,在剛剛組建的東北人民自治軍中擔任司令部情報處處長。隨即,跟著林彪帶領的“前總”(前線總指揮部的簡稱)來到錦州前線。“前總”是個非常簡便高效的指揮機構,除了林彪,就是李作鵬、蘇靜、何靜之等幾個人。
初到東北,局面相當混亂,說起來出關的部隊多達十幾萬,但各部隊都是從各自的根據地出發,彼此之間沒有電臺進行聯絡,就連林彪帶領的“前總”也不知道自己的部隊在哪里。一開始仗打得很被動,林彪到處找不到自己的隊伍。還出了這樣一個笑話:11月下旬,新四軍三師在黃克誠的率領下到達錦州前線,29日中央軍委電示黃克誠:“關于你部的編制、干部配備與活動地區和作戰意見等,你均可與林彪商談,并由你與林向中央提出意見解決。”黃克誠接到指示后當即給林彪發電聯絡。結果報是發出去了,卻杳無回音。原來雙方根本就沒有一個統一的密碼。過了幾天,林彪和黃克誠偶然碰上了,才知道彼此之間的駐地相距不過15公里。初到東北,老百姓也不了解共產黨,把國民黨當成正統。這使得我們幾乎變成了瞎子。山海關失守,錦州失守,遼西走廊洞開……守也守不住,打運動戰又集中不了兵力,此時情報工作的重要性更加突出了。身為情報處處長的蘇靜,這段時間全力以赴地工作著。在他的精心組織下,一張卓有成效的情報網漸漸地編織起來,為擺脫被動局面作出了貢獻。
1946年2月中旬,國民黨軍八十九師的一個加強團進犯至法庫縣的秀水河子一線。這一情況當即被情報處偵知,蘇靜及時把這一情況上報民主聯軍(此時東北人民自治軍已改稱東北民主聯軍) “前總”。“前總”根據這一情報,命令附近的民主聯軍各部迅速合圍。激戰兩日,全殲來犯之敵并繳獲大量武器裝備,取得了我軍出關以來第一場較大的勝仗。此后,又以準確、及時的情報保障了大洼戰斗的勝利。幾次成功的情報保障下來,林彪很滿意,曾對身邊的人說:“一個蘇靜等于十萬兵。”
這也許是對名將無名最明了的注解。
蘇靜做情報工作不僅思維縝密,細心周到,關鍵時刻也敢于負責。在東北野戰軍,誰都知道林彪的威嚴,他有個習慣,話不聽二遍!而蘇靜就敢破這個例。1948年9月,遼沈戰役拉開戰幕,東野主力直撲北寧線。10月1日,首戰義縣,在強大炮火的支援下,發起總攻僅僅4個小時就攻克了堅固設防的城池。10月5日,蘇靜在義縣附近向林彪、羅榮桓匯報義縣作戰經驗時,特別提到攻城部隊采用了近迫作業挖交通壕隱蔽接敵的方法,大大減少了在敵炮火下運動的時間與距離,有效地增加了攻擊的突然性,減少了自己的傷亡。蘇靜匯報完后,林彪當即命令蘇靜返回義縣,調主攻義縣的三縱和二縱的五師參加主攻錦州。蘇靜覺得他匯報的義縣攻堅經驗沒有得到林彪應有的重視,到了錦州前線,趕在總攻發起之前,于10月7日,斗膽再次向林彪提起義縣攻堅的經驗。這一回林彪聽進去了,向攻城各部隊下達命令,攻城各部必須實施近迫作業,挖交通壕接敵。這一招不僅在攻錦作戰中起到了同義縣戰斗同樣的作用,還在精神上給守敵以極大的打擊。戰后,被俘的國民黨軍東北“剿匪”副總司令范漢杰承認,當他看到解放軍把戰壕挖到眼皮底下時,固守的信心立時開始崩塌。
連毛主席的信也敢扣
在遼沈戰役中,解放軍全殲國民黨軍47.2萬余人,東北全境解放。緊接著,東北野戰軍85萬大軍浩浩蕩蕩入關,直插平津。在解放軍強大的軍事壓力和政治攻勢下,國民黨華北“剿匪”總司令傅作義有心與共產黨方面進行和談。
1948年12月16日,傅作義派出北平日報社社長崔載之和該社采訪部主任李炳泉出城接洽。得知這一消息后,林彪、羅榮桓指派蘇靜負責接待。經過了解,蘇靜得知傅作義確有和談的誠意,李炳泉還是北平地下黨的成員。12月19日,平津前線司令部參謀長劉亞樓接見崔載之、李炳泉。從進行第一次談判起,到1949年1月16日雙方就國民黨軍改編和北平接收各項事宜達成基本協議止,共進行了三輪談判,蘇靜作為解放軍的代表,全程參加。16日下午談判結束后,傅作義的代表鄧寶珊提出希望解放軍方面派出代表同他一起進入北平城,以便進一步聯絡。林彪、羅榮桓便派蘇靜去執行這個任務。當晚,林彪交給鄧寶珊一封信,要他交給傅作義。信沒有封口,鄧寶珊私下里看了,看完之后大驚失色,當著蘇靜的面說:“這封信太出乎意料了,這封信措辭很嚴厲,傅作義不一定會受得了,我準備暫不交給傅先生,以免節外生枝,使談判功虧一簣。”蘇靜覺得事關重大,向總前委作了匯報,得到了暫不遞交的默許。1月17日,在進城的途中,鄧寶珊再次提到那封信,提出暫不交信的想法,征求蘇靜的意見。蘇靜當即表示:您可以決定嘛!
由于這封信被暫時扣下了,蘇靜進城后談判進行得基本順利。1月21日,蘇靜同傅作義的代表分別在《關于北平和平解決問題的協議書》上簽了字,至此北平和談取得圓滿成功。從第二天起,國民黨軍開始陸續開出城外。協議簽訂后,蘇靜奉命留在北平城內,繼續負責同傅作義方面的聯絡,并監督協議的執行,同時還為即將到來的解放軍入城儀式作準備。正當他忙得不可開交之際,1月25日突然接到指示,要他立即出城到宋莊指揮部匯報工作。蘇靜放下手頭的事情,趕到宋莊,見林彪、羅榮桓、聶榮臻等首長都在。羅榮桓見到他便問:“鄧寶珊轉傅作義的信交了沒有?”蘇靜回答:“不清楚。”聶榮臻說:“你今天要回去問一下鄧寶珊,若還未交,你要同他一起去見傅,務必在今明兩天讓傅看到這封信。”
蘇靜得到指令當天晚上就急忙趕回北平城內,找到鄧寶珊,并和他一起去了傅作義當時安在中南海居仁堂的家。傅作義熱情接待了蘇靜。在兩人談話期間,鄧寶珊進入了內屋,把信交給了傅作義的女兒傅冬菊。鄧寶珊實際上認為此刻還是不宜把信給傅作義看,但又想不出別的辦法,他知道傅冬菊是共產黨員,就悄悄找她商量。傅冬菊看過信后,也認為目前還不能把信交給父親,再次把信扣下了。就這樣,蘇靜、鄧寶珊、傅冬菊三個人兩次扣壓了這封信。后來,蘇靜的一位好友開玩笑地對他說:“你可真是膽大包天啊!毛主席親自寫的信,你也敢同意不交,后來接到指示,你還是沒有讓傅看到那封信,你就不怕追究你的責任?”蘇靜笑而不答。
直到1949年2月1日,《人民日報》全文刊登了這封信,傅作義才看到它。原來這封被平津前線總前委高度重視的信雖是以林、羅的名義寫的,其實則是毛澤東的手筆。信中說,傅作義“接受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所謂‘剿匪戡亂’之偽令,率領所部數十萬反動軍隊向著……人民解放區和人民解放軍發動殘酷進攻。……”歷數了傅作義指揮的軍隊攻占解放區77座城鎮,又指責傅作義統治下國民黨犯下的累累罪行,最后還指出,如果和談不成,本軍將攻城,“破城之日,貴將軍及貴屬諸反動首領,必將從嚴懲辦,決不姑寬,勿謂言之不預”。
果然,傅作義在讀過這篇報道后,情緒出現強烈波動。其實,毛澤東寫這篇措辭激烈的信也是事出有因。三年前,內戰初起,傅作義指揮他的人馬連續攻占了解放區的多座城池,一時間得意忘形,竟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揚言共產黨不可能取得勝利,并說如果毛澤東能打贏這場戰爭,他愿意給毛做一名馬夫。不想也就三年的時光,中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當傅作義冷靜下來后,提筆給林彪、羅榮桓、聶榮臻寫了一封回信,承認他有罪,應該受到人民的懲處,要求對他作為戰犯處理,并指定看守所,他主動去報到。
2月5日,傅作義等到的答復卻是林彪、羅榮桓、聶榮臻在北京飯店的宴請。蘇靜參加了,據他回憶,宴會的氣氛是融洽的。2月20日,毛澤東在西柏坡接見了傅作義、鄧寶珊,肯定了兩位將軍在和平解決北平問題上所作的貢獻,鼓勵他們為人民立新功。
“文革”中的小智慧與大智慧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全國陷入混亂,為穩定局面,中央決定對事關國計民生的要害部門實行軍管。1967年4月,由周恩來提名,總參黨委決定,派蘇靜到鐵道部擔任軍管會主任。當時,鐵道部已經成為“文革”期間的重災區,群眾分為兩個派系,相互之間你爭我斗,各不相讓。一見到軍代表來了,都撲上來,逼軍代表表態:自己一派是真正的“左派”。這是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表態一旦出錯,無疑就會遭到滅頂之災。軍隊的同志剛到地方,情況不熟悉,心中沒有底。面對巨大的壓力,有人提醒蘇靜,戰爭年代既然和林副統帥非常熟悉,何不以老部下的名義去摸摸底?蘇靜心中有一定之規,一直沒有去。
軍管會這邊沒動靜,中央文革那邊可是專門搞煽風點火的陰謀。他們對鐵道部那邊火燒得不旺大為不滿。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帶上謝富治跑到鐵道部召開群眾大會,名曰“支左”,實為“支派”。大會一開始,陳伯達就讓他們想支持的一派的頭頭坐到主席臺上來。這樣一來,另外一派的群眾就不干了。眼看會場大亂,局面失控,蘇靜挺身而出,請另一派的頭頭也上臺來坐。這等于和中央文革公開唱對臺戲,在政治上已經冒了極大的風險。陳伯達一見陰謀沒有得逞,很生氣,站起身,帶著他的人下了主席臺,把蘇靜晾在了臺上。蘇靜也不含糊,你下臺我也下臺。臺上變得空無一人,會開不下去了。陳伯達沒辦法,只好再次請蘇靜上臺主持會議,蘇靜就再次把兩派群眾組織的代表都請上臺。陳伯達再無計可施。這下算是把中央文革給徹底得罪了。陳伯達走后,北京街頭“打倒蘇靜”的大標語開始滿天飛。蘇靜也做好了最壞的打算。過了不久,毛澤東的“最高指示”下來了:兩派都是革命群眾。中央文革只得作罷。多年后,蘇靜談起這件事時是這樣說的:“當時我覺得自己已經無路可走了,如果按中央文革的意思支一派壓一派,鐵道部肯定要大亂,全國的經濟也就必然大受影響,我就是國家和人民的罪人。如果不順從陳伯達等中央文革一伙人的旨意同他們對著干,我便是他們心目中的絆腳石,肯定要被打倒。不管怎樣,無非是個打倒,所以就豁出去了!”
對付陳伯達這種伎倆,除了膽略,用小智慧就對付了,處理同老首長林彪的關系則需要一種大智慧。1971年5月,林彪辦公室通知蘇靜,要他和冶金部、七機部的領導一起去毛家灣林彪的家匯報“支左”工作。蘇靜匯報完,臨走之前,林彪突然向他問起他的大兒子現在在哪里。在東北解放戰爭時期,林彪就認識蘇靜的大兒子蘇曉前。蘇靜回答:“在濟南軍區當兵。”林說:“大學畢業去當兵太可惜了。”蘇靜答:“年輕人當兵鍛煉一下好。”一問一答間,沒有半點借機攀附副統帥的意思。在總參工作期間,他的家離林彪的住所很近,卻從來沒有因為私事上過林家的門。
“九一三”事件后,大批曾經在林彪手下工作的人受到審查,蘇靜也受到沖擊。在群眾批斗大會上,有人要他交代同林的關系,他坦承,戰爭年代自己同林彪的關系非常密切。由于行得正,走得直,中央專案組也抓不到蘇靜的任何把柄。當他重新走上工作崗位后,專案組副組長紀登奎告訴他,中央原定要抓93人,結果只抓了92人!蘇靜再次躲過一劫,就是因為他從來沒有因私找過林彪。他的真實想法其實很簡單,就是認為領導工作忙,不該打擾。樸實的思想里面藏著大智慧。
1973年,韓先楚調任蘭州軍區司令員,他指名要蘇靜和他搭檔,出任軍區政委。蘇靜也很想回到部隊,但周恩來堅決不放。韓兩次打電話向周恩來要人,周恩來說,誰都可以調,就是蘇靜不能調。李先念也多次挽留蘇靜。直到1978年,蘇靜才如愿以償地回到了軍隊,也就是在這一年,他以大軍區正職的待遇離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