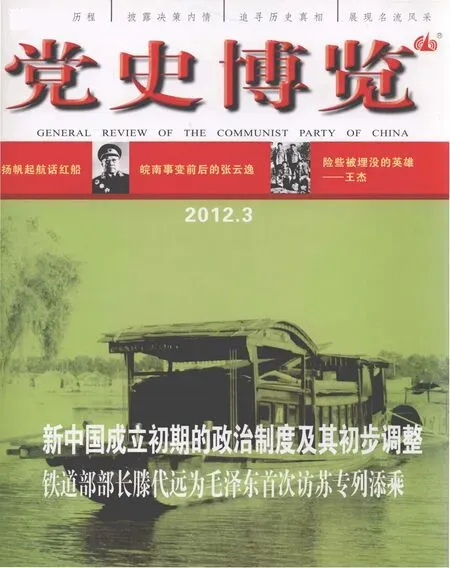海灣戰爭時期的駐伊拉克使館留守小組
鄭達庸
一
1990年8月2日,伊拉克軍事占領科威特。聯合國安理會和國際輿論強烈要求薩達姆撤軍,遭到拒絕。11月29日,安理會通過678號決議,決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迫伊撤軍。美國宣布,1991年1月15日之前,如伊拉克仍不撤軍,將組織多國部隊對伊開戰。我是1990年12月9日抵巴格達赴任當大使的。當時使館大部分人員已經撤離回國。隨著時間的推移,形勢越來越吃緊,以美國為首的多國部隊進駐海灣,戰爭呈一觸即發之勢。
根據外交部指示,使館成立由五人組成的留守小組。五人包括大使、一名二秘(李治國,現為駐南蘇丹大使)、一名機要員(李衛華)、一名報務員(陳林)和一名司機(王金弟)。一旦需要,留守小組可視情況撤離巴格達。
雖說當時美國已經對薩達姆發出最后通牒,以1月15日為限,但戰爭是否一定爆發,還有諸多復雜因素。我們必須隨時觀察形勢動向。
除陪同我一起參加對外活動、搞調研外,二秘李治國還要每天一個人開車上街,觀察動靜。他會講阿拉伯語,通英語,朋友多,信息來源廣,不時帶回鮮活的情況。
1月13日,聯合國秘書長德奎利亞爾訪問巴格達,目的是同薩達姆對話,作最后一次努力,勸薩達姆從科威特撤軍。秘書長是通過中國同伊方聯系的。我館接到指示后,趕緊聯系伊方,為保密,只說大使有要事約見伊拉克外長阿齊茲。當時伊拉克各個部門都在做應戰準備,工作秩序已經打亂。李治國到伊外交部坐等多時,終于落實阿齊茲接見中國大使這件事。我見到阿齊茲后,說明德奎利亞爾將訪問巴格達,阿齊茲表示愿意接待,但就是不說薩達姆是不是見德奎利亞爾。幾年后,我在國內見到李道豫大使(時任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聊起此事,他說當時真的很急,能不能聯系上伊方,德奎利亞爾能否前往巴格達,沒有把握。
二
中國駐伊拉克使館是個老館,有大批文件、資料必須處理,這個任務,交給了機要員李衛華。在非常時期,他的本職工作已經要比平時繁重,但小伙子還是加班加點超負荷地完成了任務。每次見到小李,他都在處理資料。當時巴格達天氣還有些寒氣,小李穿著褲衩、背心,在樓外燒資料,滿頭大汗,灰頭土臉。燒紙爐長時間保持高溫,爐體發生了爆裂,人長時間待在爐旁,前胸熱,后背涼。白天干完了,晚上還要工作,忙得他有時候也犯糊涂。記得有一次,我們計算巴格達同北京的時差,“現在是北京幾點了”,平時這根本不是問題,這次卻說法不一。大家建議,還是由小李定吧,他年紀最小嘛。最后,按照小李說的去辦了,后來發現,時間還是搞錯了。
此時,巴格達同外界的聯系變得極不正常,電臺通信增加了難度。使館同國內的聯系,同兄弟館的聯系,就靠報務員陳林了。這時候,保護電臺,保證通信暢通,成了頭等大事。陳林業務嫻熟,腦子靈活。當時我們還面臨一個課題,如果戰爭打響,國際航線全部中斷,留守小組只能從陸路自己開車出境,如何解決撤離路上同國內保持聯系的問題,我們是外行,插不上手。陳林經過思索后,想出一個同國內隨時聯系的辦法。當然,這是“非正常”手段,只能發出簡單信號。只要國內收聽到我們的信號,就知道這幾個人還存在;如果信號中斷,那就另當別論了。
小陳還上演過一出“智退外國記者”戲。一天,一名外國記者敲打使館大門,要求采訪大使。當時,留在巴格達的外國記者都在抓消息,采訪的中心問題是會不會打仗,之后發消息說這是某某使館的看法。這種采訪,不宜接待。我決定由小陳出面應付。小陳正好值班做飯,身上系著圍裙,挽著袖子,右手拿著炒勺,一副大廚的樣子。小陳開門后,搖擺著炒勺,指著耳朵,做出聽不懂的樣子,同時指著大樓搖搖手,意思是里頭沒人。那名記者見狀,搖搖頭,無奈地開車走了。小陳“得勝歸來”,大家向他表示祝賀,稱贊他有兩下子。
留守小組走后,館舍安全怎么辦?大家商量,只能把門統統鎖上,貼上封條。用蓋上使館印章的紙條,把四棟樓的房門全都封上。這個任務交給了司機王金弟。老王裁紙條,蓋印章,打糨糊,挨門挨戶地去貼,這活兒他一個人全包了。也許是太累了,有時候他索性跪在地上貼,糊里糊涂地,連廁所的門也給封了。有人發現了,指著老王說,你不讓我們上廁所了?大家哈哈大笑起來。老王還有個任務,也相當重要,那就是選出五輛汽車,準備萬不得已時,一人開一輛,從陸路撤出時用。
當時,我們選擇了三條路線:一條往西去約旦,全程1000公里,是條戰略公路,伊拉克境內的公路十分堅固,可以當飛機跑道,但有“死亡之路”之稱。戰爭中,這條公路會成為導彈襲擊的目標,很不安全。第二條往東走伊朗,兩伊戰爭后,這條公路已是千瘡百孔,還可能埋有地雷,有的地方大雪封山,并不安全。另一條路,往北走,通往土耳其,但要經過庫爾德地區,也不安全。總之,一旦戰爭打響,走哪條公路都有危險,只能闖了。我們五個人都會開車,要選好車上路。車輛出了故障,沒時間沒條件修理,只能甩掉。即便剩下一輛車,五個人也能坐下。
老王把使館其余車輛停到地下室出口,擋住外人從地下室進入樓內。老王還辦了一件大事。有一天他外出辦事,回館即告,美國大使館旗桿上的國旗不見了。這可是重要的信號。使團朋友告訴過我,你要留意美國使館的國旗,一旦降了,那就預示要開戰。老王帶回的信息,引起我們極大重視,感到撤離的時間臨近了,戰爭的腳步臨近了。
應該說,我們的食品儲備是豐富的,中資公司撤走時,好多剩余食品留給使館了。可是,我們五個人的胃口變得很小,緊張勞累,睡眠不足,都說吃不下飯。吃飯也不定點了,廚房全天開放,誰餓了誰去弄點吃的。新華社記者朱少華也來使館吃飯,他是我們的好戰友。吃飯時如果能都坐在一起就餐,成了我們這個小集體難得的聚會。大家邊吃邊聊,其樂融融,湊信息,分析形勢。
其實,現在想起來,我們當時是在“燈下黑”的狀態下工作。身處戰爭旋渦中心的巴格達,伊拉克當局嚴格控制和封鎖消息,外國使館紛紛撤離,我們對于局勢的判斷和反應,更多的是感性的。經過最后的觀察和分析,大家認定,開戰是無疑的了。11日,使館撤出的同志從約旦打來電話說,約旦那邊許多國際航線都停飛了。我們迅速投入撤離前的最后工作,降旗,處理機密材料,轉移電臺,帶走要件,等等,直至閉館。
14日凌晨,國內指示,同意撤離,留守小組前往中國駐埃及使館待命。當天清晨6時半,我們出發去機場,登上最后一班飛機,飛往約旦。抵達安曼當天,隨即轉機前往塞浦路斯。
17日凌晨,美國宣布開戰,海灣戰爭打響了。以美國為首的多國部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不僅在科威特,還在包括巴格達在內的伊拉克本土上,狂轟濫炸。
三
1月17日9時,留守小組抵達開羅。
戰爭進行了42天后,伊軍被迫撤離科威特,海灣戰爭結束。
3月1日,國內指示留守小組返回巴格達。我們五人先回到安曼,在那兒打了各種預防針,打得個個渾身難受,似病非病。在當地購買了一輛豐田越野車,租了一輛卡車,帶上糧食、罐頭、飲用水、煤氣罐等生活必需品,于3月15日登上“死亡之路”。公路上到處彈痕累累,底格里斯河大橋雖未坍塌,卻是布滿彈洞,車子走在搖擺的橋上,從裂洞中可見流淌的河水。
臨近巴格達城,遠處一片漆黑,往日燈火通明的城市,如今變成了一座死城。使館有水(不干凈),無電。次日清晨,看到使館有的房屋吊頂掉下了,窗玻璃碎了,使館附近還落下一枚導彈,不少物品尤其是食品、汽油、煤氣罐等被劫。就這樣,我們五人小組又開始了戰后的“新生活”。
從約旦帶回的煤氣罐不能用,只能用煤油爐做飯,一鍋湯要燒上一個半小時。沒有汽油,到黑市購買。大家堅守崗位,毫無怨言。和撤離前的日子相比,物質條件更差了,但吃飯時,依舊有說有笑,干起工作,一如既往。不久,其他人員陸續返館,留守小組自然解散了。
留守小組完成了歷史使命,在海灣戰爭前后的三個多月里,我們五個人經歷了人生中一段非常難忘的時期。大家緊張、辛勞地工作、生活、戰斗在一起,朝夕相處。對每個人來說,它雖然短暫,卻永遠地留在記憶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