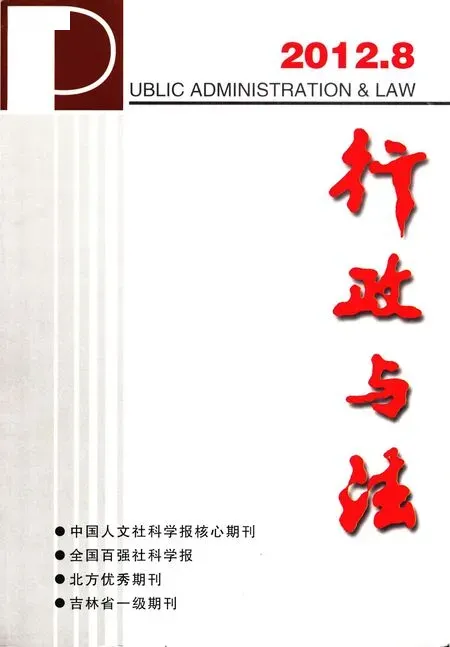人身侵權債權在破產清償順位中優先受償之思辯
□ 鄒 楊,榮振華
(⒈東北財經大學,遼寧 大連 116600,⒉西南政法大學,重慶 401120)
人身侵權債權在破產清償順位中優先受償之思辯
□ 鄒 楊,榮振華
(⒈東北財經大學,遼寧 大連 116600,⒉西南政法大學,重慶 401120)
在調整人身侵權債權的各種制度中,為人身侵權債權在破產清償順位中找尋優先清償點是次優制度選擇,因為無論人身侵權債權定位在哪一個清償層面都是后序債權人為破產企業的非法行為買單。為此,在其他法律制度足以保護人身侵權債權人權益的前提下,在破產清償順位中為人身侵權債權人設置優先受償權實屬不必要。但是其他法律制度不足以保護人身侵權債權人的權益時,我們可以考慮在破產清償順位中采用將人身侵權債權與勞動者債權同序的方式來保護人身侵權債權人的合法權益。
人身侵權債權;破產清償順位;次優制度選擇;非自愿性;剩余債務免除例外制度
一、問題的引出
三鹿“奶粉”對其大規模侵權而產生的人身侵權事件的處理結果引起了學者們的廣泛關注,受問題奶粉侵害的人身侵權債權人與普通債權人一樣所獲清償率為零。[1]若不是政府干預使侵權債權人獲得提前償付,受問題奶粉所侵害的人身侵權債權人利益將無“法”獲得保障。①三鹿集團事件中,對于侵權債權人的賠償,是由政府的行政干預下得以清償。
這時,人們不僅要質疑:是不是所有的侵權事件,最后都要以政府干預的形式來解決?那么,破產法的清償順位規定則有被政府行為旁落之嫌。而且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們消費生活對企業依賴性越來越大,從食品安全到缺陷產品等無不暗藏著侵權的危機,是不是所有破產企業的侵權之債都要由政府的行政干預?企業作為獨立法律主體,法律規定其應自主經營和自負營虧,政府干預行為顯然與法律規定的企業自負營虧的原則相違背,那么,對于三鹿“奶粉”事件之后的企業侵權,人身侵權債權人②文中所涉及的人身侵權債權人是指破產受理之前的債權人,而破產受理的之后的侵權債權人的債權被列為共益債務,享有優先權,這里不做為討論。應如何保障自己的合法權益,學者們從兩種不同的推演路徑予以探討:一種觀點是重新架構破產清償序位,賦予人身侵權債權優先權,韓長印學者從公共政策維度,分別以債權產生的自愿與非自愿為基點以及權利主體風險負擔及分散能力為切入點,探討了將侵權行為之債排序到國家稅款之后一般債權之前的可行性。[2]再如林一學者以羅爾斯的“給最少受惠者最大利益”為契點,認為如果擔保債權的設立發生于人身侵權之后,則人身侵權債權人甚至可以優先于擔保債權的債權人得以清償。[3]當然也有的學者建議采取固定比例優先方案,將有財產擔保債權額中一定比例的債權作為普通債權,將這個比例的有財產擔保的債權所對應的額度賦予人身侵權之債得以優先清償。[4]另一種觀點是建立或者完善相關法律制度,利用其他制度來保障人身侵權債權人人身權益。例如張新寶學者提出建立“大規模侵權損害救濟基金”,以基金的形式來保障人身侵權債權人的合法權益。[5]李敏學者從完善責任保險的維度提出對侵權債權人的保護。[6]陳年冰學者從懲罰性賠償制度的完善角度對人身侵權債權人予以相應的救濟。[7]更有學者從國家責任視角來探討人身侵權債權人的救濟。[8]
這兩種不同的思維進路所進行的法律制度改革,都會在一定程度上對人身侵權債權人予以某種程度上的保護。然而,法律制度是一種幅射性社會制度,一種制度的變革必然會引發各種利益主體的制度性 “蝴蝶效應”,也會產生不同層面的法律制度后果。尤其破產清算制度統攝了諸多法律和社會的愿望,涉及各種層面債權人利益——清算費用和共益債務的債權人,有擔保的債權人,無擔保的債權人,國家稅收,社會保險之債,勞動者債權等等,按照破產法的清算原理,前序債權人債權實現額的多少影響到后序債權人債權的實現,甚至同序債權人債權的實現直接影響到同序中其他債權人實現的比例。如果破產清償順位安排得當,則解決沖突各方利益主體利益保護問題,如果安排不得當,則會使本應在破產清償中得到保護的債權人的利益受損,有損法律的公平公正,畢竟一部法律制度可以讓紊亂的秩序變得和諧,也可以讓紊亂的秩序變得更加紊亂。
為此,我們需要思索的問題是,是在債權清償順位上進行重新排位的方式來保護人身侵權債權人利益,還是尋求其他制度的建立或完善來保護人身侵權債權人利益?雖然表面上來看,這兩個觀點并不沖突,而且立法可以從不同角度調整同一個問題,但是如果其他制度的建立或完善已經能夠很好的保護人身侵權債權人利益,那么立法者再挖空心思權衡破產清算的各方債權人權益,為侵權債權人尋找一個即能夠保護侵權債權人合法權益又不損害其他債權人的合法權益的支點,實在是無現實意義。
二、其他制度是否能夠完全保護人身侵權債權人的分析
由于人身侵權債權人的產生多數情況下是企業行為所致,為此,以企業相關制度為出發點,能夠使人身侵權債權人所遭受的損害獲得補救的制度主要有:法人人格否認制度,董事等高級管理人員責任追究制度,責任保險制度,剩余債務免除例外制度,懲罰性賠償制度,大規模侵權損害救濟基金制度等。本文以制度是否是我國現行法律制度為分類標準將上述制度分為現存制度和亟待建立的制度兩個層面進行分述之。
(一)現存制度的盤點
⒈法人人格否認制度。法人人格否認制度是為了制止股東濫用公司獨立法人人格,保護公司債權人的利益及社會公共利益,允許在特定情形下,否認公司獨立人格和股東的有限責任,責令公司控股股東對公司債權或公共利益承擔責任的一種制度。[9](p364)此種制度規定在我國現行《公司法》第20條第3款進行了相應的規定:“公司股東濫用公司法人獨立地位和股東有限責任,逃避債務,嚴重損害公司債權人利益的,應當對公司債務承擔連帶責任。”從公司法規定來看,法人人格否認制度對侵權債權人的保護只是提出了抽象制度的框架,至于該制度適用的具體情形,侵權債權人是否需要舉證,嚴重損害公司債權人這個嚴重尺度的衡量標準等等制度附屬問題并沒有給予相應的規定,這就可能使侵權債權人利益以此制度來維護權益存在或然性或偶然性。為此,我國公司法為了更好地保護債權人利益,應完善法人人格否認制度,以概括和列舉相結合的方式將公司人格否認的具體情形列出,使公司人格否認制度更具操作性。同時,也會減少股東將投資風險轉嫁給無辜的侵權債權人來追求企業經營的外部成本的動機。
⒉董事等高級管理人員責任追究制度。現行侵權責任法規定了用人單位對其工作人員執行職務的侵權直接承擔法律責任,對董事等高級管理人員的侵權責任的承擔沒有規定,反觀公司法也沒有相關制度的銜接,因為公司法主要以公司和股東為調整對象,因此,公司法中關于董事責任的設計側重于以董事對公司負有賠償責任為制度設計的出發點,如《公司法》第151條規定:“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執行公司職務時違反法律、行政法規或公司章程的規定,給公司造成損失的,應當承擔賠償責任。”也就是說,人身侵權債權人欲以現行法律為依據直接追究董事等高級管理人員的法律責任是不可能的,除非公司怠于行使債權,人身侵權債權人以代位權制度來追究董事等高級管理人員的法律責任。這種制度設計很可能增加董事等高級管理人員經營風險外部化的動機,同時也增加人身侵權債權人合法權益救濟成本,①相對于法律制度賦予人身侵權債權人直接訴權而言,代位權訴訟所需的訴訟成本還是較高的,其需要債權人雙重舉證,一是證明其與公司的債權存在,二是其需證明公司怠于行使權利的事實。對此,我們可以借鑒日本《商法典》第266條的相關規定,董事執行職務時有惡意或者重大過失時,對第三人承擔連帶賠償責任。英國《1986年破產法》也對董事對破產公司債權人承擔個人責任進行了詳細的規定。[10](p495)法律對債權人如此賦權,一方面增加董事違法責任的訴訟主體,進而加大債權人監督董事等高級管理人員行為的動因;另一方面減少董事履行職務時經營風險外部化的動機。
⒊責任保險制度。責任保險是以被保險人致人損害依法應當承擔損害賠償的責任為標的,由保險公司承保的一類保險。企業參加責任保險可以將本應由實施侵權行為的企業所承擔的責任轉移給保險公司,對于企業而言,其不至于因為巨額的侵權賠償費用而破產,對于人身侵權債權人來說,其可以通過保險司承擔責任保險義務的行為獲得部分救濟。由于責任保險的雙贏性質,我國現行保險法賦予侵權債權人直接對保險公司的賠償請求權。②保險法第65條規定,保險人對責任保險的被保險人給第三人造成的損害,可以依照法律的規定或者合同的約定,直接向第三人賠償保險金。但是責任保險對于企業而言,畢竟不是一種強制保險,為此,制度本身的消極因素使得人身侵權債權人可能無法依此來獲得相應的賠償。再有,企業即使購買保險,也可能傾向于不足額保險,人身侵權債權人也很難因企業參加責任保險就能獲得相對應的全額賠償,最后,保險人本身也存在無法準確衡量各公司的風險并設置一個有效合理的保費標準的技術難關。這也就是說,依現行保險法相關制度的規定,侵權債權人所應得到的賠償也很難全額實現。
⒋懲罰性賠償制度。懲罰性賠償制度對于侵權人而言,在某種程度上達到懲罰與威懾之功效;對于被侵權者來說,具有安撫和激勵作用,但是懲罰性賠償額度的確定是一個很有難度的技術問題,過低,無法發揮制度本身所應有的制度價值目標;過高,則可能遏制企業創新動機,不利于經濟發展,于是,各種法律在規定懲罰性賠償額度時,采取不同的立法態度,《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49條消費者購買商品的價款或者接受服務費用一倍的規定,《食品安全法》第96條支付價款10倍的規定,以及《侵權責任法》第47條非常謹慎地將懲罰性賠償限制在缺陷產品,并模糊地規定了額度——“相應的懲罰性賠償”。單從現行法律關于懲罰性賠償的額度的不確定這一點,我們不難推定依現行的立法技術,我們對懲罰性賠償的額度考量標準還不確定,那么該制度是否能夠妥當保障人身侵權債權人的合法權益,則不言自明。
(二)亟待建立制度的評析
⒈剩余債務免除例外制度。破產清償制度是一項具有多元價值目標的社會分配制度,強調破產企業債權人公平受償的同時,對破產企業的投資人債務免除。然而,有些個案中,債務免除有違法律的公平正義,為此,有些國家創設了剩余債務免除例外制度,即:根據破產法規定,某些特定債務屬于不可豁免的債務,不能在破產程序終結后獲得免除,而必須繼續進行清償。[11]我國2007年實施的破產法并沒有明確采取該制度。該制度有利于人身侵權債權人權益的保護,尤其現行社會的侵權,決大數都是企業明知的狀態下而為之。《美國破產法》第523條以列舉的方式對破產免責的例外進行了規定,其中規定了因故意或惡意損害他人身體或財力產生的債務不可免責。[12](p551)《日本破產法》 第253條也有相關規定,基于破產人以惡意施加的非法行為的損害賠償請求權以及基于破產人由于故意或重大過失而施加的損害人身生命健康的非法行為的損害賠償請求權屬于破產免責任許可的例外。[13](p832)
可見,破產免責任例外制度僅限于破產人以故意或惡意的方式產生的企業債務不可免責,然而,事實上,故意或惡意所產生的侵權只是人身侵權之債的一部分,還有其他主觀狀態,如過失或重大過失的侵權等。為此,該制度的適用還是存有一定的局限性的。
⒉大規模侵權損害救濟基金制度。救濟基金是指專項用于救濟和賠償大規模侵權事件的被侵權人身、財產損失的基金。[14]三鹿集團曾在政府的干預下,進行了類似救濟基金的實踐,三鹿集團向中國乳制品行業協會先期支付的9億元治療費用,包括三鹿集團在內的22家責任企業主動支付的2億元醫療賠償基金以及對死亡病例、重癥病例、普通癥狀進行賠償的費用等。[15]在德國、日本及我國的灣地區普遍設立了藥害救濟基金,規定由藥品企業根據市場份額或規定比例向基金繳納費用。[16]我們國家目前沒有專門的法律對救濟基金的籌建、管理以及賠償等問題進行相關規定。但是這種基金制度對于人身侵權債權人的保護也具有局限性,這種基金制度只針對大規模侵權損害,而現實中,不是所有企業的侵權都具備大規模。①雖然各國立法對于“大規模”的界定標準各異,有十人,也有五十人,但不管依據何種標準,總會有個別人身侵權債權人不在此限。
從上面的論證我們可以看出不同制度設計從不同維度對人身侵權債權人權益予以保護,但是這些制度本身都存在著制度的不自足性,以及相應的制度障礙,使得人身侵權債權人不可能依據這些制度得以完全救濟。這種客觀立法境地促使學者不得不將人身侵權債權人權益保護植入到破產清償順位中。
三、借鑒與建議:人身侵權債權人在破產清償順位中優先受償制度的建立
如前所述,以我國目前的制度供給無法消解人身侵權債權人因企業侵權行為所產生的損害。那么,就需要在企業退出市場制度的最后一道制度——破產清償制度的完善來保護人身侵權債權人的合法權益。然而,我們需要面對的問題是,破產清償制度如何完善才能更好地保護人身侵權債權人的利益。
(一)現行破產法對侵權債權人規定的分析
依據我國現行破產法的規定,排除有財產擔保的債權人行使別除權外,先扣除破產費用和共益債務,然后按下列順位清償,首先清償破產人所欠職工的工資和醫療、傷殘補助、撫恤費用,所欠所應當劃入職工個個賬戶的基本養老保險、基本醫療保險費用,以及法律、行政法規規定應當支付給職工的補償金;其次破產人欠繳的除前項規定以外的社會保險費用和破產人所欠稅款;最后是普通破產債權。從這個排序上我們不難看出人身侵權債權人受償序列同位于無財產擔保的合同之債。然而人身侵權之債具有合同之債所不具備的特有屬性及其內在的特殊救濟需求,即權利生成非自愿和所涉人的生存權。這兩種特性很可能使企業將投資的風險轉嫁給無辜的侵權債權人,進而產生企業經營的外部成本。[17]為此,現行破產法將人身侵權之債與無擔保的合同之債等同序位清償的規定不僅不利于人身侵權債權人的保護,而且還在某種程度上促使企業的經營者制度尋租,缺少減少侵權行為的制度動力。同時,這種將人身侵權之債等同于無財產擔保合同之債的清償順位安排,也與破產法價值目標——公平正義不相符。
(二)其他國家破產法相關規定的評析
反觀其他國家相關制度的規定,令人驚奇的是,對于人身侵權債權人在破產清償中的順位,多數國家與我們國家一樣,將其與無擔保的合同之債的債權人列為同序位的清償地位。如《美國破產法》規定擔保債權對特定擔保財產享有絕對優先權,然后以列舉的形式規定了哪些債權享有優先權,如破產管理費用、雇員工資和福利等等, 沒有將人身侵權之債列入其中。[18](p465-471)只是在鐵路公司的重整中將鐵路公司運營而造成的人身傷害或者死亡的債權列為優先債權,按照管理開支進行償付。[19](p679)以嚴謹著稱的德國也沒有對人身侵權債權在清償順位中做出特別規定,日本破產法對侵權債權的受償地位同樣沒有給予特別關注。
當然,有的國家的破產法特別規定了人身侵權之債的優先權,如俄羅斯的《支付能力法》第134條規定了債權的清償順序,其中除去各種費用外,首要順位就是債務人對其承擔生活或健康損害賠償責任的公民債權,并按照相應時間折算應付款,還賠償所造成的精神損害。并且,還在該條規范中,將享有抵押權的債權與侵權之債的債權再次進行排序,即如果侵權之債發生在抵押合同簽訂之前,侵權之債的債權優位于抵押權得以清償。[20](p271)
是什么原因導致多數國家,尤其工業發達國家,沒有對人身侵權之債做出特別規定?認真探究其他國家與之有關的制度,不難發現,這些國家存在另行救濟侵權之債的替代制度,并且這些替代制度彼此之間相互呼應,很好地保證人身侵權債權人的合法權益,如美國、日本等國家存在破產免責任例外制度,使侵權責任人不會因為企業破產而免除對侵權債權人的賠償責任。也就是說,雖然這些國家的破產法在破產清償順位中沒有給予人身侵權債權人以特別關注,但是由于其存在其他保護侵權債權人的制度,或者是其他保護侵權債權人的制度比較健全,足以在制度上抵銷了破產清償順位中對人身侵權之債的不利規定。而我們國家與之有關的制度還沒有完善到使人身侵權之債得以充分保護的程度,至于達到抵銷制度不自足性的負面影響之效,則更是微不足道。
(三)人身侵權債權人應與勞動債權同等序位的法理分析
鑒于我們國家目前法律制度的不健全,再加上人身侵權之債本身對法律制度需求的急迫性,我們在企業破產清償順位中應對侵權債權人予以救濟。問題是,我們將人身侵權之債受償順位安排在哪一點,既能滿足于人身侵權之債的保護,又不損害其他債權人利益,學者們從不同的角度進行了探討。
⒈有擔保的債權之前或與其同在一個序位。物權優于債權理論是人們千余年選擇的制度結果,雖然也有一些學者對此制度產生這樣或那樣的質疑,但有一點是肯定的,擔保法賦予債權人利用擔保方式來保障債權的實現,進而促進資金融通,具有增加社會整體福利的正外部性影響。破產法如果規定人身侵權債權絕對優先受償權,無異于將擔保法的期待權予以破壞。而且此規定也會使法律陷入自我矛盾的漩渦之中,一方面依據擔保法,人們可以通過擔保的約定來保證自我債權的完全實現,另一方面依據破產法又否定了這種合同約定,那么,人們應該以哪個法為行為基礎?
再有,如果有擔保的債權位于人身侵權債權之后得以清償,以銀行為主導的債權人就會對哪些容易侵權的企業或者具有潛在侵權的企業減少貸款或者不貸款,這種抵御性選擇很可能使一些風險行業無人問津,不利于經濟的發展。至于將人身之債與有擔保的債權在同一序位,筆者持不贊成態度,表面上看,似乎保護了侵權之債的合法權益,實質上,有擔保的債權人完全可以讓債務人提高擔保額度等方式減少侵權之債的受償額度,并且這種規定與后序的勞動債權中的某些相似債權的清償相沖突,從而影響法律的公平公正。
⒉勞動債權之前或與其同在一個序位。按照我國破產法規定,勞動債權包含以下內容:職工的工資和醫療、傷殘補助、撫恤費用,所欠所應當劃入職工個個賬戶的基本養老保險、基本醫療保險費用,以及法律、行政法規規定應當支付給職工的補償金,這些內容都關涉勞動者的最基本生活和生存利益,并且與人身侵權之債一樣具有生存權屬性和非自愿屬性,為此有些學者建議人身傷害賠償債權應與勞動債權處于同一優先順位。[21](p265)筆者比較贊同這種觀點,因為勞動債權也附有人身屬性,例如傷殘補助和撫恤費用產生的基礎是勞動者所在的用人單位或用人單位的財產侵犯了勞動的身體健康權,也屬于侵權之債,如果將此侵權之債置于勞動債權之前得以清償,很可能形成這樣局面,某企業的雇工因企業財產造成的人身侵權得到提前清償,而同樣在企業工作的勞動者也遭遇同樣的法律事實,僅因為制度的不同安排,而得到不平等的清償。這種清償安排有違破產法追求的最高價值目標——“公平原則”。
排序分析到此,再進行將人身侵權之債插序到后面的債權的討論,已無實際意義。尤其是有些學者將人身侵權之債放到稅收債權之后,無擔保債權之前的序位安排,與現行立法的“國不與民爭利”的私權優先原則嚴重沖突。
四、結論:契合侵權侵權人需求的制度重構或建立
人身債權所面臨的上述制度的改革決不是孤立的、偶發的,很大程度上可能互為因果。但不論是完善上述某一制度,還是某些制度多管齊下,法律制度本身的不自足性和負外部效應是無法克服的。為此,筆者認為,以完善其他法律制度的方式使人身侵權債權人的合法權益得以全面救濟,為人身侵權債權人權益保護的制度最優選擇,畢竟其他制度所涉及的是某一個層面的權益保護,而不像破產清償制度,在不同的利益主體之間找尋各方主體可接受的平衡點,并以此為基點將不同層面的利益主體的權益進行排序。為此,如果其他制度足以保護侵權債權人權益,我們沒有必要再糾結于人身債權的清償順位,正如有的學者所言,破產企業所余破產財產價值通常很有限,在實現某些法定優先權后常所剩無幾,此時再規定復雜的清償順序,客觀上也無實際意義。[22]
但是,在其他制度的完善或建立這一點上,我們還不得不考慮一些制度建設問題,制度的建立或完善受到當下的社會法制環境、社會需求因素、經濟條件以及其他國情等等外部因素的制約,為此,很多制度從應然到實然還需很長的制度建設期,可是侵權債權人需要相應制度跟進來保護這類群體的合法權益卻迫在眉睫。
那么,在現有其他制度不能完善以及相關的其他制度無法建立的情況下,重構破產清償順位以保護人身侵權債權人合法權益也是一種不失法律公平與正義的次優制度選擇。與此同時,我們不容忽視的是,這種正義的追求也可能鑄成非正義生成的契機,因為無論將人身侵權債權人放到哪一個清償順位都可以隱含一項悖論,那就是犧牲后序債權人利益為破產企業的非法行為“買單”。
然而,我們不能因為制度本身內含此悖論而否定該制度,制度本身可能處于這樣一種狀況,一個制度中的一個或幾個規范可能是不正義的,或者制度本身是不正義的, 而置于整個社會體系卻并非如此。[23](p44)為此,對于人身債權人置于破產清償順位這事法律制度的改革,我們需要正視制度本身的利益沖突性,當一個制度本身隱含著利益沖突時,任何一種選擇都意味著付出某種代價,我們只能從自然正義或社會正義的維度,通過利益平衡,盡可能將這種代價的負面效應減損到最小。
[1]三鹿破產 結石獲賠無望[N].廣州日報,2009-11-29(A2).
[2]韓長印.破產優先權的公共政策基礎[J].中國法學,2002,(03):39.
[3]林一.侵權債權在破產程序中的優先受償順位建構——基于“給最少受惠者最大利益”的考量[J].法學論壇,2012,(02):152.
[4]韓長印,韓永強.債權受償順位省思[J].中國社會科學,2010,(04):112.
[5][14]張新寶.設立大規模侵權損害救濟(賠償)基金的制度構想[J].法商研究,2010,(06):23-24.
[6]李敏.風險社會下的規模侵權與責任保險的適用[J].河北法學,2011,(10):09-16.
[7]陳年冰.大規模侵權與懲罰性賠償[J].西北大學學報,2010,(06).
[8]林丹紅.大規模人身損害侵權救濟中的國家責任 [J].法學,2009,(07).
[9]趙旭東.新公司法制度設計[M].法律出版社,2006.
[10]Vanessa Finch,Corporate Insolvency Law:Perspective and Principles[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
[11][16]林一.侵權債權人在破產程序中受償地位之重塑理由[J].法學,2010,(11):65.
[12][13][19][20]李飛.當代外國破產法[M].中國法制出版社,2006.
[15]崔曉紅.三鹿破產,“后事”難了[J].新財經,2009,(02).
[17]馬東.論應當賦予侵權債權在破產分配中以優先地位[J].法學雜志,2012,(02):140.
[18]David G.Epstein.美國破產法[M].韓長印等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
[21]丁文聯.破產程序中的政策目標與利益平衡[M].法律出版社,2008.
[22]許德風.破產法基本原則再認識[J].法學,2009,(08):55.
[23](美)約翰·羅爾斯.正義論[M].何懷宏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
(責任編輯:張雅光)
Analysis on the Priority Right for Personal Tort Claims in the Bankruptcy Liquidation Sequence
Zou Yang,Rong Zhenhua
in the any system of adjustment of personal tort claims,the system which legislation look for pay off point for personal tort claims in the bankruptcy liquidation sequence is the second system selection.Because whatever personal tort claims locate,the behind sequence creditor pays for the bankrupt enterprise illegal behavior.Therefore,if the other legal system enough to protect the rights of personal tort creditor,we set the priorities right under Bankruptcy Liquidation sequence for personal tort creditor,which is really unnecessary.But other legal system does not do enough to protect the rights of personal tort creditor,we may consider the same way to protect personal tort creditors and the employee in the bankruptcy liquidation sequence to protect the legal rights of the personal tort creditors.
Personal tort claims;Bankruptcy liquidation sequence;Subprime system choice;The involuntary;Remaining debt relief exception system
D922.291.92
A
1007-8207 (2012)08-0090-05
2012-06-16
鄒楊 (1965—),女,東北財經大學法學院教授,研究方向為社會法、國際商法;榮振華 (1977—),女,遼寧鐵嶺人,西南政法大學博士研究生,東北財經大學津橋商學院法律系主任,講師,研究方向為民商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