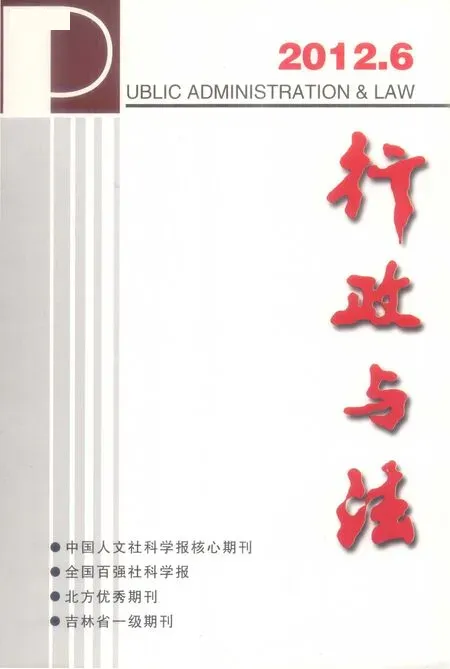論“涉眾型”經濟犯罪被害人經濟權利救濟的困境及出路
□ 重慶市大足區人民檢察院課題組
(重慶市大足區人民檢察院,重慶 402360)
論“涉眾型”經濟犯罪被害人經濟權利救濟的困境及出路
□ 重慶市大足區人民檢察院課題組
(重慶市大足區人民檢察院,重慶 402360)
辦理 “涉眾型”經濟犯罪案件的重點和難點在于如何最大限度地為被害人挽回經濟損失。對 “涉眾型”經濟犯罪被害人經濟權利進行救濟,須重構防范與保全結合型的財產控制機制、建構特殊類型案件民事救濟程序獨立于刑事訴訟程序的運行機制、建立健全長效機制破解民事賠償判決執行難、構建恢復性司法理念指導下的被害人救濟三元刑事訴訟模式、建立 “涉眾型”經濟犯罪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
“涉眾型”經濟犯罪;被害人;經濟權利;救濟
“涉眾型”經濟犯罪,是指涉及眾多受害人,特別涉及眾多不特定受害群體的經濟犯罪。主要包括非法吸收公眾存款、集資詐騙、傳銷、非法銷售未上市公司股票等犯罪活動。另外,在證券犯罪、合同詐騙犯罪、假幣犯罪、農村經濟犯罪活動中,也有類似涉眾因素存在。[1]在“涉眾型”經濟犯罪中,受害人人數眾多,極易引發集體上訪及其他群體事件。盡管被害人有著各種各樣的訴求,但在追回被騙財物、減少損失等方面往往有著相同或類似的訴求。從司法實踐中審理“涉眾型”經濟犯罪案件的情況來看,辦理“涉眾型”經濟犯罪案件的難點和重點不在于如何對涉嫌犯罪的單位和個人準確定罪量刑,而在于如何最大限度地為被害人挽回經濟損失。
一、“涉眾型”經濟犯罪被害人的界定
(一)相關問題的提出
⒈被害人與犯罪人界限模糊。在“涉眾型”經濟犯罪中,一些最初屬于被害對象的被害人,隨著事件的發展,為獲取所謂的“利潤”,往往介紹、吸收他人參與其中(如傳銷案、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其地位由原來的被害人轉變為犯罪分子的“幫兇”,更有嚴重者可能成為犯罪人。他們在介紹、吸收他人參與其中的同時,自己也有大量資金投入,案發時這些人的損失往往還大于其他被害人,從而使得被害人與犯罪人之間界限模糊。
⒉被害人與證人的訴訟身份難以界定。在 “涉眾型”經濟犯罪中,部分被害人的利息及本金已收回或部分收回,而絕大部分被害人的本金則分文未收回。前者的個人利益未遭受侵害或只遭受部分侵害,后者的個人利益受到了犯罪行為的侵害。在司法實踐中,以何種標準區分被害人與證人的訴訟身份難以確定。
⒊存在“自愿被害人”。由于“涉眾型”經濟犯罪案件具有被害人人數眾多、波及面廣、社會影響大的特征,政府為了安撫受害人,維護社會穩定,往往會從財政拿出部分資金彌補被害人的損失。這種做法雖然從一定程度上保護了被害人的權益,但也給部分被害人帶來誤解,認為虧了還有政府作為靠山,不再是簡單的被騙,有的則是自愿地把錢拿給犯罪分子,成為“自愿被害人”。
(二)“涉眾型”經濟犯罪被害人的界定
“涉眾型”經濟犯罪被害人,是指正當權利或合法利益遭受“涉眾型”經濟犯罪行為侵害的人。
⒈對于明知對方是實施“涉眾型”經濟犯罪行為而參與實施犯罪或者幫助其實施犯罪的被害人,即使其利益受到損害,也不應作為實體意義的被害人,因為這些被害人是在犯罪的過程中被害的。
⒉應當根據其是否明知對方行為的非法性來界定其訴訟地位。如果明知對方的行為是非法的,但為了獲取高額利息等非法利益而遭受損失的,不應作為實體意義上的被害人,只能以證人的身份參加訴訟。只有在行為人確實不明知對方的行為是非法的,為獲取合法較高額的利息等利益而受害的,才能作為實體意義上的被害人,以被害人的身份參加訴訟。
⒊“自愿被害”實質上是一種尋租行為,“自愿被害人”在主觀上不再是簡單的“被騙”,而是利用他人的犯罪行為謀取形式合法而實質非法的個人利益,利用國家的為民舉措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這類人不但自己主動“被騙”,還編織光環讓其他人受騙,對這類人不應作為實體意義上的被害人予以保護。
二、“涉眾型”經濟犯罪被害人經濟權利救濟的困境
(一)傳統的偵查措施在保全資產、挽回損失方面存在固有的缺陷
刑事訴訟法規定了偵查機關具有搜查、扣押、查詢、凍結等偵查措施,通過這些措施,偵查機關可以固定證據、保全贓款贓物,防止贓款贓物被非法轉移、隱匿、變賣,為指證犯罪和贓物的最終處理奠定基礎。但扣押和凍結措施僅限于可以用于證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無罪的各種財物,對犯罪嫌疑人的其他財物是禁止扣押和凍結的。而“涉眾型”經濟犯罪涉及到被害人由于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為遭受經濟損失的救濟問題,如果犯罪嫌疑人的財產未及時被控制保全,犯罪嫌疑人或其家屬往往會將其財物轉移、隱匿或揮霍,致使受害方的損失難以挽回。
(二)現行立法下被害人權利實現方式存在缺陷
按照我國《刑事訴訟法》第77條的規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為而遭受物質損失的,在刑事訴訟過程中,有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范圍問題的規定》第5條規定,“……經過追繳或者退賠仍不能彌補損失,被害人向人民法院民事審判庭另行提起民事訴訟的,人民法院可以受理。”上述司法解釋出臺后,法院一般對單純侵財類案件的被害一方提起附帶民事訴訟不予支持,被害人只能寄希望于司法機關的追繳、退賠,或者向法院另行提起民事訴訟。然而,被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訴訟,需要支付各種訴訟費,包括預付案件受理費、申請財產保全與申請法院執行判決交納申請費、向法庭請求證人出庭作證及申請鑒定等需要支付證人的差旅費、誤工補貼、鑒定費等。盡管法院判決確定案件受理費、申請執行費由敗訴方負擔,但法院并不向原告退還,而是在判決中判令被告向原告給付,這無疑又讓被害人雪上加霜。
(三)刑事附帶民事或另行提起民事訴訟賠償判決執行難容易導致被害人的“二次被害”
當“涉眾型”經濟犯罪的被害人通過司法機關的追繳、退賠仍不能挽回損失而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或向法院另行提起民事訴訟時,雖然被害人大多能勝訴,但由于“涉眾型”經濟犯罪獨特的生成運行機理,此類犯罪多由資金鏈斷裂而案發,絕大多數犯罪案件的被害人因為各種原因無法從犯罪人處獲得充分的賠償,“空判”現象大量存在,判決執行困難重重。司法實踐中的民事賠償執行難問題,已經嚴重影響著刑事司法判決的公正性和權威性。刑事附帶民事或另行提起民事訴訟賠償判決執行難,導致被害人在經歷了一次犯罪行為的傷害后,又要經歷一次“法律白條”的心理與經濟的雙重傷害。
(四)“先刑后民”原則導致部分特殊類型案件不能及時獲得民事救濟
在“涉眾型”經濟犯罪中,犯罪分子為了編織資金實力雄厚的假象,也會利用詐騙或集資錢財從事一些正常的民商事活動。犯罪分子的違法犯罪活動與正常的民商事活動交織在一起,形成刑民交叉。“先刑后民”原則是司法實踐中形成的處理刑民交叉案件的一種方式。[2]然而,在刑事訴訟過程中,如果出現影響刑事訴訟正常進行的某種障礙,訴訟進程將被暫時停止。依照“先刑后民”原則,刑事被害人只有犯罪人在案并被定罪量刑才能獲得民事救濟,當刑事案件短時間內得不到偵破或訴訟中止時,刑事被害人的經濟權利不能得到及時的保障。同時,部分刑事案件因為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條的規定,由于公安機關撤案或檢察機關酌定不起訴而無法進入刑事審判程序,刑事案件未進入刑事審判程序就意味著刑事被害人無法啟動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程序而從犯罪人處獲得賠償。
(五)被害人請求國家救助權的缺失
司法實踐中,“涉眾型”經濟犯罪的犯罪分子貪利性強,涉案金額巨大,且往往因資金鏈斷裂而案發,損失一般難以挽回,即使追回了部分贓款,但由于受害群體人數眾多,往往存在“僧多粥少”的現象,遠遠不能彌補受害人遭受的實際損失,且犯罪人也沒有其他個人財產可供執行,因此有的被害人在遭受“涉眾型”經濟犯罪侵害后,傾盡家產、負債累累,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國外在刑事被害人救助方面都有健全的立法體制保障,但大多對救助對象的范圍作了一定的限制,把被害人的范圍限于因故意的暴力犯罪遭受人身傷害或死亡后果的被害人。[3]我國在刑事被害人救助方面雖然也出臺了一些相關的規范性文件,但至今未通過立法建立起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且這些規范性文件均將被害人的范圍限于人身受到傷害的被害人。
三、“涉眾型”經濟犯罪被害人經濟權利救濟的出路
(一)重構防范與保全結合型的財產控制模式
“涉眾型”經濟犯罪被害人人數眾多的特點決定了其必須破解傳統的財產控制措施,重構適合“涉眾型”經濟犯罪的財產控制措施。對此,一些發達國家在偵查階段對犯罪嫌疑人的財物,采取防范與保全結合型(即扣押與犯罪有關的物證和扣押賠償損害物相結合型)的控制措施。如意大利刑事訴訟法專章規定了對與犯罪有關的物的預防性扣押和保全性扣押。[4]因此,我國可以借鑒國外防范與保全結合型的控制措施,為了最大限度地為挽回被害人的損失,偵查機關在辦理“涉眾型”經濟犯罪立案之時,對可以用于證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無罪的各種財物采取查封、扣押、凍結等偵查措施的同時,依法對犯罪嫌疑人及其利益關系人(包括非善意取得第三人)的財產進行先行保全,在防止用來指證犯罪的證據喪失的同時,從源頭堵塞犯罪嫌疑人及其親屬在案發后為逃避經濟賠償和制裁而變賣、轉移、隱匿犯罪嫌疑人個人財產的漏洞,確保有關賠償判決順利執行,保證被害人的損失得到最大限度的挽回。
(二)建構特殊類型案件民事救濟程序獨立于刑事訴訟程序的運行機制
在我國,特殊案件包括三大類:第一類是由公安機關、檢察機關依法對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責任做出實質認定的案件,即公安機關、檢察機關依照《刑事訴訟法》第15條的規定,對法律規定免予追究刑事責任的案件作出撤銷或不起訴決定的案件;第二類是刑事案件因證據不足等原因短時間內得不到偵破的案件;第三類是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逃、缺席或者喪失訴訟能力等情形而導致久拖不決的案件。在“涉眾型”經濟犯罪中,應打破傳統的“先刑后民”原則,在現行刑事訴訟程序的運作過程中,應建構特殊類型刑事賠償案件中民事救濟程序獨立于刑事訴訟程序的運行機制。具體而言,對第一類案件,公安機關、檢察機關應采取退贓的形式返還被害人的合法財產,經返還后仍不能彌補被害人的經濟損失的,應允許被害人單獨提起民事訴訟的權利;對第二類和第三類案件,法國刑事訴訟法典第567條規定,如果被告人未能捕獲或未到庭,應該缺席審判。[5](p350)我國可以借鑒國外的做法,對因證據不足等原因短時間內得不到偵破的 “涉眾型”經濟犯罪案件,以及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逃、缺席或者喪失訴訟能力等情形而使案件久拖不決時,允許法院采取“先民后刑”的原則,對附帶民事部分進行缺席審判。一旦法院經過主體資格審查并支持被害人的訴訟請求時,應及時采取查封、扣押、凍結等措施強制執行被告人的財產,以補償被害人因被告人的犯罪行為所遭受的損失。
(三)建立健全長效機制破解“涉眾型”經濟犯罪民事賠償判決執行難
“涉眾型”經濟犯罪民事賠償判決執行難,不僅不利于被害人受損權益的恢復,而且嚴重破壞了法律的權威。破解“涉眾型”經濟犯罪民事賠償判決執行難問題,需要建立健全相關長效機制。
⒈建立預審時財產申報與登記制度。借鑒民事執行程序中被執行人財產申報制度,要求“涉眾型”經濟犯罪的犯罪嫌疑人在偵查機關預審時如實申報全部財產情況,偵查機關依據其申報,將被告人有價值的財產線索記錄在案,隨案移送,同時將被告人的財產申報情況作為其認罪態度的一部分記錄在案,在量刑時予以考慮。
⒉建立犯罪嫌疑人家屬財產來源審查制度。“涉眾型”經濟犯罪分子往往在案發前轉移、隱藏或將自己的財產登記在他人名下,導致民事賠償判決執行難。為最大限度地挽回被害人的經濟損失,應建立被執行人家屬財產來源審查制度。偵查機關在立案之初就應對涉嫌“涉眾型”經濟犯罪的犯罪嫌疑人的家屬財產進行審查,一旦查實該財產確屬被執行人所有,應采取防范與保全結合型的控制措施,確保民事賠償判決順利執行。
⒊適當引入先予執行制度。在“涉眾型”經濟犯罪中,一些被害人因犯罪分子的犯罪行為導致經濟利益嚴重受損而生活陷入極度困境,而案件從偵破到判決周期較長,如不予以先行發還部分損失,后果將十分嚴重。因此,建議借鑒民事訴訟中的先予執行制度,對因“涉眾型”經濟犯罪而致生活極度困難的被害人先予返還部分錢財,在最終的執行中按照判決書確定的內容確保與其他被害人利益的平衡。
⒋嘗試建立財產舉報獎勵制度。在“涉眾型”經濟犯罪案件中,可以根據實際情況,借鑒對犯罪嫌疑人的線索舉報獎勵制度,對“涉眾型”經濟犯罪嫌疑人的不法財產或個人財產進行舉報獎勵,努力搜集犯罪分子的財產線索,鼓勵受害群眾或其他群眾查找贓款贓物。
⒌引進財產監管托管制度。一些“涉眾型”經濟犯罪分子,往往有自己經營的合法公司和相關項目,一旦對這些公司和項目采取強制措施和保全措施,將不利于被害人權益的保護。偵查機關在偵查階段就應對犯罪嫌疑人名下能托管的資產依法進行托管,一方面可以保證涉案財產保值增值,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出現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屬轉移財產等行為,最大限度地保值增值涉案資產。
⒍設立公告程序,建立被害人代表制度。在查處“涉眾型”經濟犯罪案件的過程中,可以借鑒民事訴訟中的公示催告程序設立公告程序。公安機關立案后,在犯罪嫌疑人實施犯罪活動的區域內,采用公告的方式督促被害人在一定期限內參與到訟訴中來,最大可能地一次性解決問題。同時,由于“涉眾型”經濟犯罪案件涉案人數眾多,可參照民事訴訟法中的訴訟代表人制度,由被害人推選代表定期召開被害人會議,建立制度化、理性化的溝通渠道,由司法機關及時公開相關信息,咨詢被害人集體意見和建議,增加執行透明度。
⒎建立長效追贓機制。贓款的追繳工作直接關系到被害人的切身利益,因此有必要建立長效追贓機制,從追贓主體、追贓程序等方面進行完善,使追贓活動不因案件審查起訴或判決而停止,不因被告人被交付執行而停止。在刑事附帶民事判決生效后,無論是服刑期間或是刑滿獲釋后,在任何時間發現被執行人有可供執行的財產時,司法機關都可以隨時繼續執行,讓被執行人最大限度地賠償被害人受到的損失,直到被執行人全部承擔賠償義務為止。
(四)構建恢復性司法理念指導下的被害人救濟三元刑事訴訟模式
傳統的刑事訴訟是以犯罪人和國家為中心的,對被害人權益未給予充分重視。“涉眾型”經濟犯罪涉及眾多被害人的利益,其處置的難點和重點不在于如何對涉嫌犯罪的單位和個人準確定罪量刑,而在于如何最大限度地為被害人挽回經濟損失。因此,“涉眾型”經濟犯罪應打破傳統的“犯罪人-國家”二元刑事訴訟模式,構建恢復性司法理念指導下的“犯罪人-被害人-國家”三元刑事訴訟模式。恢復性司法的核心是,有關機構在認真聽取犯罪者、受害者、社區各方意見的基礎上,綜合考慮各方的愿望和訴求,力圖恢復被犯罪所侵犯的原狀,代之以經濟性的賠償,將犯罪被害人的損失減少到最低限度。[6]恢復性司法理念指導下的被害人救濟三元刑事訴訟結構能較好地兼顧犯罪人、被害人、國家三者的利益,可以適用于“涉眾型”經濟犯罪的偵查、審查起訴、審判、刑罰執行各階段。在公安機關立案前后、檢察機關審查起訴和法院審判三個階段中符合適用條件且當事人有調解或和解意愿的,司法機關可以自行或委托人民調解組織進行調解,經調解達成調解或和解協議的,司法機關可以分別作出撤銷案件、不起訴、免于刑事處罰的決定,以有利于調解結果的實現。對被告人在審判前主動、自愿向司法機關全面交付可執行財產時,或協助司法機關配合追繳形式上無法辨析權屬性質的財產時,應當從量刑情節、處罰刑檔等方面對被告人予以從輕、減輕或免除處罰。在刑罰執行過程中,對仍拒不退贓、退賠的被告人,應嚴格限制、謹慎適用減刑、假釋等制度,但對于積極、有效進行退贓、退賠的被告人,應放寬減刑、假釋的幅度。
(五)建立“涉眾型”經濟犯罪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
“涉眾型”經濟犯罪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是指當“涉眾型”經濟犯罪司法救濟程序終結之后,由于犯罪人原因導致的生效刑事司法裁判中認定的民事賠償得不到實現,以及刑事被害人因為其他原因而沒有通過司法救濟程序得到應有的賠償,此時由代表國家的專門機構給予刑事被害人物質救濟的制度。建立 “涉眾型”經濟犯罪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使被害人的權益不僅從法律形式上(判決上)得到體現,更重要的是在實質上(物質上)得到補償和恢復,為通過司法救濟程序仍然難以彌補損失的被害人提供看得見、摸得著的物質上的補償幫助。同時,通過國家救助制度,對“涉眾型”經濟犯罪司法判決“執行難”的問題進行救濟,有利于維護司法判決的權威性和強制性,有利于增強法律的權威,也有利于避免將被害人推向社會的對立面,從而促進社會的和諧穩定。“涉眾型”經濟犯罪被害人國家救助制度只有刑事司法救濟程序結束之后,并且刑事被害人沒有通過司法判決或其他途徑獲得相應的賠償時才能啟動救濟程序。救助的對象限于“涉眾型”經濟犯罪造成嚴重經濟損失,無法維持或短時間內無法維持家庭基本生活的被害人。此外,在具體構建時應明確規定救助的主體、范圍、標準、方式、數額和程序。
[1]嚴打涉眾型犯罪[EB/OL].新浪網,http://news.sina.com.cn,2006-11-24.
[2]王學堂.“先刑后民”并非絕對[N].檢察日報,2011-02-23(06).
[3]陳彬,李昌林.論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J].政法論壇,2008,(04):55.
[4]黃怡.試論在經濟犯罪案件偵查中贓款贓物認定和追繳的法律問題[J].江西公安專科學校學報,2001,(02).
[5]謝佑平,萬毅.刑事訴訟法原則:程序正義的基石[M].法律出版社,2002.
[6]李衛紅,孫長春.犯罪被害人的經濟救濟[J].當代法學,2007,(05):49.
(責任編輯:王秀艷)
Research about Difficulties and Solutions of Economic Rights Relief for Victims of Economic Crime Related to Numerous Suspects
Research Group of People's Procuratorate of Dazu County,Chongqing Municipalities
The difficulty and the emphasis of tne Economic crime related to numerous suspects is on how to maximize the economic losses for the victim to restore.Economic Rights Relief for Victims of Economic Crime Related to Numerous Suspects need to reconstruct the property control mode of combination of prevent and preservation,to construct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of civil relief procedure in independent of criminal procedure about special type case,to establish and improve the long-term mechanism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execution of the civil compensation decision,to construct the victim relief ternary mode of criminal proceeding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concept of restorative justice,establish the victim state aid system of economic crime related to numerous suspects.
Economic crime related to numerous suspects;Victims;Economic Rights;Relief
D924.11
A
1007-8207(2012)06-0126-04
2012-03-16
課題組成員:孟傳香 (1977—),女,重慶人,重慶市大足縣人民檢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主任,助理檢察員,碩士,研究方向為刑法;孫志華 (1980—),女,河北人,重慶市大足區人民檢察院研究室副主任;石瑩蕓 (1982—),女,重慶人,重慶市大足區人民檢察院研究室干警。
本文系2011年度重慶市人民檢察院重點課題 “‘涉眾型’經濟犯罪研究”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