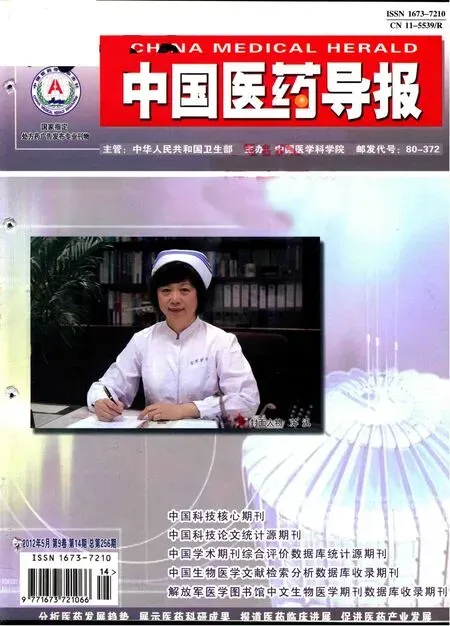堿性成纖維細胞生長因子和血管內皮生長因子在結腸癌表達的相關性及其臨床意義
劉士君 李建華
1.遼寧中醫藥大學附屬第三醫院病理科,遼寧沈陽 110003;2.中國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病理科暨中國醫科大學基礎醫學院病理教研室,遼寧沈陽 110001
結腸癌是消化道常見的惡性腫瘤之一,20世紀90年代以來,發病率呈明顯上升趨勢[1-2]。影響結腸癌預后的因素很多,血管生成在腫瘤生長、轉移中發揮重要作用。本研究采用免疫組織化學SP法,檢測85例結腸癌標本中堿性成纖維細胞生長因子(basic fibroblast growth factor,bFGF)和血管內皮生長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的表達情況,以探討bFGF和VEGF表達的相關性及其臨床意義。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材料
收集遼寧中醫藥大學附屬第三醫院2007年10月~2011年10月間85例外科手術切除結腸癌標本,所有患者術前均未接受放療或化療,所有研究對象均按HE病理切片診斷標準確診為結腸癌,年齡32~81歲,平均51.6歲,其中,男59例,女26例;伴淋巴結轉移52例,不伴淋巴結轉移33例;組織學分型:高分化32例,中分化15例,低分化38例;TNM分期:Ⅰ~Ⅱ期40例,Ⅲ~Ⅳ期45例。
1.2 方法
標本經4%甲醛固定,常規石蠟包埋,4μm連續切片,分別進行HE染色和免疫組織化學SP法染色,兔抗人的bFGF和VEGF抗體購自福州邁新生物技術開發有限公司,并設立陽性和空白對照。
1.3 結果判定
bFGF和VEGF表達均定位于細胞漿,胞漿染有明顯的棕黃色為陽性,胞漿無著色為陰性。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10.0統計學軟件進行數據分析,計數資料用率表示,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采用Spearman檢驗進行兩變量間的相關性分析。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bFGF和VEGF在結腸癌的表達情況
bFGF和VEGF在男性結腸癌的表達陽性率分別為64.4%、62.7%,女性結腸癌的陽性表達率分別為69.2%、65.4%,包漿均有明顯的棕黃色染色(圖1、2),不同性別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bFGF和VEGF在高、中、低分化結腸癌的陽性表達率依次為59.3%和56.2%、66.7%和60.0%、71.1%和71.0%,各組間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bFGF和VEGF在TNMⅠ~Ⅱ期和Ⅲ~Ⅳ期陽性表達率分別為37.5%、50.0%和91.1%、75.6%,組間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圖1 低分化結腸癌標本中bFGF的陽性表達(×200)

圖2 中分化結腸癌標本中VEGF的陽性表達(×400)

表1 bFGF和VEGF在85例結腸癌標本的表達與臨床病理特征的關系[n(%)]
2.2 bFGF和VEGF表達的相關性
bFGF和VEGF表達的相關性見表2。用Spearman檢驗進行兩變量間的相關性分析表明,bFGF和VEGF結腸癌的表達呈正相關(r=0.268,P<0.05)。

表2 bFGF和VEGF的表達情況(例)
3 討論
惡性腫瘤的發生、發展機制涉及腫瘤細胞遺傳物質、表面結構、侵襲力、黏附力、血管新生、淋巴管新生等諸多因素[3]。目前許多研究資料發現,新生血管的形成在腫瘤的生長、轉移中發揮重要作用,惡性腫瘤細胞憑借豐富的新生血管網獲取無限生長所需要的營養和氧氣,因此,腫瘤的血管生成以及以血管為靶向的藥物研究成為腫瘤研究領域的熱點之一[4]。已經發現越來越多的因子與腫瘤血管生成有關[5]。
bFGF是廣泛存在于體內多種組織的一類多肽生長因子,在機體的胚胎發育、血管形成、創傷修復過程中起重要調節作用。近年來研究發現,bFGF在肝癌、肺癌、膠質瘤、黑色素瘤中都有較高表達[6]。本實驗研究表明,bFGF在大腸癌中有異常表達,與性別、組織分化程度無關,與臨床分期、淋巴結轉移情況密切相關。
VEGF屬于血小板源生長因子超家族,為分子量46 000的高度糖基化堿性蛋白,可通過蛋白激酶C(PKC)或ras信號傳導通路激活絲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AKP)系統,刺激內皮細胞增殖,并產生纖維蛋白溶解酶原激活劑和膠原酶等[7],增加微血管通透性[8],促進血漿纖維蛋白滲出,為血管中多種細胞的遷徙提供纖維網絡,從而促進血管形成和腫瘤細胞脫落進入血管或向鄰近纖維結締組織擴散。VEGF在正常情況下表達水平較低,在一些病理情況下出現過表達。本研究表明,VEGF在大腸癌中的異常表達與性別、組織分化程度無關,與臨床分期、淋巴結轉移情況密切相關。
本研究結果顯示,bFGF和VEGF在結腸癌的表達呈正相關關系(r=0.268,P<0.05),二者共同參與了結腸癌浸潤和轉移的過程,相互的協同作用可以使結腸癌更具侵襲性。因此,聯合檢測bFGF和VEGF在大腸癌中的表達,可以作為評估結腸癌預后的客觀指標,對指導臨床診斷和治療具有一定的意義,可能作為腫瘤靶向治療的新靶點,通過某種技術抑制bFGF和VEGF高表達,可實現緩解病情甚至治療結腸癌的目的,減少復發和轉移。
[1]李穎超,張觀宇,許立莉.CD105和VEGF在大腸癌中的表達及意義[J].中國誤診學雜志,2010,10(36):8878.
[2]張娟,魏君,王士杰,等.Twist和E-cadherin在大腸癌組織中的表達及臨床意義[J].中國腫瘤臨床,2011,38(3):143-147.
[3]謝明,楊翅,梁紅,等.大腸癌中pAkt、VEGF和MVD的檢測及其臨床意義[J].診斷病理學雜志,2009,16(5):337-339.
[4]蔣金玲,劉衛仁,于穎彥,等.腫瘤學管形成的模型建立與顯微圖像定量分析研究[J].中華病理學雜志,2011,40(7):475-479.
[5]于建憲,崔琳,張七一,等.組織芯片檢測大腸癌中NOS、HIF-1α的及與血管生成的關系[J].診斷病理學雜志,2007,14(1):44-49.
[6]Okada-Ban M,Thiery JP,Jouanneau J.Fibroblast growth factor-2[J].Int J Biochem,2000,32(3):263-267.
[7]胡艷萍,呂彧,崔莉,等.血管內皮生長因子及其受體在胃腸間質瘤中的表達[J].診斷病理學雜志,2007,14(5):381-382.
[8]鄭剛,劉建生,智仁厚.結締組織生長因子、血管內皮生長因子、缺氧誘導因子-1α在胰腺癌中的表達及臨床意義[J].中國醫藥導報,2011,8(13):3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