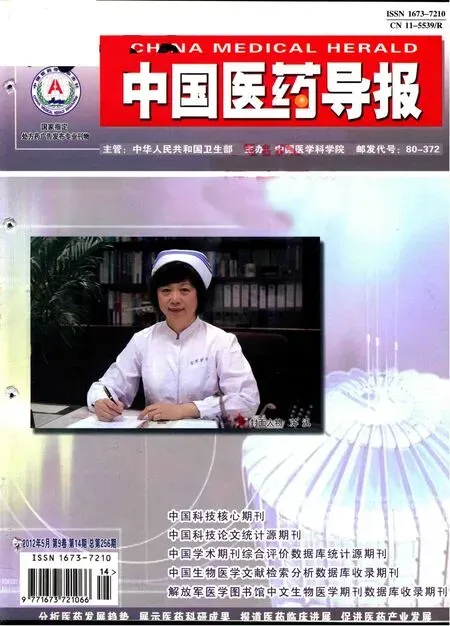我院ICU醫療干預措施與醫院感染的臨床相關性研究
李萬蘭
湖北省荊門市京山人民醫院,湖北荊門 431800
重癥監護病房(ICU)是醫院內危重癥患者集中的區域,患者診治過程中易合并各種繼發感染,是醫院感染的高發區域[1]。隨著醫療技術的發展,ICU患者的搶救成功率大大提高,但越來越多的醫療干預措施成為醫院感染發生的危險因素[2]。本文筆者探討重癥監護病房患者醫療干預措施與醫院感染的臨床相關性,為醫院感染的預防控制和管理提供參考,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擇2010年1月~2012年1月入住我院重癥監護病房≥48 h的實施了醫療干預措施的患者246例,其中,男208例,女38例,年齡≥21歲;入住ICU時間為3~35 d。
1.2 觀察方法
回顧分析246例患者的臨床資料,記錄觀察期內對患者實施醫療干預措施的時間,參照中華人民共和國2001年發布的《醫院感染診斷標準(試行)》[3],統計醫院感染部位及感染菌株種類的構成,對比觀察醫院感染組及無醫院感染組患者的危險因素,分析其醫療干預措施與醫院感染的臨床相關性。
1.3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16.0統計學軟件進行數據處理,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表示,兩組間比較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比較采用χ2檢驗,采用Logistic回歸分析各種醫療干預措施與醫院感染發生的相關性,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醫院感染發生的部位
246例患者中繼發醫院感染42例,感染率為17.07%,均為入住ICU后首次醫院感染,感染部位以下呼吸道、尿道和顱內感染為主,具體見表1。

表1 醫院感染發生部位的構成(n=42)
2.2 實施醫療干預的病原菌醫院感染菌株種類以及構成
對發生醫院感染的42例患者分別取痰液、尿液、腦脊液、血液等標本檢出病原菌感染32例,病原菌醫院感染率為76.19%(32/42),其中,實施醫療干預措施發生的病原菌醫院感染為21例,占65.62%,兩者比較差異有高度統計學意義(χ2=9.980,P<0.01)。具體見表2。

表2 實施醫療干預的病原菌醫院感染菌株種類以及構成
2.3 醫院感染發生的相關因素
通過發生醫院感染的42例患者與未發生醫院感染的204例患者的干預措施比較,發現入住ICU時間長、脫水劑應用時間長、機械通氣、開放性損傷、合并多發傷、氣管切開時間長以及不合理應用抗生素是醫院感染的危險因素(P均<0.05)。見表3。

表3 兩組患者醫院感染相關性因素比較
2.4 醫療干預與醫院感染發生率的相關性
使用1種醫療干預措施的患者,其醫院感染發生率為6.39%,使用2種及以上者醫院感染發生率為13.41%,兩者經χ2檢驗,χ2=30.874,P<0.01;經Logistic回歸分析,OR值為19.65,此結果表明,使用的醫療干預措施越多其發生醫院感染的危險性越高。
2.5 醫院感染的預后
發生醫院感染組患者42例,死亡9例,病死率為21.43%(9/42);非感染組204例患者,死亡19例,病死率為9.31%(19/204),感染組病死率顯著高于非感染組,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χ2=6.334,P<0.05)。
3 討論
隨著醫院重癥監護病房(ICU)的建立和醫療技術的飛速發展,許多危重患者的生命得到挽救,但隨之發生的醫院感染又成為患者良好預后的障礙[2]。本文筆者通過分析醫療干預措施與醫院感染的臨床相關性,發現ICU醫院感染發生率較高(17.07%),感染以呼吸道、泌尿道、消化道為主,感染的菌株種類以G-菌和G+菌為主;使用1種及多種醫療干預措施其醫院感染發生率也不同,這就證明醫療干預措施是醫院感染發生的危險因素,且隨著干預措施種類的增多,其發生醫院感染的危險性越高。醫院感染的高危因素常見的為[4-6]:入住ICU時間長,這樣交叉感染的機會就會增加;開放性創傷使細菌容易入侵;合并多發傷:缺血缺氧,微循環受損,因而加重炎癥反應;侵入性操作:如留置導管、氣管切開等,生理屏障功能發生障礙,因而失去生理防御能力;不合理應用抗生素導致二重感染、耐藥菌、新的致病菌生成;多因素綜合作用最終導致繼發醫院感染發生。本文的研究也得到類似的結果。
醫院感染可使患者住院時間延長,病死率增加。因此,認清醫院感染的高危因素,對預防醫院感染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熟悉醫院感染的部位及常見的致病菌和耐藥現狀,對于準確合理地使用抗生素、降低炎癥應激、減緩細菌耐藥、保護臟器功能,阻斷全身炎癥反應并擴散向多臟器功能障礙或多器官衰竭的進程,具有重要的臨床意義[7-8]。筆者還認識到:加強危重患者的保護性隔離措施,強化醫護人員無菌觀念,提升無菌技術操作水平,確保消毒工作質量等也十分重要。
綜上所述,重癥監護病房患者醫院感染發生率較高,感染后可增加患者致殘致死率;入住ICU時間長、脫水劑應用時間長、機械通氣、開放性損傷、合并多發傷、氣管切開時間長以及不合理應用抗生素是醫院感染的危險因素。建議臨床針對感染因素進行積極預防。這就要求在綜合衡量患者病情和治療措施的同時,要盡量減少一些不必要的醫療干預措施,尤其是侵入性操作,從而減少醫院感染的發生,改善患者預后[9]。
[1]蔣景華.醫院感染發病現狀的流行病學調查分析[J].中華醫院感染學雜志,2010,20(4):484.
[2]張京利,趙霞,王力紅,等.重癥監護病房患者醫療干預措施與醫院感染的相關性研究[J].中華醫院感染學雜志,2010,20(2):187-189.
[3]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醫院感染診斷標準(試行)[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1:10-12.
[4]任南.現代醫院感染監測方法與技術[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7:88.
[5]李雙玲,王東信,吳新民,等.外科重癥監護病房醫院感染和相關死亡危險因素[J].中華醫院感染學雜志,2006,16(5):503-507.
[6]吳安華,李丹.重癥監護病房臨床與環境、手分離耐藥革蘭陰性桿菌的同源性研究[J].中華醫院感染學雜志,2008,18(7):909-912.
[7]肖永紅,王進,朱燕,等.Mohnarin 2008年度全國細菌耐藥監測[J].中華醫院感染學雜志,2010,20(16):2377-2383.
[8]Gadepalli R,Dhawan B,Kapil A,et al.Clinical and molecular characteristics of nosocomial meticill in 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 skin and soft tissueisolates from three Indian hospitals[J].J Hosp Infect,2009,73(3):253-263.
[9]徐秀芝.醫院感染經濟損失病例對照研究[J].浙江預防醫學,2009,21(11):78-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