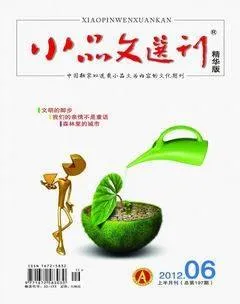那一雙憂郁的眼睛
我寫過一首關于狗的敘事詩《達爾文的故事》,寫這首詩,是因為總會在眼前浮現出它那一雙憂郁的眼睛。我與這條狗是在長途汽車站認識的。那是“文革”中插隊的年月。陜北初冬,收完了莊稼就沒有什么農活可干了。北京的插隊知青紛紛回城探親,我送同村的知識青年到了公社長途車站。車一輛又一輛地開走了,車場一下子變得空曠冷寂,陣陣寒風卷起散落的黃葉,還有我,還有一條狗。
這條狗是知青養的。在陜北,知青養的狗和知青一樣,很容易被識別出來。農民養的狗,不咬自家人,但對其他人,特別是陌生人,不管是誰,都會汪汪叫。知青養的狗,不咬知青,不管是哪村哪莊的知青,它都會迎上去搖尾巴。這個現象讓當地一些人很不爽,我曾寫過一篇《狗鼻子》議論過這件事。看來,這條狗的主人回北京去了,丟下了它。我也沒有回城,父母都在“牛棚”里挨批判受審查。我看了這狗一眼,它也用憂郁的眼神看著我。“回去吧!”我對它說了一句,轉身離開大路進了溝。我的生產隊知青點在這條溝里,距公社有小十里山路。不一會兒,我發現那條狗遠遠地跟著我,低著頭夾著尾巴也進了溝。我停下,它也停下,用憂郁的眼睛望著我。我拾了一塊土疙瘩嚇唬它,它也不躲,仍然用那雙憂郁的眼睛望著我。天色暗下來,月亮升起來,月光下的冬夜,清淒而寒意四散。我對這條狗說:“到家了,別怕。”我給它取了一個名字“達爾文”,因為那雙憂郁的眼睛。
想起這雙眼睛,是因為愛護動物的討論引出的“善良”話題。常聽到收養被遺棄動物的好心人的故事,在公園里散步也會看到每天都有人給流浪貓喂食。善良是一種美德,行為是利他和施與。而我以為,就我這個修行不足的書生而言,善良首先是因為“為自己”,“為自己”,有利己的原因。就說這個憂郁眼睛的事吧。那時我正煩著呢,它不就是一條喪家狗嘛,它跟我走,我又跟誰?這些念頭讓我一次次轟它走!但是,走著走著,我想:沒有主人的家它肯定進不去了,它會怎么樣呢?會被人攆,會被人打,還會死掉?它跟著你,相任你,你卻不管?我最后收留它,是我確信,如果不收留它,我這一晚上會做噩夢。常言說“與人為善”,我以為這首先是自我的一種需要,讓自己“心安”!
人其實是在兩個世界里活著的,一個是充滿現實利益的外部世界,一個是屬于自己的內心世界。有的人在外面風光倜儻而內心不得安寧,有的人日子坎坷多舛內心平靜安詳。善舉是人們看得見的利他行為,善良是心寬安寧的自我感受。在處理各種“與人”的事情時,我對自己訂出底線:不要做自己都看不起自己的事,不要做夜里睡不著覺的事,不要做無法坦然面對各種猜疑非議的事。做事要做得讓自己心安,讓自己心寬,讓自己心凈,這樣做的事也能夠與人為善了。有這樣的心理底線,與人為善會成為一種習慣,能讓一步讓人一步,能拉一把拉人一把,能忍一下忍耐一下,這個世界便多一些和平安寧。也許有人說:“你拉起來的是條落水狗,上來就要咬你怎么辦?”其實真的遇到這樣的事,再找個棍子也不遲。
再回到“憂郁的眼睛”這個故事吧。那個冬天因為有那條狗做伴,不再漫長而孤寂。我甚至想,不是我收留了這條被主人遺棄的狗,大概是這狗看見我在車場煢煢孑立于風中而找上門來?半年過去,春暖花開,有一天“達爾文”躁動不安,嗚嗚地低吠,晚上出走了,再也沒有回來。后來據老鄉說,那天有幾個外莊的知青從村頭路過。我知道了,那里面有它的老主人。好狗戀舊?好心沒好報!是的,起初我也這么想,然而,事件過去越久,回想起來越有一種讓自己感到溫馨的安慰,善行不是生意,也不是交易,善行出于內心而不求回報,善行是你給這個世界的祝福,而這個祝福也讓你的內心寧靜而幸福……
選自《揚子晚報》2012年4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