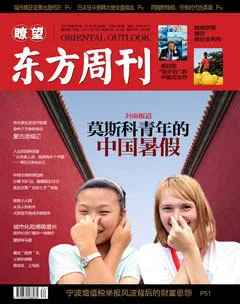“從衣食上講,我擁有半個中國”
2012-12-29 00:00:00杜博奇
瞭望東方周刊 2012年34期

榮宗敬發號施令,儼然企業“教父”,也曾難掩意氣地說:“從衣食上講,我擁有半個中國。”
1911年12月29日,孫中山回歸,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時代向商人們敞開了新的大門。
改朝換代的間隙,許多商人驚訝于新政府的寬容和厚道,從官方的文書上他們讀出鼓舞性的涵義。暫時看來,這對他們是極有利的訊號,于是受慣衙門老爺壓榨盤剝的懷疑者變得活躍起來。
榮宗敬比別人更能感受到這種變化,這個精于世故的青年有著非同尋常的觀察力和判斷力。看那無錫鄉間工廠日夜不息的煙囪以及上海錢莊門前的如織人流,經濟復蘇的景象躍然浮現。誰也沒有想到,史所罕見的金融危機帶來的陰影居然被政權更迭一掃而光,取而代之的是一個更令人充滿期待的世界,經久彌漫的輕商思維也不復存在,看起來沒什么比這更好了。
1912年開始的時候,街道復歸車水馬龍,一切回到原點,仿佛什么都未發生。也許更深遠的變化還未到來而已。
破舊立新之際,沒有理由不期待改弦更張。對于新世界,榮宗敬也有自己的主張。
沒用多久,榮宗敬就收到來自官方的反饋。新成立的無錫商會會員名單上,榮宗敬和榮德生的名字赫然在列,這表明他們已經被納入這個半官方組織,得到某種政治上的重視。盡管同期成為會員的商人為數眾多,榮氏兄弟不過是其中兩個小字輩,但他們還是對這種轉變寄予了超乎想象的熱情。
這年秋天,新政府在北平召開全國臨時工商會議,榮德生以無錫商會會員的身份與上百名全國代表參會。國務總理趙秉鈞派秘書與榮德生詳談,協商振興實業的措施。
對吶喊的積極回饋固然可貴,但落到實處才見真意。對榮宗敬和榮德生來說,眼下最迫切的愿望不是國家若何,實業怎樣,而是尋到一條擺脫企業危機的出路,畢竟,只有生存下來才能談論發展。
過去的一年,榮氏企業頻頻遭遇損失,簡直到了慘不忍睹的地步,即便廣生錢莊永久地關上大門,也無法阻止危機繼續蔓延。那年夏天的洪水在造成大面積棉花減產的同時,對小麥收成也造成巨大破壞,四溢的河水還光顧了茂新的倉庫,對于面粉廠來說,不啻一個晴天霹靂。
盡管戰亂之后的和平意味著糧食市場的春天,商人們迫不及待地開辦面粉廠,但種種跡象表明,無錫正在失去作為面粉業基地的優勢。一年來,榮德生反復考察,到北京開會之前已經拿定主意,要將新工廠設在更為開放、便捷、高效的上海——一個競爭更加激烈的平臺。
到上海去
許多準備投身面粉業的商人一定與榮德生有同樣的感觸:上海這個城市對實業經營簡直再合適不過了。
在多數中國人眼中,這個彈丸之地魔力無窮,吸引著四面八方的資金、人力和商品通商交匯。不過,人們在心中一遍又一遍強化“冒險家樂園”的時候,無意間忽視了它作為工業城市的種種得天獨厚的條件,因此那些最先發現這些便捷之處的先行者常常輕而易舉地獲得商業成功。
從1900年第一家民族資本機器廠阜豐在上海建立以來,到1911年的11年間這里已有民族面粉廠7家。而且,還有更多人打算來此開創面粉事業,其中便包括榮宗敬與榮德生。
兄弟二人在上海考察的間隙,流言蜚語在茂新面粉廠傳開來。
原來,看到面粉業發展迅速,茂新辦麥主任浦文汀和銷粉主任王禹卿不滿于做“高級打工仔”,私下計議脫離榮氏,到上海聯合創業。浦文汀和王禹卿都是業務骨干,一個諳熟上游采購,一個在全國商埠關系亨通,在茂新創建過程中立下汗馬功勞。多年耕耘,浦、王二人掌握了茂新進出關鍵和各種關系,如果他們一走了之,茂新這座大廈必定不能支撐多久。
榮氏兄弟聽此傳聞,不免心中大驚,火速奔回無錫詳查。在各種沮喪消息中,他們打聽到一個有利因素:浦、王兩家財力有限,東拼西湊勉強籌到2萬元,到上海開辦面粉廠,至少還需要2萬。
榮宗敬放出話來,愿意出這筆錢。浦王兩家幾番協商,自感無力獨撐局面,遂同意榮氏入伙。于是,榮宗敬、榮德生出資2萬元,王堯臣、王禹卿兄弟出資8000元,浦文渭、浦文汀出資1.2萬元,合計4萬銀元,到上海籌建新廠,這便是坊間所傳“三姓六兄弟”創業佳話。
經過數月設備調試、員工招聘等準備工作,1913年2月,福新面粉廠開工,每日夜出粉1200包。廠內,榮宗敬威望最高,任總經理,統攬全局;王堯臣和浦文渭以股份多少,分別擔任經理、副經理,負責采購、銷售等具體事項;榮德生為“公正圖董”,職位相當于總管。
有茂新在先,福新共用其采購、運輸、銷售體系,少走許多彎路。浦氏兄弟采取賒賬方式以茂新名義統一收購小麥,由于茂新信用好,可以開具7天期商業匯票,小麥每日從無錫運往上海,隔天即可從福新廠出粉,裝袋時打上“兵船”牌商標。
與此同時,王氏兄弟展開銷售才能,打著“兵船”旗號四處預售,求購者眾,產品尚未出廠,訂單便紛至沓來,而且預付全額現金,償付小麥匯票綽綽有余。
凡此種種,不僅解決流動資金困難,且極大縮短了生產周期,福新面粉廠發展迅速,很快在上海灘站穩腳跟。
“兵船”牌面粉
福新面粉廠開工數月,市場反映良好,產品供不應求,榮氏兄弟產生擴大生產的想法。恰好中興面粉廠因經營不善在市場競爭中步履維艱,四處尋求收購。中興面粉廠屬于老牌工廠,生產能力不俗,但由于競爭乏力,無人愿意接手。榮氏兄弟趁機將其租來,租期10年,每日夜出產面粉2000包,貼“兵船”商標銷售。
榮宗敬與榮德生善于借助外力實現自有產業發展,幾番出手,無不展現過人才干。而租借老牌的中興面粉廠頗有產業代工的神來之筆,更意味著新興勢力開始取代傳統老廠而崛起。
然而,榮氏兄弟還不打算停止擴張的腳步。1913年冬,經過數月積累,他們手中小有閑錢,劃撥10萬兩白銀,在中興面粉廠東面購地建廠,向恒豐洋行訂購21部美制粉機,命名為福新二廠,年底開工,每日夜出面粉5500包。而此時,運營10個月的福新一廠已經實現贏利3.2萬元。
此間正值上海面粉業大發展時期。1913年,上海新開3家本土面粉廠,本土面粉廠總數達到11家,資本總額230萬元,日產面粉25100包,平均每家2282包。11家粉廠中榮氏占有或掌控3家,產能高出行業平均值,產品更是一騎絕塵,直接叫板大肆傾銷的洋面粉。
當“兵船”面粉暢銷國內時,人們多將榮氏面粉事業發達原因歸于美制磨粉機,而忽略了其深層次的經營策略。
榮氏對信譽異常看重,嚴把質量關口,從源頭抓起。
辛亥革命后,榮氏兄弟考察全國各地的小麥,綜合比較后認為四川小麥品質最好,主選川麥做原料。他們制定嚴格的篩選流程,壞麥、熟麥、潮麥統統剔去,將摻雜沙石逐一揀出,保證產粉質量。1911年,大水淹沒茂新無錫倉庫,榮德生下令將受潮面粉和小麥統統處理掉,倉庫可能發霉的小麥全部不要,堅決不用工廠聲譽換取眼前利益。
此外,因用麥量巨大,榮氏先后在安徽蚌埠,山東濟寧,江蘇泰州、揚州、常熟、鎮江等地設立麥莊。榮氏有一個秘不外傳的生意經:每逢新麥上市,就大肆拋售面粉,以壓低粉價和麥價。
久而久之,榮氏面粉廠成為國內小麥行情波動的重要因素,大有操控市價之勢。而那些單打獨斗或規模弱小的面粉廠無力屯麥,只能聽憑擺布,在麥收季開工,其他時間停產。利用這個“時間差”,茂新、福新從競爭者手中輕而易舉地奪取面粉市場的半壁江山。
如此種種,“兵船”牌聲譽日隆,成為國產面粉品牌的佼佼者。與此同時,本土面粉廠紛紛使用英美機器,極大提高生產能力,拉低市場價格,對洋面粉傾銷形成正面阻擊,迫使進口量逐步下滑。
隨著1913年的結束,民族工業發展的黃金時代隨之到來,面粉業毫無疑問地走在前面。
撤股與創業
榮宗敬和榮德生是抱著同樣理念和信心去經營振新紗廠的。
從外在環境看,“一戰”爆發后面粉業的情形也出現在棉紗業,榮氏兄弟意氣風發地制訂了棉紡工業發展計劃,決意將振新紗廠的產能提高幾個臺階。然而,作為管理者的他們太過單純,忽略了“產權掣肘”,毫無意外地遭到保守的董事會的否決。
1914年的一天,振新紗廠召開董事會,榮德生第一次提出那個發展計劃:增機擴建,發展4家工廠,無錫振新一廠、二廠設在上海,三廠設在南京,四廠設在鄭州,紗錠數量隨設廠數相應提高,由3萬增加到30萬。榮德生剛說完,董事會就炸開了鍋,股東們幾乎一邊倒地反對他。
反對者毫不避諱地指出自己唯一目的就是賺錢,如果按照榮德生的方案,將贏利滾動投入建新廠,永遠無法分到現錢。這些人并非全是鼠目寸光之輩,有些身兼洋買辦等職,只是在風雨飄搖的時代缺乏安全感,所愿無非人財兩全,都是抱著賺快錢的心理投資,所以會聯合反對榮德生。
1914年秋天,關于發展計劃的紛爭上升為訴訟。大股東榮瑞馨以賬目不清為由要求查賬,并暗中聯絡其余股東,要求將振新盈余以現金形式發放紅利。協調無果,榮氏兄弟認為留在振新于人于己都是折磨,決意退出,重新創業。
年底,在無錫商會的見證下,振新拆股,榮氏兄弟用振新股份與榮瑞馨所持茂新股份互換,最后尚余3萬余元留在振新,以示不忘創業之情。
榮宗敬發愿:“我能多買一只錠子,就多得了一支槍。總應在50歲時有50萬紗錠,60歲時有60萬,70歲時有70萬,80歲時達到80萬。”在他心中,此乃進軍紡織業的宣言。
榮氏兄弟撤股出來時已到年底,國內棉紗市場正處于變革前夜。因戰事牽連,交戰國由生產過剩轉入生產不足,紡織品緊缺,致使價格急速攀高。一夜之間,由傾銷轉為進口,曾經在中國市場鋪天蓋地的洋紗、洋布轉眼間消失無影。
突如其來的改變讓中國棉紗界一派鼓舞,各家工廠加緊擴張步伐,爭搶洋人留下的市場空白。因供小于求,棉紗廠獲利倍增,社會上流傳“一件棉紗賺一只元寶”的說法,雖有夸張成分,亦可見此項事業誘惑力之大。
轉過年來,面粉廠籌建有條不紊,榮氏兄弟開始把更多精力投放到紡織業。
榮德生篤信風水,反復查閱典籍,希望為新工廠尋找一個上佳位置。一天,他從《楊公堪輿記》上讀到這樣一句話——“吳淞九曲出明堂”,大意是說吳淞江經過九道轉彎,將有一塊風水寶地。榮德生按圖索驥,果然在周家橋發現吳淞江第九道轉彎,于是篤定地認為,此處便是理想的建廠之所。
當時的周家橋還是一片人跡罕至的荒蕪之地,幾經考察,發現唯一勉強可以充作廠舍的只有一處破落的場地。這是一位意大利地產商的產業,不久,意大利商人開價41000兩,掛牌出售這塊場地。榮氏籌資將其買下,開始打造自家的紡織廠。
榮氏從振新紗廠得來一個教訓:穩定的組織結構是正常經營的保障,必須在企業擁有絕對控股權才能有效開展工作,企業需要上下一心。于是,在招股時,榮氏兄弟保持55%股份,另一位朋友持股25%,其余20%為散戶所持。
1915年10月,當36臺英國進口紗機開始轉動起來的時候,歷時5個月的籌建工作宣告結束。榮宗敬、榮德生為該廠定名“上海申新紡織廠”,即申新一廠,作為其棉紗事業的新起點。
申新的組織形式別具一格,與多數企業采取的股份制公司形式不同,它采用了股份無限公司的形式。企業不設董事會,股東會亦無大權,經理總掌大局,對企業全權負責,甚至擁有不經股東會改組企業的權力。
這種組織結構的優勢很快顯現。申新開工僅兩個月,1915年底即實現2萬元盈余。企業利潤節節攀高,到1916年利潤達11萬元,1917年達40萬元,1918年為80萬元,1919年達到100萬元。
“棉紗大王”
申新紗廠旗開得勝,鼓舞了榮氏增建新廠的愿望。1917年,兄弟二人意欲在無錫茂新面粉廠附近建造紡織廠,廠址遲遲未定之際,聽聞上海恒昌源紗廠盤讓出售,無論從成本、時間、效率等角度考慮,現成紗廠的誘惑大大高于自建工廠,于是榮氏兄弟緊急趕往上海探察。
最后,榮氏兄弟以40萬元買下恒昌源,改造后更名申新二廠,于1919年3月正式投產。
兩個月后,“五四運動”爆發,抵制洋貨運動風起云涌,紡織業獲得空前的市場契機。耐人尋味的是,在榮氏兄弟經營之下,恒昌源生產頗有起色,迅速占據日紗消退后的市場空白。日資建造的紗廠為華商收購,并成為阻擊日紗的主角,這在中國商業史上恐怕是破天荒的紀錄。
隨后,榮氏趕回無錫,在振新紗廠旁覓得土地,籌備申新三廠。
建廠期間,榮氏兄弟又前往湖北漢口,投資150余萬元,籌建申新四廠。1922年3月,申新三廠、四廠同時開工生產。
籌建申新新廠期間,榮宗敬召集華商紗廠聯合會同仁,積極籌建紗布交易所。
當時棉紗期貨交易被日商控制,榮宗敬建議,各廠絕不從日商取引所采購棉花,凡在取引所買賣棉紗的商號或掮客,一律斷絕往來,并在報上刊登說明。各紗廠早對日本人恨之入骨,如今有榮宗敬帶頭,自然群起響應,募集200萬元,組建紗布交易所,榮宗敬、穆藕初擔任理事。
申新出品“人鐘”牌棉紗質量上乘,廣受歡迎,被列為紗布交易所標準樣紗,也帶動“人鐘”牌布線銷量。“人鐘”牌產品暢銷國內,為榮氏兄弟贏得“棉紗大王”稱號。
衣食上坐擁半個中國
上世紀20年代初的中國,“三新財團”一定是個讓人眼前一亮的詞匯。作為榮氏兄弟數十年打造的茂新、福新、申新系統的統稱,“三新財團”雄踞面粉、棉紗兩界,分別占據全國面粉、棉紗產能的1/4和2/7。
1921年,上海江西路聳立起一座英國城堡式建筑,即茂、福、申總公司所在地“三新大廈”。作為榮氏“大本營”,這幢耗資35萬元、占地2.8畝的辦公大樓高三層,樓頂插公司旗幟,風光氣派,在當時,恐怕只有“狀元企業家”張謇在上海建造的南通大廈可與之比肩。
三新總公司實行總經理(榮宗敬)負責制,對茂新、福新、申新系統的采購、供應、銷售、資金和人事進行統一管理。各廠經理每日中午到總公司開會,報告生產經營狀況,領取指令,然后分頭行動,通過電報、電話將指令傳至上海、無錫、濟南的工廠。從規模和做派上講,頗具現代企業風范。榮宗敬發號施令,儼然企業“教父”,也曾難掩意氣地說:“從衣食上講,我擁有半個中國。”
自1902年投身實業,榮氏從資本5萬元的保興面粉廠起步,到1922年,經歷20年的時間,已發展為資本上千萬,更是近20家面粉、棉紗工廠的產業巨頭,為數十萬員工提供工作崗位。
在國貧民弱的時代,三新總公司的出現不禁令人眼前一亮,其代表著民族工業的最高發展水平。榮氏兄弟更是被譽為國內實業界的“騎士”,他們的創業故事被日本人寫入小學課本,就連一向低調的榮宗敬也認為自己的事業“幾滿半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