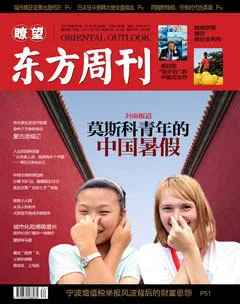阿姆斯特朗:所有時代的英雄
傳遞愿意探索并超越極限的精神,影響一代又一代的年輕人,這應該是他成為所有時代英雄的理由。
2012年8月25日,“登月第一人”尼爾·阿姆斯特朗走完了82年人生。去世當天,美國總統奧巴馬給予他的評價是:“美國最偉大的英雄之一——不單只是他的時代,而是所有時代的英雄。”
“時勢造英雄”,如果一個英雄能超越所有時代成為永恒,那么以后所有時代的人們都會感興趣于同一個問題:這個人到底做了什么?
溫故1969
1969年7月20日,在澳大利亞的一個小鄉村,20歲的小學教師奧爾森告訴他的33個學生,今天不用上課了,跟他一起看電視直播。學生們有些茫然,他們對電視直播還比較陌生,因為村子里一共只有4戶人家擁有電視機。
這33個孩子無疑十分幸運,他們在電視畫面上看到了終身難忘的奇異景象:兩個身著白色宇航服的人從登月艙緩緩走入一個奇怪的空間中。小學生們當時也許并不清楚,這個地方離地球有384000公里。
在地球更多地方,人們沒有條件看到電視畫面,甚至無法及時從媒體獲知這個本該傳遍地球每一個角落的重大消息。當時的中國風雨如晦,據說在阿姆斯特朗登月成功的次日,《人民日報》上唯一一則關于美國的消息是“備受種族歧視、階級壓迫和剝削的美國黑人群眾,掀起了日益高漲的抗暴斗爭浪潮”。盡管當時《參考消息》和《參考資料》對登月事件做了一些報道,但限于受眾范圍的狹小,大多數中國人并不知情,而知情的少數中國人因為意識形態的原因也很難有興奮感。
在當時的另一大陣營蘇聯,獲知這一消息后,人們震驚異常。1961年4月12日,蘇聯宇航員尤里·加加林乘坐“東方”號宇宙飛船繞地球飛行了一圈,成為第一個進入太空的人,整個社會主義陣營歡呼一片。8年后,美國人卻率先登上了月球。
從肯尼迪發誓要在太空競賽上超越蘇聯開始,美國在整個阿波羅計劃上耗費巨大,亦有不少美國人對此心生埋怨。但在阿姆斯特朗踏上月球的那一刻,電視機前的美國人興奮得難以自已。
今天的人們還可以從新聞圖片和電視紀錄片中看到阿姆斯特朗和他的同伴從月球回到美國后受到歡迎的盛大場面,其中包括持續數周的游行、總統晚宴、28個城市的親善旅行,所到之處歡呼聲山呼海嘯。
尼爾·阿姆斯特朗作為美國在太空競賽方面超過蘇聯的標志性人物,是那個時代所有美國人心目中的英雄。
英雄前傳
在英雄綻放光彩的那一刻之后,媒體總有探尋他們在英雄時刻之前一切的強烈沖動。當登月新聞的余溫逐漸消退之時,媒體對于阿姆斯特朗的興趣慢慢轉移,更愿意挖掘登月英雄成名前的故事。他們奮力把阿姆斯特朗推到聚光燈下,演繹出許多虛虛實實的故事。
有一則故事是這樣說的:阿姆斯特朗很小的時候,有一次媽媽正準備開飯,外面忽然下起大雨。穿著新衣服的阿姆斯特朗突然跑到外面瘋玩,在雨中不斷跳躍,新衣轉眼間沾滿泥水。他邊跳邊開心地對媽媽說:“媽媽,我要跳到月球上去。”媽媽只是淡定回應:“好啊,只是你別忘了從月球上跳回來,回家吃晚飯!”
另一則關于他的故事就更有戲劇性,仿佛是幽默的美國人編出的一個笑話。阿姆斯特朗小時候和伙伴們在院子里打棒球,他的朋友把球打到鄰居戈斯基夫婦家窗戶下面。阿姆斯特朗跑去撿球的時候,聽到戈斯基夫婦在吵架,戈斯基太太大聲嚷道:“你想跟我上床?休想!除非鄰居家的小孩登上月球。”
童年阿姆斯特朗是否把成為宇航員當作理想,此事存疑,但說他對從事飛行員工作早就表現出強烈興趣則有事實為證——15歲參加飛行課程;16歲生日當天獲得飛機駕駛執照,那時,他還不到拿汽車駕照的年齡;1947年,17歲的他選擇就讀印第安納州普渡大學航空工程專業;學業沒有結束,19歲的阿姆斯特朗便迫不及待地應召入伍,成為海軍飛行員,參加了朝鮮戰爭。
在朝鮮戰爭中,阿姆斯特朗作為美軍飛行員“表現卓越”,只是后人往往忽略這些。他在朝鮮一共執行了78次任務,飛行時間達到121小時,其中超過三分之一是在1952年1月。因為在朝鮮的表現,他獲得了美國飛行獎章、金星獎章以及朝鮮服役獎章。
在“英雄前傳”里,原本朝鮮戰爭可以算是他飛行生涯里的“輝煌時刻”,可是許多年后,當有人問起這段歲月時,阿姆斯特朗只是說了幾個字:“那不重要。”
后登月時代
英雄成名后,有的保持長時間的風光無限,名利雙收;有的被漸漸遺忘,甚至就此沉淪。這兩種情況,顯然尼爾·阿姆斯特朗都不是。
在整個阿波羅計劃中,美國共誕生了12位登月英雄。阿姆斯特朗并不愿意像其他11位那樣時時站在聚光燈下,他本人的意愿似乎是一步步從人們的視野中消失。他拒絕所有電視臺請他講述“阿波羅11號”往事的采訪邀請,也沒有像其他航天英雄一樣撰寫自傳。
在阿姆斯特朗的后登月時代里,他總是極力淡化自己“登月第一人”的身份。他先是在1970年離開了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此后在南加州大學獲得了航空工程專業的碩士學位。1971年至1979年,他在辛辛那提大學任航空工程學教授。后來,阿姆斯特朗又投身商業活動,幾乎很難讓人看出他與宇航員這個身份還有什么關系。
今天的人們再來看另外11位阿波羅計劃的航天英雄,他們在返回地球之后的生活中遇到各種困擾,境況令人嘆息。
阿姆斯特朗的登月伙伴奧爾德林在回到地球之后幾度受到抑郁癥的影響,在經歷眾人追捧的光榮歲月之后,開始疑惑未來的人生將如何度過。他說:“我要見誰呢?我的日程表在哪里呢?將要發生什么事?這種無組織和不確定不會給你信心。”
“阿波羅14號”飛船登月艙駕駛員埃德加·米切爾從月球返回太空艙時,有一種被某種東西注視的奇怪感覺,他感到自己和宇宙中的智能生命產生了一種心靈的接觸。回到地球后,米切爾開始研究神秘的超自然現象,他在加利福尼亞建立了一個“抽象科學協會”,專門研究人類意識和各種超自然事件。
另一位登月英雄查爾斯·杜克同樣無法應付登月事件帶來的巨大心理震撼,他開始酗酒,并經常虐待自己的孩子,后來皈依宗教,將登月事件稱作“我生命中的灰塵”。
阿姆斯特朗晚年曾感慨:“到底要花多少時間,別人才不把我當做一名宇航員看?”他似乎一直竭力擺脫閃耀在頭頂的英雄光環,為了過一個普通人的正常生活,他因為和教師工會的矛盾而選擇從大學辭職;他像一個普通學者一樣在國際會議發表科學論文——《從空間探測中對地球的新認識》、《臭氧層之爭》等;他還會像個一般意義上的商人,從事最基本的商業活動。
英雄的偶然和必然
一個人成為英雄,是偶然還是必然?阿姆斯特朗曾經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他成為登月第一人是個“偶然事件”。
媒體顯然認為阿姆斯特朗的上述表述充滿謙虛成分,但是縱觀登月前后的整個過程,其中的確存在著許多偶然因素。
據前英國廣播公司航天特派記者特尼透露,在1958年至1976年間,他曾數次和阿姆斯特朗會面。據特尼了解,NASA曾經從公關角度考慮,認為“登月第一人”應該是一位更健談、熱情的宇航員,而非沉默寡言的阿姆斯特朗。現年97歲的特尼稱,阿姆斯特朗是位優秀的宇航員,但同時卻是一位喜歡埋頭于實驗室的“科學怪人”,這樣的性格并不符合NASA的口味。阿姆斯特朗的另外兩名搭檔奧爾德林和柯林斯同樣不好社交,因此也不是最佳人選。
特尼表示,NASA更希望看到“阿波羅12號”登月,因為這艘飛船上的指令長宇航員康拉德口才了得,將是推廣航天事業的最佳代言人。然而,阿姆斯特朗最終被選中,據說是因為他出色的技術和沉靜的個性。
阿姆斯特朗在登月實施過程中也曾遇到偶發的危險,他在距離月球表面幾百米的位置有個驚人發現:月球重力出乎意料的變化致使導航系統失靈,從而引導登月艙向著一個布滿巨石的區域降落。擔任過飛機試飛員、具有豐富飛行經驗的阿姆斯特朗開始利用人工操作尋找更佳著陸點,這時,他發現燃料僅夠維持30秒,原來他只顧著完成任務,忘了在著陸前關閉發動機,這有可能造成登月艙在月球表面廢棄爆炸的嚴重后果。
如果阿姆斯特朗運氣稍有不佳,就有可能永遠留在月球上了。今天人們發現,實際上當時美國總統尼克松已經為他們準備了悼詞以防不測。但尼爾·阿姆斯特朗終究還是成了英雄,偶然和必然一起成就了他。
所有時代的英雄
在阿姆斯特朗去世之后,奧巴馬下令白宮、聯邦政府機構、美國公共建筑和場所以及軍營、軍艦等處所在阿姆斯特朗葬禮當天降半旗,以此“向阿姆斯特朗帶給人們的回憶”致敬。而奧巴馬的競選對手羅姆尼這樣評價阿姆斯特朗:“帶著對國家無法衡量的勇氣和無限的愛,他行走于人類從未抵達之境。月球將想念她的第一個地球之子。”
美國猶他州退休女教師朱麗婭·布賴恩回憶,1969年7月20日當天,他的小兒子鮑勃還在上小學,平日這個時候他早應進入夢鄉。“阿姆斯特朗宣布實現了人類的一大步時,我注意到鮑勃的眼睛張得大大的,眼里滿是驚喜和憧憬。”布賴恩說,“我想他那時還太小,或許不能完全理解登月的意義,但這讓他從此愛上了科學探索。”
像鮑勃一樣,世界各地成千上萬的孩子被阿姆斯特朗登上月球所鼓舞,由此踏上科學道路。直至今日,NASA依然將“阿波羅11號”登月作為青少年科普教育的一個重要內容。“把人類送上月球不僅激勵了美國,也同樣激勵了全世界。”NASA首席歷史學家斯蒂文·迪克說,“上世紀60年代是一個充滿動蕩的時代,但在那樣的環境下,登月成功證明了人類的潛能。”
在阿姆斯特朗去世后,世界各國的人們紛紛表達哀思。1969年,多數中國人還無法獲知阿姆斯特朗登月的消息,也無法對這一事件發表理性評論。而2012年,他去世的消息卻瞬間引發中文網絡的關注與熱議。
如同阿姆斯特朗的家人所發表的聲明:“我們為失去一個好人而哀悼,同時為他不平凡的人生而贊嘆。希望全世界青年人能夠視他為榜樣,努力實現他們的夢想,愿意探索并超越極限,忘我地投入一項比自身更加重要的事業。”
傳遞愿意探索并超越極限的精神,影響一代又一代的年輕人,這應該是他成為所有時代英雄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