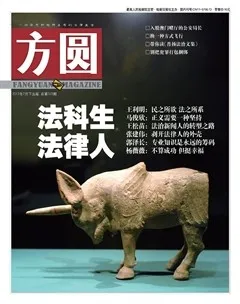法律人百年沉浮
2012-12-29 00:00:00靖力
方圓 2012年14期

【√】法律人總是有一種書生意氣,百折而不撓,著名法學家江平有一句最經典的格言,可以評價法律人的共性:“我只向真理低頭。”
又到畢業的季節,校園里總彌漫著喜悅與傷感的氣氛。北京師范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所在的新主樓,電梯前擠滿了穿著黑色學士服、藍色碩士服的朝氣蓬勃的年輕人,粉色垂布告訴我們他們是法科畢業生。
他們高聲說笑,聽來有兩個主題:商量怎樣在接下來的“散伙飯”中將導師灌醉;談論畢業后各自有怎樣的安排。聽他們的談笑,忽然想起聽人說過,法科畢業生就像分岔的河流,一出校門總是各走各的路,有許多的職業和未來可供選擇;然而又萬涓入海,總逃不過匯聚到一起的命運,成為“法律人”的一份子。
其實近些年來,在社會、經濟、教育以及輿論等許多領域,常常可以看見以“法”的名義聚集在一起的一群人,發揮著越發重要的作用。
他們可以是法官、檢察官,可以是律師、法務,也可以是專家、學者,他們自稱為“法律人”,別人稱他們為“法律職業共同體”。
法律人的概念與外延
近幾年興起的“法律職業共同體”是個新潮的概念,常用來指法官、檢察官、律師以及法學家組成的法律職業群體,這個群體受過專門的法律專業訓練、具有嫻熟的法律技能,因為相同的“法”的背景聚集在一起,相互作用和聯系。
在中國,法律職業成型很晚。“中國歷史上一直沒有形成西方意義上的職業法律人。”復旦大學特聘教授、法理學研究專家孫笑俠在講座上表示。只有一些兼職從事司法工作的人員,比如訟師、書吏、刑名幕友(又稱師爺)等等。
歷代所謂廷尉、大理、推官、判官等并不是專門的司法官員,而是行政官員——司法者只不過是作為權力者的手段而附屬于當政者。直到近代,受西方法律制度影響,才產生了律師、法官這些法律職業群體。
比較而言,西方的法律職業則誕生得早很多。意大利波倫尼亞的法學教育在11世紀末即已大放異彩,在13世紀末,幾乎所有西方國家的較大型大學都有一座法學學院。西方著名法哲學家韋伯曾在闡述西方專業官吏的興起時說,由于司法程序的發展,歐洲的法律專家迅速崛起成為一種職業,司法程序的細密化要求決定了法律專家的地位。
相較于“法律職業共同體”而言,“法律人”的概念更加古老,外延也更大。中國政法大學知識產權中心主任徐家力在一次講座上稱,一般來說,“只要是具有較高法律水平的人,推崇利用法律解決問題,內心向往法治的人,都可以被稱為法律人”。
在徐家力看來,“法律人”不一定是法學家,也不一定是法官、檢察官。法律人可能的職業有8種之多,包括律師、司法官、法學家、法務、除司法官以外的公務員、有關法律的商業經濟工作者、媒體記者、無關法律的工作者。前三類是法律人的核心,也是構成“法律職業共同體”的職業。
當然“法律人”的定義并不是唯一固定的,也有相對狹義的說法,即認為法律人就是法科學生和從事法律相關工作的人的合稱。
孫笑俠曾經表示,大眾思維基于生活邏輯,而法律思維基于專業邏輯。法律人和非法律人有很大的區別,首先就體現在思維方式上。大眾以情感為重,法律人以理性為重;大眾追求科學的“真”,法律人追求程序的“真”;大眾喜歡遇事“權衡”,法律人則總是“非此即彼”……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強世功則認為,法律人與“其他人”最為不同的地方,除了與眾不同的思維方式,還有專門的法學知識體系和普遍的社會正義感。匯聚了這三部分特點的人,就是一個典型的法律人。在這個范疇里,“無論是最高法院的大法官還是鄉村的司法調解員,無論是滿世界飛來飛去的大律師還是小小的地方檢察官,無論是學富五車的知名教授還是啃著饅頭咸菜在租來的房間里復習考試的法律自考生,都是法律人。”
中國法律人由近代起源
自商代以降,李悝、商鞅、張湯、衛覬、劉頌、柳宗元、王安石……屈指數來,中國古代不乏法學家,但沈家本卻評價中國古代的法律人:“國無專科,群相鄙棄。”雖然有學法之人,卻無安身立命之地,還遭到各種鄙視,不得不說是中國古代法學界最大的遺憾。而照現在的定義,這些沒有法學“職業”的古代法學家甚至很難稱得上是法律人。
真正以法安身立命的法律人誕生在近代中國,伍廷芳算是個中翹楚。他在林肯律師會館受過系統的法律訓練,是中國近代第一個法學博士,也成為中國最早的執業律師。1902年,伍廷芳應召同沈家本一起主持修律,可以說是法律人登上近現代中國歷史政治舞臺的處子秀。
法律人作為一個群體在近代中國產生,要歸結于清末大量法政學堂的設立以及留學研習法政潮流的出現。這有其時代背景和烙印:1905年清政府廢除沿襲數百年的科舉制度,讀書人傳統晉身官場之路被堵塞,而當時觀念認為法政專業與為官之道相差不遠,于是天下中學生群起而逐之。經濟狀況好點的學生東渡日本,而大部分進入遍布各省城乃至地方的法政學堂。其二,法政學堂辦學成本低廉,對硬件要求不高,說辦就辦,辦不下去就散。這與今天法學院遍地開花至少在表面上很相似。
這些歷經法政學堂洗禮或留學務洋的人就這樣成為中國第一批法律人。但這批人并未在歷史上留下好名聲。
“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等留學派,后來在五四運動中成為了所謂的賣國賊。更激進者如汪精衛,則在留學日本期間成為革命黨人,在人彈襲擊中一戰成名,革命勝利后一度也成為黨國元老。槍炮作響法無聲,早期‘法律人’大都不務正業。”曾經著有《百年中國法律人剪影》一書的中國政法大學法學博士陳夏紅說,除去梁啟超、伍廷芳等少數精英,最早的法律人多半淪為了時代政治斗爭的犧牲品。
反而是那些法政學堂,在硝煙中留存下來,奠定了中國大量法學院校的基礎。如今,許多法學院校的校慶或者院慶,往往將建校(院)時間追溯到1905年左右,把當年的法政學堂當做它們的前身。
法律人群體的浮沉遭遇
一個誕生在硝煙中的嬰孩值得同情。法律人群體的發展壯大,一直在戰爭狀態下進行,辛亥革命、軍閥混戰、抗日戰爭加上解放戰爭,似乎法律人一出生便沒過過好日子。
毫無疑問,1949年對于中國法律人來說是個分水嶺。解放戰爭得出分曉后,擺在中國法律人面前有一個時代的抉擇,“該何去何從”?
這里面,既有遠走美國的,如顧維鈞;亦有隨國民黨遷居臺灣的,如第一個將《德國民法典》翻譯成英文的王寵惠、國民黨政府法制局局長王世杰、重慶《中央日報》總主筆蒲薛鳳;當然還有大部分,則留在解放區,期待追隨中國共產黨建設新中國,這部分人很多,如羅隆基、王造時、楊兆龍、李浩培、韓德培等,甚至不乏如錢端升這樣放棄哈佛訪學良機而留在中國大陸的。
難以想象的是,1949年前即已成名成家的這批法律人,留在中國大陸的境況竟然最差,命運的悲劇性最為強烈。
國民時代“六法全書”的廢除,相當于廢除了這批法律人賴依安身立命的法律體系;其次,決絕而無情的思想改造,從精神上徹底打垮了他們。1952年,全國實行院系調整,將傳統的大學體制破壞無余,原來的法學院被拆分,然后裝入革大師生主導的幾所政法學院,法律學者再度喪失精神家園;同時,1951年前后掀起司法改革運動,司法系統內的從業人員全部被做為舊法人員而掃地出門。這樣下來,不到三年時間,中國法律人忽如一夜之間喪失了所有賴以生存的體系。
到了1957年,一場反右運動將幾乎早已改行教外語的法律人劃為異類,這里面楊兆龍、謝懷栻的經歷十分慘烈。楊兆龍的女婿陸錦碧遭受遷連而劃右、勞改,后因"牙膏皮事件"幾近槍斃,當屬慘烈者中尤為慘烈者。
與法律人的這種悲劇性命運相因應,即便如江平這樣在1949年之后由政府自己送出去學法律的法律人,1956年提前學成歸國后,也難逃反右斗爭與文化大革命的劫難。
法律人的脾氣
近代近百年的特殊經歷,鑄就了中國法律人與眾不同的特質。
古羅馬名著《法學階梯》中有一句名言:“法學乃正義之學”。從沈家本開始,中國許多OlJijMTMVLFc0HHRibg2Gg==法律人就堅持站在正義的立場上治學、入仕。郁達夫的哥哥郁華,早年在日本法政大學研習法學,卒業后任民國最高法院東北分院刑事審判庭庭長,后來在擔任上海租借區法院法官時,罔顧自己的生命,救出了田漢、陽翰笙等當時的進步人士。即使是在“五四運動”期間受非議頗多的曹汝霖,在抗日戰爭爆發以后也因慚愧而拒絕與日本人同流合污。
除了高高懸于心中的“正義”二字,法律人最為看重的是他們為社會帶來的改造。法學家談理論成果,司法官則重實踐成果。新中國第一位民法博士王利明在接受《方圓》采訪時就多次表示,“法學家應當盡可能的為國家、社會的發展提供所需要的法學智力成果”。
生于1916年的“行政法之父”王名揚,在飽經劫難之后的古稀之年連續推出了《英國行政法》、《法國行政法》、《美國行政法》三部著作,開辟了中國行政法學研究的陣地,在80多歲接受采訪時,王名揚還說,身在一個適合著書立說的時代,他計劃寫出5本關于行政法的書,3本已經完成,另一本《比較行政法》已寫了一半。后來雖然因身體原因,王名揚未能完成計劃中的5本著作,但其法學研究的公心,已經廣為世人知曉和贊嘆。離開東交民巷4年之久的前首席大法官肖揚,最近在其新書《肖揚法治文集》中依然在思考中國的司法改革問題:“當依法治國已經被確定為基本方略之后,在其已經成為憲法原則的今天,應當遵循怎樣的推行路徑?是否繼續依法‘自下而上’地摸索,抑或站在國家的全局有領導、有計劃、有步驟、有秩序地依法‘自上而下’地推行?”
英國著名的“功利主義”法律學家邊沁曾經說:“法律的原則就是追求最大多數人的幸福。”追求正義、追求成果,成為中國法律人最大的共性。在陳夏紅眼中,這也成為法律人幾經沉浮而命途多舛的原因。
“法學畢竟是依賴于書本和理論的學科,所有的法律人都會帶點倔強、固執的壞脾氣。他們在時局混亂、崇尚武力的時代,地位本來已經很尷尬,但因為其固守的追求,使得他們的遭遇更加難堪。這種時候,‘法律人’與當權者的關系,往往就成為決定他們能否在法治社會的形成中建功立業的基礎。因此‘法律人’的基本命運就是:呼之即來,揮之即去,關系好時法典化如火如荼,司法建設捷報頻傳,‘法律人’恨不能身兼多任,鞠躬盡瘁;而關系變差時,右派、勞改、入獄、監禁乃至各種各樣的被死亡、被失蹤,法律界可謂是重災區。”
陳夏紅說,替法律人反省,他們氣質上先天性地偏于保守、理性,但又有一顆憂世憂民企圖闖出一番天地的心,這在熱衷于搞運動、鬧革命或動輒約架的國度,不大可能占到大便宜,于是在時局最動蕩的時期受苦受累便成了必然。
曾經有人評價法律人“守經有余,權變不足”。法律人總是有一種書生意氣,百折而不撓,著名法學家江平有一句最經典的格言,可以評價法律人的共性:“我只向真理低頭。”
六代法律人
1978年之后改革開放,劫后余生的中國法律人總算迎來一段不那么灰暗的日子,往日的錯誤被逐漸糾正,新一代的法律人才終于能站在法治的最前沿。1977年至今,法學院校的恢復和重建、國家立法的進步與完善,各種情勢都顯示出法律人冰雪初融的春天正在到來。
中國這嶄新的一代法律人,被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許章潤稱為中國的“第五代、第六代”法律人,并寄予厚望。他曾撰文《書生事業,無限江山》闡述了他劃分的理由。
許章潤文中的前四代法律人,許多都已成為歷史,健在的也大都進入耄耋之年。這些法律人或在百年洪流里留下了珍貴的法學研究史料,或在新的時代厚積薄發,完成了為后世法學的最后一推。許章潤說,當今時代,是第五代法律人甚或“第六代”法律人的時代。“如果說現代中國法學肇始于百年之前,脫手于第一、二代法律公民,那么,必最終成型于第五、六代的努力之中。”
許章潤所謂的第五代法律人,即現在正值壯年、在法律界當家做主的法律人,第六代法律人,大概就是指仍在象牙塔中磨礪自己充實自己的準法律人吧。
根據相關統計,目前中國的“第五代、第六代”法律人可能已有百萬之眾。這個數據也可以透過司法考試大概推理出來。
從1986年開始實行的律師資格考試在1993年以后改為每年一次,2001年以后更名為國家司法考試。然后就是這個國家司法考試,成為了當代法律人必須邁過的門檻。如今,要當法官、檢察官、公證員、律師、大學法學教授都需要通過司法考試,甚至一些公司招募法務、個人尋求訴訟代理人也都有此要求。通過司法考試不再僅僅是律師一個行業的入行資格,它漸漸演變成為了所有法律職業的共同門檻。
根據司法部公布的相關數據,近幾年通過國家司法考試的人數,2002年首屆通過人數為24800余人,5年后的2007年這一數據增加到58800余人。一直到2011年,總共舉辦的10次司法考試,全國共有50余萬人通過。加上在校就讀的法科學生、在此之前的少數“免試”的從事法律職業的人員,以及一些基層單位未通過司法考試但仍舊從事法律服務工作的人員,中國的法律人也許接近百萬。新時期的法律人數量如此巨大,那么這些法律人過得好嗎?
北京君合律師事務所律師潘躍新說,至少律師過得不錯。
截止到2008年,中國有12萬執業律師,全國律師事務所超過1萬家。較大型的律所有擁有超過50個律師的,年創收能達到5000萬元人民幣,但比起國外動輒成百上千人的大所來說仍然不算什么。另外,隨著法治建設發展,律師也越來越成為高收入、高地位的職業。
還記得1997年以前,中國律師辦案都按照一個律師收費標準領取每一次案件的勞務費。刑事案件50元,民商事案件按案件標的的3%-5%提成。那時候,經常會有提著破公文包上法庭啃冷饅頭的律師出現。現在情況好多了,不僅各地紛紛揭開收入帽,而且在京滬等發達城市,有一些律師的年收入可以達到幾十上百萬,也算得上標準的高收入人群了。
至于法官、檢察官,更是年輕法律人最為醉心向往的法律職業。據相關公開資料顯示,2008年全國檢察官人數達到11萬人,而全國法官人數早在2005年就已經超過22萬人。接受《方圓》采訪的西安市中級法院法官葛峰向記者表示,法官的形象在他年少的時候就給他留下機敏而莊嚴的印象,當上法官之后也非常以自己的職業自豪,也許這能代表所有法官、檢察官的心聲吧。
在學界,法律人的勢力也迅速擴大。來自2011年的統計資料顯示,全國目前已有12所高校是法學一級學科博士點、30個學校將近50個法學二級學科博士點。碩士點更不計其數。在立法、司法方面也有越來越多的高校名師參與進來。許多法學院校的教授均在法院、檢察院兼任重要職務。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教授何家弘在最近的一篇回憶學生吳丹紅的文章中,也有部分文字提到自己的博士生,都有不錯的著落,有的畢業至今甚至有所小成。這也從側面說明,法律人的隊伍,在這一代代的傳承與培養中,不斷充實和擴大著。
當代“法律職業共同體”的責任與期待
現在許多研究法律人群體的人,喜歡將法律人稱作“法律職業共同體”,有人評價這個稱謂,說它太“功利”,“應該相互對立的幾個職業被放到同一個體系中去,不成體統”,不符合法律人應有的孤獨和正義的感覺。
但也有人認為,法律人應當將自己置身于法律職業共同體的環境中去,才可能完成一位法律人的職責。有人打過一個比方,法學家類似于種植者,他們通過參與立法、教育法科學生,培養法律職業共同體的新生力量;律師和檢察官則像保護枝椏的人,幫助不同角度伸展的枝椏獲得陽光和雨水;法官則是最終修裁植物的人,他判斷植物生長是否勻稱是否有頂端優勢,然后決定哪個枝椏需要被裁剪,哪個需要保留。
支持或者否定,從兩個方面給法律職業共同體帶來啟示,即互助與制約應當并存。
然而,如今的“法律職業共同體”卻因為其不夠團結、各自為政的現狀,給一些法律人帶來了深深的憂慮。
有學者表示:“有時候,表面上我們在試圖通過司法考試,建立法律職業共同體,但實際上法律人內部的結盟與敵對狀況卻越來越嚴重。說結盟,既有辦案機關聯合辦案、不分你我的結盟,也有律師們同聲相應、互相聲援的結盟;說敵對,則更顯而易見,司法機關與律師互不信任的狀況無以復加。有些刑辯律師走投無路,要么把當事人救出來,要么自己被關進去。我認為,不管是律師、法官還是檢察官,都應該先做到行業內部的自治,然后才能去管別人的公平正義,如果最該追求公平正義的團體自身不保,那還談何其他?”
清華大學比較法研究中心主任韓世遠在2010年清華大學法學院畢業典禮上說,法治要求法律人共同的努力,需要在規則中互相制約他們行為和理想,法律人必須要有一個共同的理想:法治中國。法治中國又必須要有統一的行為方式:規則之治。
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王振民也曾撰文表示,法律人需要有共同的標準和理想。王振民認為,每一個法律人都應該要有強烈的使命感,要有頑強的毅力,要有很高的與人協作的情商和協調能力,要有高尚的品格。
無論是王利明、王松苗還是葛峰、郭澤長,隨著社會的進步,法律人在各行各業都呈現脫穎而出的趨勢,司法界、政治界、商界以及社會各界都有法律人正在成為領袖。許多其他國家也是這種趨勢。這既是許多非法律人學習法律的動因,也應該成為法律人堅守法律的理由。法律人既然已經作為上層建筑的構建者,就應當承擔約束,完成社會使命。
采訪中,陳夏紅也說,研究所謂法律人或法律職業共同體的歷史和現狀,盡管無法轉化為現實的GDP,但對于中國的法律環境,對于新生代法律人的啟迪,有很大價值。
商鞅強調“以法治國”要求國家官吏學法、明法,百姓學習法律者“以吏為師”。他還改法為律。強調法律的普遍性,具有“范天下不一而歸于一”的功能。同時,商鞅還主張輕罪重罰,強化法律意識,不赦不宥。主張凡是有罪者皆應受罰。
中國法律人之最
》最早的律師:伍廷芳
伍廷芳(1842-1922)是清末民初的法學家,祖籍廣東新會。他早年在香港圣保羅書院讀書,1874年自費留學英國,在倫敦學院攻讀法學,獲得博士學位及大律師資格,成為近代中國第一位法學博士。
1877年,伍廷芳回到香港,當即開業做律師。他也是中國近代第一位執業律師。
洋務運動開始后,伍廷芳被李鴻章辟用,開始了一段輾轉的仕途生涯。他先在李鴻章身邊出任法律顧問,參與中法談判、馬關談判等等。后又擔任清朝住美國、西班牙等國的公使,還主持修訂晚清法律。辛亥革命爆發后,伍廷芳又陸續擔任了民國外交總長、南京臨時政府司法總長等職。
1917年,年逾70的伍廷芳赴廣州參加護法運動,5年后,因陳炯明的叛變驚憤成疾,逝于廣州。
》最富的法律人:李嘉誠
要說李嘉誠(1928-)是法律人,肯定很多人不相信。事實上,李嘉誠獲得過3個國家或地區的4所高校授予的名譽法學博士學位,分別是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英國的劍橋大學、加拿大的卡加里大學。早在1985年,李嘉誠就被選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李嘉誠雖然未曾進過法律院校,但其好學的品格使他比許多科班出身的法律人更加懂法。
李嘉誠可以稱得上是最富的中國法律人了,2012年的福布斯富豪榜,李嘉誠名列第十,資產超過了240億美元,這也是李嘉誠首次進入該榜單的前十名。
》最長壽的法學家:芮沐
去年辭世的芮沐(1908-2011),享年103歲,是中國近代以來最長壽的法學家。
芮沐作為中國經濟法學和國際經濟法學學科的奠基人,曾在北京大學、中國政法大學等法學學府任教。芮沐一生治學嚴謹,著作不多,對待法學教育異常重視,數十年如一日。他在70歲還堅持給本科生上課,直到2000年,92歲的高齡的他,還在帶著好幾個博士研究生。
芮沐年輕時英俊瀟灑,踢足球、游泳、騎馬、擊劍無一不通,也許對體育的熱愛正是他長壽的秘訣吧。
》游學最廣的法學家:吳經熊
吳經熊(1899-1986)一生的游學遍及世界10余個國家和地區,可謂中國游學最廣的法學家。他是浙江人,長大后入上海滬江大學學習,后又轉入天津北洋大學,在后來又轉到東吳大學。
國內輾轉多次以后,吳經熊從東吳大學畢業,赴美國密歇根大學法學院學習,1921年獲得法律博士以后,吳經熊又先后赴法國、德國等歐洲國家訪學。
在歐洲周游一圈以后,吳經熊回國任教,先后出任上海和南京等地的法官、立法委員等要職。期間,吳經熊多次受邀,前往美國哈佛大學等地講學。
1937年,吳經熊皈依天主教,全家移居羅馬,同時出任民國駐梵蒂岡教廷公使。
1966年,吳經熊再度移居,遷至臺灣。20年后,87歲的吳經熊終于徹底停止了他的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