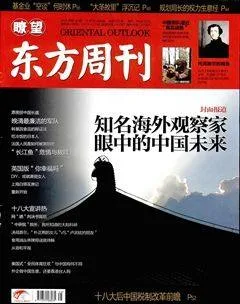愿美麗中國長盛
名山大川歷來是中國人精神之家園,無論是王維眼中“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的邊塞之雄壯,還是陶淵明“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的田園之閑適,均寄托著中國人對美麗大自然的憧憬。
但是名勝風景區的現實卻多少令人揪心,詩句中的美麗中國仿佛成了一個依稀可辨的夢境:人滿為患的景象、遍地狼藉的垃圾、突兀豪華的建筑、名目繁多的收費,將游客心中的盤景砸個粉碎。2012年國慶長假,華山大批游客的滯留,長城黑壓壓的人流,對于身處其間的每個人來說,都如同揮之不去的夢魘。
滔滔人流,帶來的不僅是經濟收益,更反映著人們對名勝古跡的向往。近日第八批國家風景名勝區名單出臺,迄今已有20g處自然景觀被納入國家級保護名錄。設立國家級名勝風景區的本意也在于此:這些區域具有觀賞、文化或者科學價值,自然景觀、人文景觀比較集中,環境優美,可供人們游覽或者進行科學、文化活動,通過保護和適度開發,讓所有人都能夠欣賞與體驗。
2006年9月頒布的《風景名勝區條例》規定了基本原則:“國家對風景名勝區實行科學規劃、統一管理、嚴格保護、永續利用的原則”。然而,規定是一回事,現狀則是另一回事。在不少風景區,“以景養景”、“靠山吃山”、大興土木的情況并不鮮見,神神鬼鬼、牽強附會的所謂文化景點亦隨處可見,而架索道、建豪華賓館、搞娛樂城等,也是司空見慣。扛著名勝的旗,謀著實在的利,至于風景的原貌、游客的體驗則變成次要的。
風景區自然文化資源是不可再生、不可取代的資源,部分景區過度開發,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以世界通行的國家公園模式為例,可窺斑知豹。
美國自1872年建立世界上第一個國家公園以來,其發展經歷了130多年,其模式的精要是:經國會通過、由總統批準、并立法保護、通過國家管理,將這些不可再生的資源直接納入國家控制。
1916年頒布的《國家公園管理局基本法》是美國國家公園進行管理的主要依據,明確提出,“保護風景資源、自然和歷史資源、野生動物資源,并在能夠保證子孫后代不受影響地欣賞上述資源的前提下,提供當代人欣賞上述資源的機會”。毫無疑問,風景資源的保護居于優先地位。
相較而言,我國《風景名勝區條例》在法律層級上還不夠高,總則第一條——“為了加強對風景名勝區的管理,有效保護和合理利用風景名勝資源,制定本條例”——沒有突出強調保護的優先次序。
該規定基于我國特殊國情而設。中國面積廣大,風景名勝區半數以上集中分布在四川、浙江、福建、貴州、云南、江西、安徽、湖南八個省區,中、西部省份居多,因經濟欠發達而導致收益不足,“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思路幾乎主導了各地風景名勝區的發展。加之中國風景名勝區管理資金主要來源于經營收入,經營盈利動機明顯。
當保護管理與經營發展之間的天平傾向于后者時,難免會導致失當和過度開發。無節制地開發名勝區,無異于竭澤而漁。
美國國家公園的經費則主要是由中央國家公園管理局通過國會預算直接撥給,同時也接受社會團體、私人慈善家的捐贈,如美國黃石公園就有專門的黃石公園基金會。在規劃設計方面,美國國家公園的規劃設計由國家公園管理局下設的丹佛設計中心獨家承擔,該中心擁有知識多元化的專家學者,全權統一負責。
英國國家公園的授權和管理同樣具有明顯的“由上至下”的痕跡。每一個國家公園都有自己的國家公園管理部門,其成員由國家和地方政府的代表共同組成,其中國家代表須占1/3到1/4。由于其人員組成的原因,管理人員與中央政府關系密切,使得國家公園能夠得到足夠的資金和外來資源,進行公園的基礎調查、專題研究及管理。
盡管我們仍然是發展中國家,但是我們已經是現代國家,我們追求的是人類的進步和文明。風景名勝資源是難以再生的,任何鼠目寸光、急功近利式的開發利用,都會帶來難以挽救的災難。在保護和利用風景名勝資源方面,發達國家的經驗值得早些借鑒。
剛剛結束的十八大提出了建設“生態文明”的目標,可視作對風景名勝區發展戰略的方向性調整。科學發展、和諧發展、可持續發展,這些人們耳熟能詳的觀念恰恰是對自然文化資源最切實的理解和態度。愿美麗中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