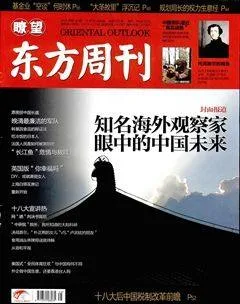日本人如何看待中國未來
2012-12-29 00:00:00陳言
瞭望東方周刊 2012年48期

如果日本經濟持續原地踏步,中國以7%~8%的速度飛速前行,到2020年中國經濟等同于美國的規模躍居世界第一時,日本怎么辦?在日本有識之士心里,這已經是個必須立即開始思考的問題
對現在的日本人來說,中國已經是生活中無法缺少的一部分。在東京乘客最多的山手線輕軌上坐半個小時的車,如果沒有聽到中文,就會讓人有些奇怪。每年過百萬的中國人到日本旅游,將中國的語言、文化、商品等帶到了日本的各個角落。
釣魚島爭端之后,日本似乎更多了些“厭華”的氣氛。于是,在東京街頭,人們一邊穿著中國制造的服裝,在餐館里吃著中國加工的食品,一邊指著電視對中國社會品頭論足。9月中國一些城市抗議游行的鏡頭如同剛剛發生的事件一樣,不斷在電視里播放,其反復程度近年少有。
這種現象今后或許還會持續很多年,但到了2020年或2030年中國的經濟規模達到很多日本政治家所崇拜的美國的水平時,日本人的對華態度恐怕也會改變了。而他們心里也清楚,這樣的情形可能為期不遠了。
如果中國經濟規模躍居世界第一,日本怎么辦
“我們也許用不了太長時間,就會失去在中國面前的優越感。”企業職員渡邊泰三對《瞭望東方周刊》說。
過去10年,每年來中國訪問,渡邊看到了中國的不足,也看到了中國迅速掙脫“落后”的種種變化。過去,中國企業管理較為落后,信息化不普及,讓日本企業覺得有很強的優越感。
“我們的工廠在生產過程的自動化、銷售信息化方面,在10年前是大大超出中國同行的,但現在已經不比中國人強多少,能談得上的優勢,只是我們的經驗更豐富一些。”渡邊說。
而渡邊回到家里,和自己上大學的女兒談起學校情況時,他覺得時代已經完全變了。“我女兒出生在日本開始‘失落’的時代,到現在正好20歲,成長過程中日本經濟幾乎就沒有復蘇過。她的中國同學則根本沒有經濟失落的感覺,學習能力和消費水平基本超過了日本同學。”
如果說老一代的日本人還存有一種對中國的優越感的話,年輕的日本人已悄悄開始適應新的中日力量對比了。
這是一種在日本經濟失落、中國努力趕超,中日經濟規模平起平坐時出現的特殊感覺。但如果日本經濟持續原地踏步,中國以7%-8%的速度前行,到2020年中國經濟等同于美國的規模甚至躍居世界第一時,日本怎么辦?在日本有識之士心里,這已經是個必須立即開始思考的問題。
用示強來掩飾內心的恐懼
但中日未來力量對比的變化,投射到日本國民心態之上,卻催生了一些日本人對中國不友好的情緒。中國強,日本似乎對中國有一份友好相處之心;中國強,日本厭惡中國的人好像忽然多了起來,并且在厭惡之外又增加了幾分恐懼感。
日本內閣府2011年的調查結果顯示,盡管美國在日駐軍基地經常發生強暴日本婦女的事件,但日本人中對美國持有好感的仍占到81.9%,而對中國有同樣感覺的人為26.1%。7012年前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全面挑起中日領土紛爭后,這一數字恐怕還要下降。
“眼下日本正處在選舉階段,除了能聽到各個政黨要‘捍衛日本領土’、進駐島嶼的呼聲外,卻從來聽不到日本該如何處理與周邊國家關系的理性聲音。”早稻田大學一位專攻亞洲關系的中國留學生對本刊記者說。
甚至一些家庭婦女談起日本的對外關系時,也從過去的“不再戰”(不再打仗)、“救助弱者”等話題,漸漸轉向領土問題,并表現出強烈的“愛國”情緒。
《網絡與愛國》一書的作者安田浩一在解釋日本出現的變化時說:“很多日本男性參加游行,主要出于政治目的,有時也是一種發泄感情的方式,但女性上街游行,參與政治爭論,則往往源于她們對社會的絕望和心頭的危機感。”經濟的長期失落,政治上的動蕩,在無法找到出路的時候,不少日本人便把這種情緒放在了對外關系上,用示強來掩飾內心的恐慌。
“日本仍然必須在中國做下去”
釣魚島爭端惡化之后,不少日本企業開始強調“中國+1”,希望通過一個中國之外的市場,來分散中國市場上的風險。
但日本經濟產業省一位負責亞洲事務的官員對本刊記者說:“今后5年到10年時間內,無論是印度還是東南亞,都不能取代中國市場,日本仍然必須在中國做下去。”從零部件基地的建立到現代化物流體制的構筑,再到成品的組裝銷售,再加上民眾消費水平的提高,中國只用二三十年時間就實現了。在世界其他地方重建一個和中國相當的市場,幾乎是不可能的,也是日本經濟現有的能力所等不起的。
“問題是,現在日本經濟開始和政治脫節,企業實現了全面跨國化,而政治依舊停留在日本國內,政治家不顧國家經濟利益,按自己的想法搞亂了國家間的關系。”日本一家大報的主編對記者說。
于是,當日本看不到走出經濟困境的出路,保守政治又影響至深的時候,在日本聽到的最高的聲調,就是唱衰中國。書店里充斥著不少對中國政治制度持全面否定觀點的書籍,對中國經濟可能取得的發展視若無睹,很多人寧肯相信明天的中國一定會問題更多,而不去為中國的真正崛起做好準備。日本眼下這種缺乏自信和冷靜的心態,令日本的一些有識之士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