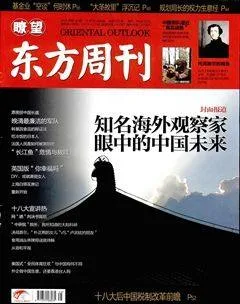從容和平視
2012-12-29 00:00:00劉伊曼
瞭望東方周刊 2012年48期

“不要老說‘自由’、‘自由’——我不說這話。我的感覺就是回歸民族,回歸老百姓。”
“賣了我,就是餓死也別賣孩子了,中不?”近期上映的電影《一九四二》中,當(dāng)花枝說完這句話坐上馬車漸行漸遠(yuǎn),影院里回旋起一段揪人心肺的旋律。
并沒有復(fù)雜的配器,兩種簡單的樂器——小提琴和簫——演奏出深沉綿延的憂傷。
這段音樂是音樂家趙季平和他的兒子趙麟合作創(chuàng)作的。
“這部電影之所以找我爸作曲,是因為我爺爺曾經(jīng)在黃泛區(qū)畫過大量的寫生,畫過這些苦難的人,而且在《大公報》上刊登了。”趙麟對《瞭望東方周刊》說。
父親
趙麟口中的“我爺爺”是趙望云,國畫家,長安畫派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生于1906年。
上個世紀(jì)二十年代末,趙望云的畫作已見諸報端。1932年,他開始了記者生涯,以一支畫筆為《大公報》做“寫生通訊”。
從候車室的平民,到村頭抱小孩的婦女……趙望云的畫作很少著意雕刻或者渲染,畫面干凈、簡潔,水墨中的意蘊卻能打動人心。
1933年,馮玉祥曾為《趙望云農(nóng)村寫生集》作序,寫下了這樣的文字:
“近年來,中國農(nóng)村的破產(chǎn),可以說達(dá)到了極點,這是毫無諱言的事實。但是人民究竟在一種怎樣痛苦的狀況中生活著呢?恐怕是很少有人去注意到吧!在趙君這一部寫生畫里,卻已很生動地告訴我們了……”
在自序里,趙望云表達(dá)了對時局和未來深沉的擔(dān)憂:
“如此樸實勞苦的貧民生活,現(xiàn)下已逐趨向不安與動搖!如果等到數(shù)年之后,拙作寫生通訊,或許要看成中國農(nóng)村過去的黃金時代,也未可知?”
歷史不幸如其所言,其后十?dāng)?shù)年間的中國,飽受戰(zhàn)爭蹂躪,每下愈況。畫家步履之處,是越發(fā)深重的苦難。
1947年,國共內(nèi)戰(zhàn)全面爆發(fā)后,胡宗南在延安看到共產(chǎn)黨中央辦公廳的會議室里掛著一幅畫。那幅畫是周恩來買的,作者正是趙望云。沒多久,趙望云就以“通共”的罪名被逮捕了。
1948年到1949年間,年幼的趙季平曾經(jīng)被母親帶著到監(jiān)獄去探視過父親。不久,骨肉分離的苦痛隨著新中國的建立而消除。困頓和成長
1970年,25歲的趙季平從西安音樂學(xué)院畢業(yè)后,被分配到陜西省戲曲研究院。
“工作跟作曲風(fēng)馬牛不相及,”趙季平對本刊記者回憶,“當(dāng)時我父親正被下放農(nóng)村,我去找他,跟他說工作分配得不好,到了戲曲研究院。我父親說,分得好啊!你在學(xué)校學(xué)的是技術(shù),你在那兒(戲曲研究院)學(xué)到的是中國傳統(tǒng)的藝術(shù)文化,那是最好的地方。我父親說去,我就去了,一直在那個單位待了21年。這個經(jīng)歷對我后來的作曲起到了莫大的作用。”
1973年,趙麟出生。今天的趙麟對“文革”沒有什么記憶,他只是后來知道,那個時候爺爺趙望云被打成“黑畫家”,經(jīng)常下午就被拉著去游街。“我奶奶受很大刺激,‘文革’結(jié)束后很久,一聽到高音喇叭,她都會緊張兮兮地問‘又整誰啦?’。”
在那段非常歲月里,年輕的趙季平比他父親幸運:他有很多時間行走在田間地頭,在采風(fēng)的旅途中汲取民間音樂的營養(yǎng)。
讓也是搞音樂的兒子趙麟覺得欽佩不已的是,趙季平在上世紀(jì)70年代就開始用西方交響樂的理念為民族樂團配器的嘗試。那時候戲曲樂團下鄉(xiāng)表演樣板戲和秦腔唱段,趙季平就用五線譜配器,一部戲配下來譜子能有一尺多厚。要把民族器樂不成體系的“散板”納入到交響樂嚴(yán)謹(jǐn)?shù)目蚣芙Y(jié)構(gòu)里,是一件非常難的腦力活兼體力活。
和父親趙望云說自己“生活上的責(zé)任”是要到民間去,畫自己身歷其境的事物一樣,趙季平對本刊記者說,作曲家的職責(zé),也應(yīng)當(dāng)是“回歸民族,回歸老百姓”,不僅如此,還要能“與世界對話”。
從容和平視
1976年9月的一天,趙季平所在的戲曲團剛到一個偏遠(yuǎn)的村子巡演,毛澤東去世的消息傳來,所有文娛活動即刻中止。戲曲團一連被困數(shù)日,沒有交通工具回去,也不能繼續(xù)表演,只能閑著。
一個月之后,“四人幫”垮臺,這個國家開始了新的歷史階段。趙季平的音樂人生也奏響了新樂章。
1984年,依靠自己幾十年陜北生活的積累,趙季平駕輕就熟地為陳凱歌導(dǎo)演的電影《黃土地》配樂,獲得廣泛的肯定。但在他自己看來,那時還處于探索階段。在后來的影視音樂創(chuàng)作中,他以非常規(guī)的手段、構(gòu)思、結(jié)構(gòu)去表現(xiàn)諸多新時期影片特有的內(nèi)涵。
如1987年為張藝謀導(dǎo)演的電影《紅高梁》所寫的音樂,據(jù)他回憶,創(chuàng)作時特別注意到紅高梁是山東的東西,“所以要用大北方的概念,把人性噴發(fā)的東西張揚出來。”他為這部電影創(chuàng)作的音樂和電影一起成為了那個時代的一個文化回憶,并獲得了第八屆“金雞”獎最佳作曲獎。
在給1991年的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張藝謀導(dǎo)演)寫音樂時,他說自己開始了“從音樂的角度去結(jié)構(gòu)故事背后的思想”,用專屬于“三太太”的京劇風(fēng)貫穿始終,“哲學(xué)層次上去了。西皮流水形成了一個循環(huán)圈,從這個大院里婦女的命運中提升出一種悲劇性的東西。”
如果說上述這些探索意味濃厚的新時期電影可大致歸為一類的話,后來的《大話西游》、《孔繁森》、《烈火金剛》、《秦頌》、《水滸傳》等影視作品基調(diào)已各各不同,而作為這些影片的音樂創(chuàng)作者,趙季平始終能從容地完成風(fēng)格各異的“命題作業(yè)”。他也藉此成為我國目前電影音樂界獲獎最多、獎次最高的音樂家。
這“從容感”,他自己解釋為來自藝術(shù)和生活兩方面的長期積累,“臨時抱佛腳是不行的”。
而“從容感”,以及始終“平視”的姿態(tài),是他反復(fù)提及的藝術(shù)立場。
“也就是沒有俯視、仰視,沒有說教的東西在里面?”本刊記者問。
“不說‘說教’——這詞很敏感。‘平視’就是沒有俯視也沒有仰視。就是要有一種平等的心態(tài),老百姓的心態(tài)。”他答。
回歸民族,回歸老百姓
網(wǎng)絡(luò)搜索一下,可以發(fā)現(xiàn)趙季平有著或曾經(jīng)有過很多社會組織或官方的頭銜:西安音樂學(xué)院院長、中國音樂家協(xié)會主席、陜西省文聯(lián)主席、黨的十五大代表、陜西省第十屆政協(xié)委員,等等。還曾獲得過國務(wù)院有突出貢獻(xiàn)的專家、全國文化系統(tǒng)先進工作者等稱號。
這讓有些人感到困惑,也引發(fā)了一些微詞——覺得作為一位音樂家,他“不夠純粹”。
面對本刊記者“你作為一位音樂家如何應(yīng)付社會乃至政治方面的各種影響”的疑問,趙季平淡然說:“這個問題應(yīng)該從另一個角度來說。作為一個作曲家,中國的作曲家,應(yīng)該給自己的民族,給自己的人民,寫出更多好作品。在音樂這方面,現(xiàn)在我們的創(chuàng)作是非常開放的。”
“你曾經(jīng)說現(xiàn)在的‘紅歌’創(chuàng)作也要體現(xiàn)終極的人文關(guān)懷。怎樣實現(xiàn)這種終極關(guān)懷?”本刊記者問。
“我覺得還是要上升到一種更平實的東西,讓人感到溫暖和親切——你去體會吧。”
“從神壇上走下來?”
“我不說這話。我在寫音樂的時候,我和我的對象,和所有的對象是平等的。我希望我們都用這樣的心態(tài)去創(chuàng)作,寫出來的東西可能更有生命力。用老百姓的心態(tài)去創(chuàng)作,你永遠(yuǎn)會感受到,你是這個民族的一分子。你應(yīng)該為了這個民族去創(chuàng)作。”
“不管面對什么對象,什么要求,你內(nèi)心始終能保持這種自由的創(chuàng)作狀態(tài)?”本刊記者最后問。
“不要老說‘自由’、‘自由’——我不說這話。我的感覺就是回歸民族,回歸老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