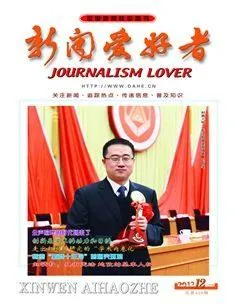淺析調解類電視節目的儀式傳播

【摘要】民間調解儀式通過電視呈現,在傳遞價值觀、社會整合和城市文化共同體的構建方面具有較大的作用,本文將以《新老娘舅》節目為例,從傳播儀式觀的視角對調解類電視節目的儀式傳播進行分析和研究。
【關鍵詞】新老娘舅;電視調解;儀式觀;儀式傳播
在社會轉型期,社會結構的重新調整和巨大變動,使得人們承受著比平穩時期更大的壓力,同時,各種矛盾和困惑影響著人們的生活,從而出現了社會人際關系的緊張、家庭危機增多等現象。在這一特殊的社會大背景下,糾紛調解類電視節目應運而生,承擔起特殊的“老娘舅”的角色。
據統計,2011年上半年,全國71座城市有38個頻道播出了調解類節目,其中省級衛視頻道4個,地面頻道34個。[1]美國傳播學者詹姆斯·凱瑞提出的傳播儀式觀指出,傳播不單是一種傳遞信息或影響的行為,還是共同信仰的創造、表征與慶典,是將人們以共同體或共同體的形式聚集在一起的神圣典禮。在凱瑞看來,“傳播的儀式觀并非直指訊息在空中的擴散,而是指在時間上對一個社會的維系;不是指分享信息的行為,而是共享信仰的表征”[2]。
本研究將運用儀式觀的研究視角對《新老娘舅》這類調解類電視的儀式傳播進行研究,試圖去了解當下走紅的調解類節目的儀式表征及其儀式傳播的功能。
電視調解儀式的構成
儀式是人類歷史中古老、普遍的文化現象,而“傳播儀式觀的研究,不是把傳播過程視為相互間的信息發送或獲取,而是將其視為參加一次神圣的彌撒儀式。在參加這個儀式的過程中,人們并不關注是否學到了什么新的東西,而是注重在規則化的儀式程序中使特定的價值觀和世界觀得到描述和強化”[3]。而調解儀式是中國民間最為普遍的一種解決糾紛的方式,電視調解正是脫胎于此。
在調解類電視節目《新老娘舅》中,每期有一名相對固定的主持人和一位被邀請的老娘舅(即調解員),一般而言,節目會邀請兩名(或兩群)糾紛當事人,雙方各自闡述糾紛的原因,在這一環節中,一般由求助一方的“被調解者”先陳述內情,接著,請另一方“被調解者”進行反駁、補充和“辯論”。在雙方的陳述過程中,往往出現言語、肢體的沖突。在雙方面對電視節目所組織的少數現場觀眾及大多數虛擬的電視機前的觀眾進行聲淚俱下的陳述時,調解儀式往往會達到高潮。而在此過程中,調解員(即老娘舅)除了進行言簡意賅的提問外,多以觀察為主,主持人擔當“穿針引線”的作用。在故事情節和糾紛矛盾介紹基本清楚的情況下,“老娘舅”正式“發言”——他首先會對糾紛矛盾進行梳理,其次,對被調解者“各打五十大板”——指出各自不足與錯誤,點明各自應讓步的空間,接著,對雙方的訴求進行協調并商討出一個較合理的解決方案,讓被調解雙方在節目錄制現場的觀眾及“電視觀眾”的見證下達成口頭或書面的調解協議,節目結束。
電視調解儀式與日常生活中的調解儀式最大的區別在于,前者充分運用了電視這一媒介手段。因此,當電視媒介介入儀式后,原本只局限于局部人群的調解活動被置于廣大電視受眾面前,調解儀式原本相對私密的性質被徹底改變了,如此一來,調解原本所具有的深層意義有可能被弱化,而調解儀式中表演的性質則大大加強。其次,電視媒介介入調解儀式后,調解儀式的過程和節奏徹底被媒體改變、規定和控制,電視媒體不是再現調解儀式的過程,而是再造了調解儀式。儀式過程完全要按照電視拍攝的需求進行,拍攝成了儀式的主體,儀式及儀式中的主體卻成為拍攝的道具,同時,調解儀式也必須在符合拍攝條件的攝影棚中進行,這自然改變了儀式文化的空間感。
調解類電視節目的表征
美國學者喬治·格伯納與拉理·戈羅斯在《與電視共同成長:涵化過程》一文中指出:“自工業化前的宗教以來,也許是電視才首次提供了一種精英們和其他公眾都能共享的日常儀式。如同宗教一樣,電視的社會功能依賴于故事(神話、‘事實’、經驗等)的持續性重復,而這些故事又是為界定世界以及使一種特定的社會秩序合法化服務的。”[4]
調解類電視節目作為一種“講故事”的藝術,一種真實的敘事形態,猶如電視系列劇一般(有時因糾紛矛盾激烈,此類節目如電視連續劇般分成上下集),依托現代媒介的技術手段,在現代社會中發揮著“集會”一般的儀式功能。此類調解類電視節目通過普通人之間真實發生的故事,為觀眾(參與者)提供一種直接和擴展的某種共享的經驗,用來支撐社會及公眾共享的價值觀和信仰。
為了更好地考察調解類電視節目的儀式表征,筆者在土豆網以“新老娘舅”為關鍵詞進行搜索,按照播放量篩選出2012年居前的10個節目(如節目有上下集將以同一個節目計算),統計如表1:
文化展演:主流價值觀的表達。維克多·特納在《儀式過程:結構與反結構》中,通過對非洲部落的田野考察發現,部落內部通過定期的儀式來緩解矛盾沖突,而這些儀式都是圍繞著某些“主要象征”——主要指狩獵、農耕、繁衍等社會存在的基本需要和美德等共有的價值觀而組織起來的,“主要象征代表著結構的秩序,以及秩序所依靠的價值與美德”[5]。調解類電視節目的儀式表征中,責任、平等、尊重、和睦等傳統倫理道德為觀眾傳遞著主流意識形態的價值觀和行為標準。從表1可以看出,此類調解類節目承擔著傳播主流傳統價值觀的重要任務,具有輿論導向的功能。中國有著深厚的文化歷史積淀,尤其以儒家的“仁義禮智信孝”等為代表的核心傳統價值觀深深地影響著中華民族的一代代兒女,在當前傳統價值觀受到挑戰和瓦解的當下,此類調解類電視節目重新向觀眾展示、確認道德的底線和主流的價值觀,這正是這類節目的主要表征。
此外,此類調解類電視節目因具有較好的觀眾口碑,也打造出了一個個調解明星,如《新老娘舅》節目的調解員柏萬青,已然成為觀眾心目中的“社會價值維護者”。
秩序幻象:和諧穩定的確認。調解類電視節目向觀眾呈現的是五花八門的各類矛盾,如夫妻矛盾、贍養矛盾、財產糾紛、兄弟失和,等等。但是,調解類節目除了通過調和這些激烈的矛盾以獲取收視率外,并非想向觀眾傳遞社會混亂的負面印象,相反,調解類節目以其較高的調解成功率,傳達給觀眾一種穩定、可期待的“秩序幻象”。
具體以《新老娘舅》節目為例,在表1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在10個節目中有9個節目得到了成功調解。此外,即使調解不能達成一致,最后節目主持人通過結束陳詞,也能給觀眾傳遞出“矛盾是可控的”“調解仍留有空間”等信息,從而達到維護良好秩序、營造高尚品德的社會核心目標。
調解類電視節目的儀式傳播功能
伊芙特·皮洛指出:“儀式的奧秘和力量在于它的普遍性……儀式是一種社會的約束,是一套共同使用的語言,是一條紐帶。”[6]這條紐帶聯系起了電視節目和觀眾。其實,調解類電視節目的力量不僅來自儀式形式本身,還出自儀式的意義。
城市作為一個生人社會,傳統族群中調解的功能越來越削弱,從調解的效率來看,電視調解根本無法成為一種主流的調解渠道,但是卻因為電視受眾的廣泛存在,使得調解類電視節目可以承擔起傳播社會共同信仰、價值觀和規范的功能,在某種程度上發揮一種“社會神話”般的儀式傳播功能。
社會整合功能。人類學家格魯克曼認為:“社會是因具備解決沖突和對立的機制而成為整體,而儀式在建構社會結構的過程中,主要在兩個方面發揮作用:一是夸大社會規則的自相矛盾,二是通過象征形式上的展演讓社會群體中的個人獲悉‘雖然有些許沖突,但社會仍舊統一’。”[7]
在調解類節目《新老娘舅》中,節目雖然展示的是沖突和矛盾,且節目組不乏有夸大矛盾的做法,如在節目播放過程中插入大字幕、制作出各類動漫效果以渲染矛盾的激烈,但節目的導向仍是家庭、社會的人際倫理價值。此類調解類節目往往放大的是以家庭矛盾為主的“小矛盾”,進而回避了一些社會熱點矛盾,轉移了觀眾的注意力和視線,讓處于社會底層的觀眾看到比他們更為底層的人的原生態的存在,從而間接地起到了“社會減壓閥”的作用。
此外,傳播的儀式觀把傳播看作是一個創造、修改和轉變共享文化的過程。在凱瑞看來,傳播的本質并不在于控制,而是一種文化儀式。媒介是文本的呈現,是供人類參與其中的戲劇舞臺。《新老娘舅》這一電視調解節目雖然也傳遞信息,但更多的是展示正義與非正義、公平與非公平的角逐和斗爭,觀眾收看這類節目,相當于替代式地置身于變幻不定的角色或舞臺的中心,而《新老娘舅》節目以方言為主要語言,并邀請平民擔任“老娘舅”,使得“本土”“親和”“情感”這些關鍵詞成為能夠“召喚”大多數百姓參與節目的重要因素,從而起到社會整合和城市文化共同體的構建作用。
價值認同功能。凱瑞借助儀式展演過程中人們所處的精神情狀,認為傳播不僅僅是信息的物理流動,更是人們對“意義的分享”。在參加儀式的過程中,人們并不關注是否學到了什么新的東西,而是注重在規則化的儀式程序中使特定的價值觀和世界觀得到描述和強化。
調解類節目每天播放的無非是房產糾紛、遺產(遺囑)糾紛、老人贍養糾紛、婆媳沖突、夫妻矛盾等,高重復度的題材為何能夠吸引受眾?其實,受眾主要并非期望從節目中獲取信息,從儀式觀的視角來看,受眾通過“參加”這樣一場調解儀式,再次確認并認同了公正、公平、誠信、慈孝等社會主流的價值觀。
結 語
電視調解類節目以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觀為取向,深入到了民眾生活的細部,一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收視成績,另一方面也弘揚了中國傳統的道德觀念。然而我們也可以看到,個別節目為了迎合觀眾的獵奇心理,刻意追求視覺刺激,過度渲染調解中當事人的肢體、言語沖突,讓調解變成一場鬧劇和表演,不僅破壞了調解儀式的嚴肅性,更將調解當事人變成電視節目的消費品。因此,我們應該從儀式觀的視角重新打量電視調解類節目,從社會整合和主流價值觀傳播的角度來進行節目的編排和設計,使節目真正得到老百姓的認可。
參考文獻:
[1]馮波.調解類節目“收視之道”解析[J],收視中國,2011(7).
[2]詹姆斯·W·凱瑞.作為文化的傳播——“媒介與社會”論文集[M].丁未,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5.
[3]王晶.傳播儀式觀研究的支點與路徑——基于我國傳播儀式觀研究現狀的探討[J].當代傳播,2010(3).
[4]喬治·格伯納.與電視共同成長:涵化過程[A].新聞與傳播評論:2004年卷[C].武漢:武漢出版社,2005.
[5]維克多·特納.儀式過程:結構與反結構[M].黃劍波.柳博赟,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93.
[6]皮洛.世俗神話[M].崔君衍,譯.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91:44.
[7]Gluckman Max.Order and Rebellion in Tribal Africa. London:Routledge.1961.
(作者為上海交通大學媒體與設計學院碩士生)
編校:董方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