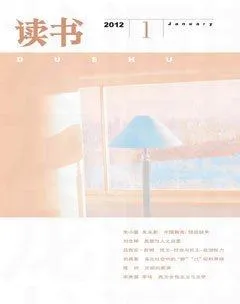布滿沮喪的英雄時代
一條黃瓜的風波讓素以食品安全(其食品與藥品的監管最為規范嚴格)為驕傲的德國顏面盡失,同時令其鄰國西班牙(被指稱是毒黃瓜的源頭)蒙冤受屈,后經中德兩國醫學家聯合稽查,原來是出血性大腸桿菌在作亂。大腸桿菌是與人類共生的一種細菌,很少有作亂的前科,屬于細菌世界里的“乖孩子”,這回卻因為兩種細菌的基因鏈接產生惡變,變成一頭暴虐的怪獸,讓人類猝不及防,更有意思的是專家的治療建議不是揮舞抗生素的大棒去彈壓,而且不妄止瀉,讓病人多喝水,加快排泄,以利排毒。這讓人聯想到兩百年前流行的自然排泄原則(放血、催吐、利尿、通便)。因此,對于某些不明感染的暴發,避其鋒芒的自然療法還有積極意義,尤其是在超級細菌不斷孽生的后抗生素時代。
平心而論,這個突發事件在人類與疾病的抗爭史上只是一個轉瞬即逝的小插曲,不值得格外驚異,但它也明白地告訴人們一個樸素的道理,醫學的社會圖景不過是人類健康與疾病版圖的消長與博弈,現代醫學的進步使得天平向著理想狀態傾斜,為人類贏得更多的健康,更少的疾病。不過,醫學無論如何進步,疾病的版圖永遠也不會消亡。一城一地的得失并非最后的勝利,人類無法抹去徘徊于心頭的深深敬畏。
對待人類疾病的波譎云詭,我們不僅需要高倍的顯微鏡去探幽索微,還需要歷史的長鏡頭與社會學的廣角鏡去撥萬輪千。王紅漫的新著《醫學社會學讀本》就是這樣的廣角鏡與長鏡頭。在作者的筆下,二十世紀的醫學攻城略地,可歌可泣,抗生素的發明掃蕩了細菌性感染的千年巢穴,也宣告了醫療戰爭模型的誕生,器官移植與人工器官使得醫療干預超越了有限的自身修復,開辟了醫療替代模型的航道,基因檢測、高分辨影像技術讓疾病的早期發現、早期治療成為可能,醫學的生活化(醫療美容、換膚、變性,性愛與生殖義務分離,延緩衰老藥物等)更令人類求美、性愛、長壽、永生的欲望愈發高企??現代醫學顯赫的成績單足以讓歷史學家將它界定為英雄的時代。而戰后WHO的登場,更刷新了疾病防控與全球衛生戰略統籌的歷史。然而,作者也毫不掩飾地描述了疾病無時不在大舉反撲或悄悄地偷襲人類。君不見,超級病菌正越過抗生素的鐵壁銅墻重新集結,抗生素絞殺的大多是普通的病菌,幸存的病菌大多具有更強的適應生存能力,在抗生素鋪天蓋地濫用的環境中通過變異演化為“刀槍不入”的超級細菌。新病毒的奇異魔方接二連三地造就了瘋牛病、艾滋病、“非典”、埃博拉出血熱等世紀恐慌,那些早已被現代醫學基本征服的傳染病(鼠疫、霍亂、結核、麻疹、瘧疾、血吸蟲病)又在試圖卷土重來,伴隨人類長壽和現代生活方式而至的心腦血管病、糖尿病、車禍、癌癥長期盤踞在死因排行榜的高位。自然環境崩潰與報復所造成的極端氣候變化和污染,道德敗壞所致的食品、藥品的假劣危害對健康帶來空前的威脅。因此,醫學的當代命運如同“雨天背米,越背越沉”,印證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隱喻。對于人類健康和現代醫學來說,二十世紀既是英雄的時代,也是沮喪的時代。
英國歷史學家懷特(Hayden White)曾經將歷史敘事分為四種類型:傳奇、喜劇、悲劇、反諷(這是由于Metapher,Metonymy,Synecdoche,Irony導致的四種不同的歷史想象)。借用這樣的歷史解讀框架,現代醫學飽含沮喪的英雄時代便有了真實的圖景,人們開始從醫學社會學的嬗變與遞進里讀出了歷史深處的美學意蘊來,人類的疾苦與抗爭史從來就是一部波瀾壯闊的悲喜劇,光明與陰霾,喜悅與悲傷,進取與墮落,希望與絕望糾纏不休。
二十世紀無疑是醫學的英雄時代。不同于科學史的建構,在歷史敘事與文學敘事中,似乎沒有完美的英雄形象,不是“堂吉訶德”式的莽撞英雄,就是“拿破侖”、“項羽”式的末路英雄,高歌猛進之日,也是霸王別姬之時。英雄在順利、勝利時,都會發昏,過高地估計自身的力量。同時,擴大征服的對象。不是嗎?我們當下就有人試圖將人類基因的個體差異、非表達性基因缺陷通通歸于當下必須處置的疾病譜系,發愿進行實時監控與干預。還將正常的衰老進程、甚至壽終正寢的生命終結(無疾而終)也定義為可逆的疾病過程,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造就了沒有生命尊嚴和質量的植物人狀態。醫學的長矛不僅直逼疾病,還直指衰老,甚至死亡,生命不再無常,生老病死的進程完全可逆。在英雄主義醫學的詞典里,病魔、死神都是紙老虎,當今已經被人類逼到了墻角,不久將俯首臣服。同時,WHO健康標準與解讀的擴大化,也使得現代醫學越來越力不從心。因此,我們對醫學征程中的“英雄主義”應該有清醒的認知,應該告誡人們,任何時候都不可驕縱輕狂,面對自然,面對生死,必須充滿敬畏。每一個世間的凡夫俗子都是被“開除”的神仙。生命中注定會有無限的煩惱、困境,注定要經受疾苦的折騰與折磨,注定不能長生不老,更無望長生不死。
無疑,滋長與支撐現代醫學英雄幻象的是披在他身上厚重的技術主義戰袍,如果卸下厚厚的技術鎧甲,我們的氣勢還會如此飆揚嗎?我們的精神還如此強壯嗎?或許,有人會反詰,為什么不能將技術的鎧甲作為英雄的搏擊資本?現代技術不是已經物化為人類的衛生福利了嗎?是的,無法抹殺技術在現代醫學發展中的功勛,但是,他只是人類謀幸福、謀健康的工具,不是醫學的目的與價值歸依,技術的異化已經帶來了諸如客觀性危機(高負擔、過度診斷),技術化的醫患失語,衰老、死亡定義的顛覆(關機時間,抑或停電時間),滋生了永生的奢望以及對衰老、死亡的違拗和堅拒,改變著醫學的目的與承諾。技術主義與消費主義的結盟正在改變著醫學的命運,成為人類無法承受的福利重負,全球的健保系統都面臨著破產,都呼喚著生命、健康、疾苦、醫學觀念與醫療體制的改革。因此,作者在書中基于全球化視野的衛生攻略還不足以破解當下的醫學社會學難題,我們還需要一套靈魂攻略,去破解技術主義與消費主義的作繭自縛。期待作者不久有新作來拓展這些話題。
(《醫學社會學讀本——全球健康國際衛生攻略》,王紅漫著,北京大學醫學出版社二○一○年十一月版,2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