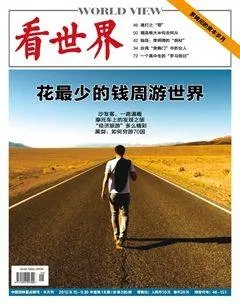渣打之“罪”
2012-12-29 00:00:00關照
看世界 2012年18期


1983年10月23日,黎巴嫩首都貝魯特,清晨6點半,一輛滿載炸藥的卡車沖過哨卡,撞向駐貝魯特的美軍海軍陸戰隊總部大樓,威力相當于12000磅TNT的炸藥將4層大樓完全炸毀,241名美軍士兵在襲擊中喪生。這是珍珠港事件后,美軍士兵遭遇的最血腥的一天。
調查后美方認定,伊朗是爆炸案的元兇之一。2007年9月,華盛頓特區聯邦法庭判處伊朗政府賠償受害者家屬26.5億美元,但是這筆錢遲遲沒有兌現。2012年8月15日,受害者家屬再度提起訴訟,這一次他們將英國渣打銀行推上了被告席。
“瞪羚”計劃
一樁過去了29年的爆炸案,在美國和伊朗之間突然插入一個最新的當事方——英國渣打銀行。這聽起來讓人覺得匪夷所思。對此,原告方提出來的理由是,渣打銀行曾協助伊朗方面隱瞞資產,以逃避26.5億美元的賠償。那么渣打銀行和伊朗之間究竟有著什么樣的利益瓜葛呢?這一疑問被炒得沸沸揚揚。而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此前一天,渣打銀行剛剛從另外一起與伊朗有關的案件中抽身,它付出的代價是3.4億美元的和解金。而在這一案件中,原告紐約州金融服務局的指控理由是:渣打攪亂了美國對伊朗的金融制裁。
8月6日,美國紐約州金融服務局,一個剛成立10個月的監管部門公布了一個長達27頁的金融監管令,矛頭直指渣打銀行。英國金融分析人士伊恩·戈登說:“金融服務局指控渣打銀行隱藏6萬起與伊朗的交易,金額高達2500億美元。”在花了9個月的時間,調查了3萬份渣打銀行內部資料后,紐約州金融服務局認定,渣打銀行在2001年至2010年間,通過一個名為“瞪羚”的項目,幫助伊朗和其企業在金融活動中隱藏身份信息,躲避美國監管部門的審查,涉嫌違反了美國的反洗錢法令。
“瞪羚”項目的基礎之一,是電匯代碼消除技術。通過這一技術,渣打員工可以在資金轉移過程中,消除識別伊朗客戶的代碼,確保任何指令都不會帶有伊朗客戶的任何信息,從而讓來自伊朗的轉賬在不知不覺中完成。《英才》財經記者胡偉凡在接受本刊采訪時解釋道:“打個比方,一家擁有法國賬戶的伊朗企業,要把貨物賣給德國公司,用美元進行交易,就需要經過美國金融體系。而如果這家伊朗企業名列美國制裁清單,則無法通過美國監管部門的審核。而渣打銀行美國分行所做的,就是幫助伊朗企業隱藏其身份,改頭換面,使交易可以順利完成。這就像是在美國為伊朗筑起的制裁高墻上開鑿了一個洞,負責鑿洞的渣打銀行也獲得了高額的手續費。”
對此,紐約州金融服務局局長勞斯基評論說:“渣打的行為讓美國金融系統暴露在恐怖分子、軍火商、毒販組織和腐敗集團的風險中。”勞斯基毫不客氣地指責渣打銀行是受利益驅動的流氓貪婪機構,并威脅要吊銷渣打在紐約州的金融執照。《紐約商業周刊》估計,如果失去這一金融牌照,渣打的盈利將會失去40%。倫敦城市大學教授羅巴克評論說:“當你用美元交易時,這些錢需要經過美國,主要是在紐約。如果失去紐約州的經營牌照,就意味著美元交易受限。而世界上大多數的交易都是用美元。”
對于紐約州金融服務局的指控,渣打銀行一開始堅稱在接受調查的交易中,99.9%都是合法的,只有1400萬美元的交易可能涉及違規。渣打銀行總裁桑茲辯稱:“我們拒絕接受金融服務局的指控和他們對事情的描述,對于事實我們有不同的解釋。”按照原計劃,渣打需要在原定于8月15日舉行的聽證會上出示證據,以證明自己的清白。而就在聽證會舉行的前一天,渣打選擇了與紐約州金融服務局達成和解,渣打承認自己與伊朗曾有達2500億美元的不合法交易,向紐約州金融服務局繳納了3.4億美元的罰款,就此保住了營業執照。
此外,渣打銀行還同意在紐約分行設立一名監督者,監控銀行內部的洗錢風險控制情況,并任命專職人員審核每一筆海外交易,以保證不再觸犯美國的反洗錢法律。
政客們的籌碼
紐約完勝,渣打妥協。此案傳遞出非常明確的信息:只要你與伊朗交易,美國就會揮舞大棒。白宮發言人卡尼在記者招待會上說:“對于違反制裁的行為,美國政府向來嚴懲不貸。”美國對外經濟制裁始于1919年威爾遜總統的一次講話:“一個遭受抵制的國家,就是一個即將投降的國家。運用這種經濟的、和平的、平靜的但致命的手段,就沒有必要訴諸武力。”冷戰后,經濟制裁由一種國家間的對抗工具,演變為一種國際干涉手段。
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之后,伊朗成為美國經濟制裁主要對象之一。《伊朗制裁法》是美國制裁伊朗的國內法主要依據。而近年來,隨著伊朗核問題日趨緊張,美國的對伊制裁也不斷升級。美國2012年國防預算法案中規定:凡與伊朗央行或伊朗其他金融機構發生重要金融業務的外國金融機構,將不得在美國開設或保留銀行賬戶,外國央行如果涉及伊朗石油或石油產品買賣業務也將受到同樣制裁。對此,羅巴克教授解讀說:“任何人和伊朗有交易,都是絕對合法的,但前提是你不在美國。如果在美國,將變得不合法。”
值得注意的是,渣打的案件并非最近才發生,但偏偏在此時被美國瞄準,時機選擇耐人尋味。英國金融分析人士史密斯說:“不得不提,今年是美國的大選之年,打擊外國銀行對政客來說很有吸引力。”而英國《金融時報》認為,在大選前的政治博弈中,伊朗作為幾個少數突出外交政策問題之一,不會被輕易放過。懲辦渣打,既整治了金融業,又收緊了對伊朗的制裁,可謂一箭雙雕。事實上,早在紐約州金融服務局成立以前,美國司法部、財政部、美聯儲和紐約曼哈頓地區檢察署就已經開始著手調查渣打銀行為伊朗洗錢的行為。
按照慣例,在調查洗錢案時,監管部門一般會協調聯動,選擇最佳時機出手。而此次,成立僅10個月的紐約州金融服務局單槍匹馬,突然出手,讓美國的監管同行們也頗感意外。史密斯分析說:“這就像是有人在比賽中搶跑,其中有不少蹊蹺之處,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美國國內政治的問題。”
斯皮策和科莫,兩人都因曾打擊華爾街的違法行為來擴展其政治地圖,先后成為紐約州第54任和第56任州長。英國《衛報》把此次渣打案中大出風頭的紐約州金融服務局局長勞斯基的名字和前兩位排在了一起,《衛報》評論說:“或許勞斯基局長也想成為他們的追隨者?”
隨著渣打銀行與紐約州當局達成和解,這場渣打八月風云似乎告一段落。但是渣打接下來又該如何應對黎巴嫩爆炸案受害者家屬的指控,繼續撇清自己和伊朗的關系呢?是否還要繼續破財消災,大事化小?這仍然值得關注。一邊是全球化下熱熱鬧鬧的金融圖景,另外一邊是國際政治角力中經常亮出的冷冰冰的金融制裁手段。身為金融機構,身處其間,確實是在夾縫中求生存。所謂渣打之“罪”,套用中國的一句老話是:人在屋檐下,卻不肯低頭。而它最終又不得不服軟認輸。這既是因為美元的強勢,也是由于美國的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