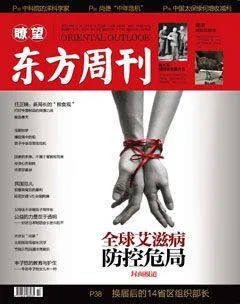豐子愷的教育與護生(上)
“剛剛出門散步,在郵局遇到一位先生,他說認識我,家里還收藏有我爸爸的畫呢!”
豐一吟,84歲,是豐子愷的七個子女中唯一的健在者。2012年3月的一個上午,《望東方周刊》記者如約到她上海的家中采訪。她進門說她上午的經歷。
房間里掛著豐子愷生前畫作。書桌上有攤開的宣紙,是豐一吟臨摹了一半的豐子愷書法作品。
一般到她這個年齡的人,稱呼自己過世的父母,都會稱“父親或母親”,但,豐一吟談到豐子愷,仍然呼“爸爸”,親切地宛如老先生還在眼前。
不玩怎么行
在豐一吟印象中,豐子愷從來沒對她的兄弟姐妹幾個說過“你必須怎么樣,不可以怎么樣”。
即使在戰亂年代,豐子愷仍然對兒女身心照顧有加。豐一吟回憶,上世紀40年代,日軍進犯中國,豐子愷全家逃難到貴州遵義的時候,每個禮拜六晚上,豐子愷會花上5塊錢,買一些吃的回來。然后,他一邊教古詩詞,孩子們一邊吃東西,接下來還會講故事給大家聽,講的時候不許做記錄,之后再讓孩子們寫出來。
采訪中,談到有趣處,豐一吟常常開懷大笑,在她現在的笑聲中,似乎仍然能感受到來自兒時的自在與舒展。
對于現在的教育,豐一吟很感嘆,“拼命地壓著孩子們學習,壓得很苦”。而在小時候,“爸爸”很支持他們“玩兒”,“小孩子當然要玩了,不玩怎么行?!”豐一吟說。
豐子愷有一幅畫作《小大人》,源于豐子愷看到的情景:六七歲的男孩子被父母親穿上小長袍和小馬褂,戴上小銅盆帽,教他學父親走路;六七歲的女孩子被父母親帶到理發店去燙頭發,在臉上敷脂粉,嘴上涂口紅,教她學母親交際。豐子愷感慨道,“想象那兩個孩子的模樣,覺得可怕,這簡直是畸形發育的怪人!”
“在精神生活上都以成人思想為標準,以成人觀感為本位,因此兒童在成人的家庭里精神生活很苦痛。”豐子愷在他的文章中寫道。
豐子愷精通文學、音樂、美術以及多種外語,多才多藝,堪稱一代大師,但是他的七個子女都沒有從事藝術工作,豐一吟說,“爸爸從來不硬要我們學什么”。她和其他兄弟姊妹分別在中文、數學等領域各有自己的一番事業。
豐一吟則先后從事俄文圖書翻譯和豐子愷研究工作,此外,她酷愛京劇。她興致勃勃地說,前幾日,朋友陪著她去植物園,碰到票友,她還即興唱了一段老生行當《甘露寺》。
設身處地
近幾年,一套1932年版《開明國語課本》被發現,重印,熱賣,甚至賣斷市了。這套老課本系列在網上收獲好評一片,同時引起教育部的重視。這套教材,正是民國時期開明書局為小學生編寫的語文教材,葉圣陶編纂、豐子愷繪畫,在1949年前就印過四十余版次。
豐子愷青年時賣掉祖宅,赴日本東京學習美術,偶見日本著名畫家竹久夢二的作品,因愛其簡煉,醒世勸誡,遂引為榜樣。回到浙江,任教于上虞春暉中學的豐子愷,作了一幅畫《一鉤新月天如水》,被鄭振鐸看到,頗為贊賞。慢慢地等豐子愷畫稿成集,鄭振鐸為其命名為《子愷漫畫》,至此,中國才有“漫畫”一詞。豐子愷是中國漫畫的開創者,他清新洗練的中國漫畫風格,至今仍是標桿。
現在,開明國語課本已經出現了盜版,甚至還有兩個出版社為了爭奪再版版權打官司,豐一吟告訴本刊記者說,“(打官司的兩家出版社)一家在上海,一家在北京,我說,你們一南一北,互不影響,自己出自己的。”
在豐一吟書架上,擺放著多套不同版本的開明國語課本。翻開課本,課文內容就像豐子愷的漫畫一樣,內容簡明,意蘊卻深刻。
比如,18課,篇名《職業》,“貓捕鼠,犬守門,各司其事,人無職業,不如貓犬。”
每篇課文,都有一幅很大的漫畫,文字只有十幾個字,如:
《濟貧》,女出門,見貧婦,衣服不完,入門告母,母取舊衣贈之。
《愛同類》,一犬傷足,臥于地上,一犬見之,守其旁,不去。
《合群》,群鳥筑巢,或銜樹枝,或銜泥草,一日而巢成。
豐一吟說,豐子愷對他們的教育,就像課本的風格一樣,能設身處地體驗孩子們的生活。豐子愷的漫畫往往能從兒童的視角來觀察世界。他曾經作過這樣的一幅畫:房間里有異常高大的桌子、椅子和床鋪。一個成人正在想爬上椅子去坐,但椅子的座位比他的胸膊更高,他努力攀躋,顯然不容易爬上椅子;如果他要爬到床上去睡,也顯然不容易爬上,因為床同椅子一樣高;如果他想拿桌上的茶杯來喝茶,也顯然不可能,因為桌子面同他的頭差不多高,茶杯放在桌子中央,而且比他的手大得多。這幅畫的題目叫做《設身處地做了兒童》。豐子愷畫后感想:“我看見成人們大都認為兒童是準備做成人的,就一心希望他們變為成人,而忽視了他們這準備期的生活。因此家具器雜都以成人的身體尺寸為標準,以成人的生活便利為目的,因此兒童在成人的家庭里日常生活很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