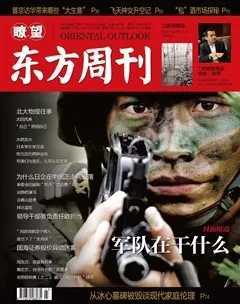寂靜的演習

在前往確山之前,石家莊陸軍指揮學院院長石忠武少將就提醒說,這將是一場寂靜的演習。
沒有鉗形攻勢,沒有坦克集團沖鋒,也沒有“層層扒皮”的進攻、節節防御的堅守,“就像典型的現代戰爭,在寂靜中交鋒。”作為“聯教—2012·確山”演習總導演,石忠武這樣向《瞭望東方周刊》解釋。
6月上旬,來自全軍19所軍事院校的500多名學員,確切地說是500多名以營團級為主的現役軍官,在河南確山合同戰術訓練基地上演聯合實兵演練。陸、海、空、二炮等主要軍兵種以及裝備、后勤、政工等系統的學員,將組成聯合戰術兵團指揮部,對陣由機步旅扮演的藍軍。
在解放軍歷史上,以軍事院校為平臺,進行這樣軍兵種齊備的“全要素”聯合演練,尚屬首次。
除了為“聯教聯訓”這一軍隊重要的教育訓練改革提供試點經驗,這次確山演兵,對于一般公眾而言,更值得關注的是解放軍在信息化進程中謀求新突破的努力。
信息化已成為最近20年來世界軍事領域的“終極殺招”,可它如同戰爭本身,仍然迷霧重重。比如一個根本問題:信息化軍隊到底是什么樣子?是飛得更快的J系列戰機,還是裝備到單兵的便攜野戰終端,又或是能力更強的偵查衛星?
今日軍演,對于一支信息化條件下的軍隊而言,戰斗力的觀察要點,并不在于用多大口徑的自行火炮轟擊,而是戰場信息和指揮官的命令能否迅捷、無聲、無衰減地上下傳遞。
即使在實彈演練部分,集團沖鋒也不再是演習的主角。信息化戰爭中,兩個軍事集團之間的對決,很可能只是數十分鐘的接觸。
無須地毯式轟炸,只用精確投放武器一招制敵。當人們在靜謐的清晨醒來,卻發現戰局已定,勝負已分- - -這就是信息化條件下“寂靜的戰爭”。
技術的變化決定戰術的變化,軍事訓練也在發生根本性變化。
“經過30多年的不懈努力,我軍信息化建設已經取得重大歷史性成就。”石忠武說,積30年國力成長,今天解放軍的信息化已有相當基礎。指揮信息平臺更新換代,“目標中心戰”這樣的新戰法被提出并付諸訓練,信息主導、體系對抗、要素集成、聯合制勝的觀念開始生根。
“我不關心實兵對抗的輸贏,我關心的是指揮員們的聯合意識和運用戰術思想的能力。”石忠武說。
正在進行時的新軍事變革,需要更多嘗試與突破。
指揮員站上信息高地
從外形上看,被偽裝網遮蔽的指揮所,像一座座巨大的迷彩外星戰艦,降落在確山訓練基地東山的高地上。
為了聯通這些指揮機構并進行保障,使用了1萬多米線纜以及衛星設備。巨量的傳輸需求,源自本次演習使用的指揮信息系統。這套曾獲得國家科學技術特等獎的系統是軍隊的最高秘密之一。在演練準備會上,石忠武強調,它比人的生命還重要。
這是改進后的指揮信息系統第一次大規模的全要素應用:讓陸海空、二炮乃至政工、后勤、裝備的指揮員看到共同的偵察報告和作戰態勢。
這是軍隊信息化歷程的一大步。
拿破侖和他的敵人也許是最后一批能夠親身俯視整個戰場的高級指揮員。之后,隨著戰場的擴展,戰斗地點旁的山坡,已經無法讓指揮員看到自己的每一支部隊。而且,軍官與自己部隊的物理距離也越拉越遠。
所以有這樣一種說法:一條命令可以讓一個人成為團長,但只有通信才能讓他成為指揮官。
指揮信息系統,讓一名聯合作戰指揮員站上信息高地,他們能夠像200年前的先輩那樣,看到自己的所有部隊,并直接下達命令。
信息改變了指揮方式。由于能夠更加直接地觀察戰場,并獲得經過精確計算的戰場信息,用于傳統作業的參謀人員將迅步減少,“指揮員定下決心的時候,效率將大大提高。”石忠武說。
與傳統的陸軍司令部相比,聯合戰術兵團的指揮部顯得過分安靜:沒有參謀們扎堆討論的喧嚷,也沒有報告部隊位置的呼叫。
聯合戰術兵團司令員在電腦前輕點鼠標,偶爾和對面同樣埋頭電腦的參謀長對話幾句,然后一個人面對戰場態勢默然思考。
不過,也許第一次面對“全要素”這樣復雜的抉擇,也有指揮員在顯示器前猶豫許久,最后站起來慢慢踱步,輕聲說:“該多弄幾個參謀……”
“像這樣的指揮演習,主要觀察指揮員們運用指揮信息系統的情況。”石忠武說,雖然也有作戰部隊配合,但作為一次以中級指揮員為主的演習,東山高地上“外星戰艦”里的作業才是取勝之道。
傳統依然會留下痕跡- - -當知道演習總導演要來視察,正在電腦上繪圖作業的中校從拎包中翻出一張地圖鋪開來。
信息化無疑改變了訓練方式。比如,指揮信息系統可以控制演習進程,每個系統都顯示兩個時間:一個是天文時間,一個是演習時間。前者指實際時間,后者可調,一些關系不大的演習階段可以“快進”。

總有一些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信息化對于訓練最大的改變,就是為聯合作戰和聯合訓練提供更寬廣的平臺。反過來,不能實現充分聯合,信息化只是炫技式的獨舞。
每艘“戰艦”中都包含一個指揮決策中心,居于指揮部正中;兩邊若干耳房,海、空、二炮、陸航等軍兵種小組分列其中,政工、保障等指揮小組也是指揮部的重要元素。“這次演習的指揮部編成完全是面對聯合指揮的。”石家莊陸軍指揮學院科研部副部長楊曉東告訴本刊記者,與過去相比最大的不同是,海空軍及其他軍種指揮員在指揮部中擁有席位,直接指揮本軍兵種部隊。“過去的聯合大多是陸軍以外的軍兵種在聯合指揮部設立聯絡員,合成指揮員下達作戰命令,由聯絡人員向本兵種司令部傳達,再擬定作戰計劃并執行。”
不過,軍官們似乎還不太適應這種融合。
演習副總指揮、空軍指揮學院副院長李勇少將對《瞭望東方周刊》說,演習讓空軍深刻了解了陸軍的地面行動是如何策劃實施的,也讓其他軍兵種了解空軍。不過從開始階段看,其他軍兵種對空軍的認識可能還不很到位。
比如,指揮部給空軍劃定了7平方公里的打擊范圍,“根本施展不開,而且在退回的過程中還和陸航重疊。”相比之下,卻給二炮劃定了30多平方公里的打擊范圍,“它沒法打移動目標,范圍太大了。”
用術語講,就是軍種運用不到位,“總有一些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比如二炮部隊連續打擊,空軍戰機呼之即來,甚至不考慮起飛抵達轟炸目標的時間。
陸軍指揮員還是更了解陸航,“其實這次配置的陸航兵力并不多,而且載彈量小。如果利用空軍適當,完全可以打掉藍軍一般的重裝戰斗力。”李勇說。
比較普遍的情況是,指揮員們介紹自己的計劃時,還較少涉及其他軍兵種。例如,很少有人提到,如果自己的火力打擊沒有達到預期效果,建議其他哪個軍兵種繼續打擊。看起來還是“各打各的”。
軍種聯隊打贏“大陸軍”
據李勇介紹,聯合作戰本來屬于高級指揮員的培養內容,營團一級的中級指揮員掌握合同作戰的能力即可。
聯合作戰一般是指海陸空二炮等不同軍種之間的聯合,合同作戰則主要是軍種內部的協同,有的也有其他軍種的支援配合。
這也是首次在中級指揮員的培養過程中,進行大規模、全要素的聯合戰斗演練。“中級指揮員雖然目前不是聯合作戰指揮的主角,但需要先培養他們的聯合作戰意識、知識和技能。”李勇說。
其實,對于軍隊自身而言,這次演習的核心是實現“聯教聯訓”試點。具體講,就是如何實現不同軍兵種院校以及部隊、科研機構之間的聯合理論研究、聯合教學訓練,并嘗試建立相關制度。為解決這些問題,從2012年春季起,已經召開了三次理論研討會。
總參謀部在《2012年軍事訓練指示》中,明確由石家莊陸軍指揮學院牽頭試點,使其具有總部一級的意義。此次演習,即為試點中的一個重要環節。
縱向看,聯教聯訓希望以“嵌入”的方式,強化軍事院校與部隊的聯系;橫向看,它在成長階段就培養部隊指揮員的聯合作戰意識和能力。
為了從多角度促成聯合意識,演習間歇的籃球比賽并不是按照單位組隊,而是按“軍種聯隊”、“兵種聯隊”、“系統聯隊”等組成。在第一場預賽中,海、空、二炮指揮員組成的“軍種聯隊”反敗為勝,打敗炮兵、裝甲兵、工程兵、防化兵指揮員組成的“兵種聯隊”。
“我們的聯合程度還有待加強。”楊曉東說,這次演習主要針對團一級干部,以下級別的大規模聯合學習訓練還未提上日程。他覺得,這種聯合本應該像一張天然生長的優質牛皮,而在目前體制下,將如此多的單位“縫”在一起,已經是極有難度的嘗試。
試點一旦形成經驗,再由總部以制度的形式固化下來,則將是軍隊教育訓練的一大進步。
“看不見人”的演習
總指揮口中“寂靜的演習”,在其他角度也被印證。
確山合同戰術訓練基地司令員許民說,現在演習展開,一般看不到人,坦克打完炮也躲在隱蔽處。那種坦克掩護步兵沖鋒的經典場景,幾乎不會出現。
“演習現場不如以前熱鬧,但效能高了。”炮兵出身的許民說,以前炮兵打擊一片火海,現在都是精確打擊,一擊完成。
此次扮演藍軍的機步旅旅長萬麗華說,現代戰爭,只要火力能實現精確打擊,就盡量不用人力,場面“肯定不那么火爆”。
此次雖然是軍事院校最大規模的全要素聯合演習,但實彈部分顯然不如人們想象那樣壯觀。短暫的營級進攻,除了坦克和裝甲車,只能看見戰士執行單兵爆破路障任務。直到占領“敵”陣地,才有持槍的步兵出現在視野中。
一度,開進的坦克在射擊后退到隱蔽處,于是整個實彈演習場看不到任何兵器和人員。
幾公里外炮群齊射,也不是過去那樣把整個山頭都炸得一塌糊涂,而是覆蓋十幾個平方米的連續射擊就擊中靶子。短暫射擊后,連火炮也沉默了。
石忠武說,機械化戰爭時期,作戰一般采取整師、整旅、整團建制運用兵力。而在信息化條件下,體系作戰成為主要特征,各種力量按照作戰任務編組,以單元、要素的形式進入體系發揮作用。
這就是體系作戰,目前軍隊建設中的一個熱點詞匯。《解放軍報》說,它是“胡主席關于加強基于信息系統的體系作戰能力建設的重要戰略思想”。
缺乏防護、火力較弱的步兵,在體系中似乎難成主角,數百人沖鋒的鏡頭也將成為歷史。
2012年初,美國海軍陸戰隊司令曾表示,未來美海軍陸戰隊將全面轉變成一支特種作戰部隊。換句話說,他們再也不會執行硫磺島戰役那樣的人海戰術。
占領也許不再需要步兵,用遠程火力對一條公路進行控制,也可以阻擋敵人通過。
這種武器發展帶來的改變是劃時代的。“比如,它打破了通常的戰略、戰役、戰術的界線。”楊曉東舉例:美軍對拉登的突襲無疑具有戰略價值,但是只動用了不到一個連的兵力。在過去的時代,它連執行一個戰術任務都很難滿足,“已經很難回答這究竟是戰略還是戰術任務。”
“這次演習,我們希望充分體現信息化條件下作戰的新思想、新戰法。”石忠武說,現代戰爭中的戰線已經越來越模糊,這讓對戰雙方必須有新的作戰理論
作為一種嘗試,紅軍將盡力采用名為“目標中心戰”的新戰法。它是濟南戰區近年來提出的信息化條件下的作戰理論,即以目標為中心組織的作戰。
通俗講,就是不再用主攻部隊層層推進、突破,而是集中力量打擊支撐敵人體系的關鍵節點。而這種打擊往往要依靠先進兵器跨越戰線,直達敵后。
“在信息化條件下,主攻方向已不再是傳統的由前至后的地理指向,確定主攻方向也不再是指揮決策的核心和關鍵。確定重點打擊目標成為了定下決心的核心內容。”某集團軍副軍長楊劍少將向《瞭望東方周刊》解釋說,確定重點打擊目標需要先做評估,在各個評估系統中重疊次數多者最為重要。而且,打擊對象不宜過多。
紅軍聯合戰術兵團指揮部將藍軍旅指揮部設定為首要目標。
步兵在目標中心戰中的特點也是多樣化和特戰化。這似乎是信息時代步兵唯一的出路。李勇說,引導空軍攻擊目標是最主要的任務之一。
一個特種作戰師在作戰時不會用營團去攻擊敵人,而是派出幾十、上百個特戰小組。
用18世紀法國元帥莫里斯·德·薩克斯的話說:“并非數量龐大的軍隊,而是更優秀的軍隊,才能贏得戰爭。”

訓練決定命運
雖然1991年的“沙漠風暴”以其高技術特性而令人震驚,但在美軍看來,2003年的第二次伊拉克戰爭更具備信息戰的特征。換句話說,如果后者是信息化軍事時代的黎明,前者不過是凌晨一兩點鐘。
而這期間經歷的12年,美軍仍在全球各地參與實戰,最終成就了“網絡中心戰”這一目前最為成熟的信息戰模式。
面向新形勢,解放軍的應對之道,叫做集成訓練。就好像計算機的集成電路,把各自獨立的模塊插在主板上,從而產生強大的整體能力,而新功能是各部件簡單疊加所無法形成的。
“從2004年全軍一體化訓練試點開始,就提出了作戰要素、作戰單元、作戰體系集成訓練的概念。之后逐漸被全軍引用。”石忠武說,經過近10年的研究和探索,全軍對集成訓練概念及其內涵有了基本認識。
他說,集成訓練的根本目的是形成體系作戰能力。
體系作戰對中國軍隊的建設提出了更高要求。但是像任何一種戰略理論一樣,它在戰術層面的落實,“戰場最后一公里”的實踐是其能否實施的主要挑戰。這也是美軍“網絡中心戰”在十幾年中反復實驗總結的核心問題。
集成分為不同層次:由要素、單元集成,一直到最高層次的體系集成。這次演習,在一定意義上講就是一次體系集成的嘗試。
石忠武認為,集成訓練的挑戰首先在于理念,“裝備更新了,理念還是傳統模式,不能叫改變。”而后,就是訓練的方式方法和訓練內容,“很多改變還需要時間”。
“必須有很好的信息平臺,但再好的平臺也需要理念牽引。”李勇總結說。
“以后也許不需要搞這么大規模,但是這種形式是可以推廣的。”石忠武認為,未來幾個院校、部隊、科研機構之間的合作會成為常態。
一個悖論是,將軍隊和芯片捆綁,它雖然會像芯片一樣即時迅捷,但也會像芯片一樣脆弱。此次演習,一個重要的自創“裝備”就是木制墊板,防止電腦主機直接接觸地面,潮濕短路。
而如果遭遇更快的芯片,我們又該如何應對?
這些問題,需要一次新長征來給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