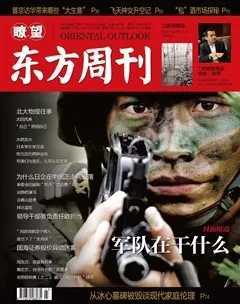審委會回避制“風(fēng)聲”之后看“雨點”
對于各地法院正陸續(xù)推行的審委會委員回避制,北京大禹律師事務(wù)所主任張燕生連用了兩個“非常必要”。
“我曾代理的福建念斌投毒案,歷時5年共7次審判,其中4次判處死刑立即執(zhí)行。第四次發(fā)回福州中院重審時,被告人要求所有的審委會委員回避。”張燕生對《瞭望東方周刊》說,被告人當(dāng)時認為雖然每次發(fā)回重審時合議庭成員都變了,但案件最后都是上審委會討論決定,審委會還是原班人馬。
“對于該被告人的申請,法官當(dāng)時未予支持。”張燕生說,福州中院第四次也是判處念斌死刑。
審委會作為新中國成立之初為保證案件審理質(zhì)量而設(shè)的審判組織,雖然不在判決書上出現(xiàn),但因案件被認定為“重大、疑難”的標(biāo)準(zhǔn)彈性很大,事實上幾乎所有社會影響較大、異地審判和性質(zhì)敏感案件的最終裁判都出自審委會。曾引發(fā)社會關(guān)注的劉涌、杜培武、聶樹斌等案件的終審判決均是如此。
近年來,法學(xué)界和律師界的一些人也不斷呼吁改革審委會,詬病焦點是其僅聽承辦人匯報就作裁判的做法。
“審委會委員回避制有益于司法公正,要肯定,但實踐時怎么操作,有沒有機制保障,肯定會影響改革的效果。”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法學(xué)研究所訴訟法室主任熊秋紅對《瞭望東方周刊》說,“未來發(fā)展方向肯定是要不斷地弱化和限制審委會職權(quán),將審判權(quán)交給合議庭,使庭審更加實質(zhì)化。”
吃螃蟹者
2012年5月,廣東省高院發(fā)布《關(guān)于完善審判委員會工作機制的實施辦法》。《辦法》規(guī)定:審判委員會全體委員的姓名以及履行職務(wù)有關(guān)的信息,應(yīng)當(dāng)通過廣東法院網(wǎng)或其他方式對外公開,案件提交審判委員會討論之前,合議庭應(yīng)當(dāng)書面向當(dāng)事人公開審判委員會名單,并告知當(dāng)事人有權(quán)申請回避。
“今年我們將在全省范圍內(nèi)推行審委會委員回避制度。”廣東高院審判管理辦公室負責(zé)人公開表示,下一步還將“建立審判指導(dǎo)意見的備案審查制度”、“以適當(dāng)方式公布審判指導(dǎo)意見”。
試水審委會回避制度,廣東并不是全國“第一個吃螃蟹”的。2011年3月22日,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舉行《關(guān)于深化落實司法公開制度實施意見》新聞發(fā)布會,宣布將在全國率先推行當(dāng)事人申請審委會委員回避制度,于當(dāng)年4月1日后開始實行。
上海二中院副院長徐松青當(dāng)時公開表示,“這是我們致力于‘看得見的公正’的一項具體措施”。最高人民法院司改辦副主任、應(yīng)用法學(xué)研究所副所長蔣惠嶺當(dāng)時也表態(tài)說,上海二中院的做法具有在全國范圍內(nèi)推廣的價值。
隨后多地法院不斷試水審委會委員回避制。2011年5月5日,寧波江北區(qū)法院開始試行該制度;2011年10月20日,北海中院制定《告知審判委員會委員名單及申請回避權(quán)利通知書(樣式)》。
盡管已經(jīng)有了制度,而在上述地區(qū),公開的申請回避案例還不多見。
2011年10月13日,浙江之星律師事務(wù)所律師袁裕來在代理一起起訴寧波某地城管局執(zhí)法行為違法的行政案件中,寧波江北區(qū)法院向當(dāng)事人和代理律師發(fā)出“申請審判委員會委員回避權(quán)利告知書”,說該案要提請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告知書附上了參與討論案件的委員名單。
“這是我第一次被通知可以申請審委會回避。”袁裕來對《瞭望東方周刊》說,隨后他申請江北區(qū)法院全體審委會委員回避,“理由是如果審委會‘判而不審’,它就無法對雙方當(dāng)事人爭議的事實和法律問題,根據(jù)當(dāng)事人提供的證據(jù)、依據(jù)以及各自發(fā)表的意見,作出準(zhǔn)確判斷。”
袁裕來在業(yè)界享有“行政訴訟第一人”之稱。“一般稍尖銳點的,比如涉及拆遷等的行政訴訟案件,都會上審委會討論,這類案子常牽涉地方政府,我們因此對審委會缺乏充分的信任基礎(chǔ)。”袁裕來說。
他的申請沒有得到法院準(zhǔn)許。
在北海,2011年12月7日,案件當(dāng)事人伍某和張某向北海中院遞交申請書,申請審委會3名委員回避,認為其中兩名委員曾作為原審合議庭成員參與此案審理,而另一名委員曾作為審委會委員參與過審理涉及申請人的多宗案件,均與案件有利害關(guān)系。
經(jīng)過審查,北海中院院長作出決定并告知申請人,同意請求對其中兩名委員不參加該案審委會討論的回避申請。
截至2012年4月11日,北海中院已向案件當(dāng)事人發(fā)放《告知審判委員會委員名單及申請回避權(quán)利通知書》上千份,已有兩個案件的3名當(dāng)事人申請該院4名審委會委員回避,已依法決定其中2名委員回避。

“利害關(guān)系”應(yīng)有更明確規(guī)定
就回避制度的具體操作,張燕生認為“法官回避的制度規(guī)定應(yīng)更明確些。”
張燕生說,《法官法》第六章十六條、十七條以及2000年1月30日最高法發(fā)布的《關(guān)于審判人員嚴格執(zhí)行回避制度的若干規(guī)定》、2011年2月10日發(fā)布的《關(guān)于對配偶子女從事律師職業(yè)的法院領(lǐng)導(dǎo)干部和審判執(zhí)行崗位法官實行任職回避的規(guī)定(試行)》等是目前關(guān)于法官回避制度的依據(jù)。
此外,《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中對審判人員自行回避和當(dāng)事人有權(quán)申請審判人員回避均有原則性規(guī)定,最高法院先后制定并公布了執(zhí)行三大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而在1998年最高院《關(guān)于執(zhí)行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中,首次在回避主體上將審判委員會委員納入其中。
“在中國審判組織中,獨任庭是由職業(yè)法官一人組成的審判組織,對簡單案件進行審判;合議庭則是根據(jù)合議制原則建立的審判組織,負責(zé)絕大多數(shù)案件的審判工作。”熊秋紅說,審委會盡管不直接主持或參加法庭審判,也實際承擔(dān)著審判職能,“將回避制度延伸至審委會,符合一個簡單邏輯,只要判案中涉及利害關(guān)系就應(yīng)該回避。”
“現(xiàn)實中,對審委會回避還用得不太多,很多人沒有想到這項權(quán)利,因為一直沒有清晰明確的法律根據(jù),其實有需求的當(dāng)事方是不少的。”張燕生說。
目前一些地方對審委會委員回避已經(jīng)有了相對詳細的規(guī)定,如廣東高院規(guī)定:審委會委員是案件的當(dāng)事人或者與當(dāng)事人有直系血親、三代以內(nèi)旁系血親及姻親關(guān)系,本人或者其近親屬與案件有利害關(guān)系,與案件的訴訟代理人、辯護人有夫妻、父母、子女或者同胞兄弟姐妹關(guān)系,及與案件當(dāng)事人之間存在有其他利害關(guān)系,可能影響案件公正處理等五種情形之一的,審委會委員應(yīng)當(dāng)自行回避,當(dāng)事人也可以申請回避。
張燕生曾接手一個案子,“院長跟受害人之間有非常輕微的關(guān)系,受害人家屬曾經(jīng)在院長家里當(dāng)過保姆,無論這最后是否成為一個回避理由,申請院長回避是可以提的。”
“今年5月有個案子,我申請了法官回避,理由是法官和被告律師曾合作出版過一本書,兩者之間就可能存在出版費、稿費等關(guān)系,法院同意了我們的申請。”袁裕來說。
法官眼中的回避制
“審委會回避制度是一個好的開端,”張燕生說,“審判委員會有十幾個成員,對其中個別委員申請回避成功,不能說一點效果沒有,但不見得能對案件的最后結(jié)果起決定性作用。”
目前北京尚未推行審委會回避制,“我還沒有遇到過當(dāng)事人提出要審委會回避的例子,一般是當(dāng)事人提出法官回避,原因是態(tài)度不好之類,當(dāng)事人一般說不出什么真正的理由來,因為老百姓很難了解有關(guān)人員之間的關(guān)系。”北京市某法院刑事審判一庭法官陳華(化名)對《瞭望東方周刊》說。
“對審委會回避,以北京來說,不少當(dāng)事人不知道是誰組成審委會,審委會委員的回避只能是主動回避,如果他不提出來,別人也不知道。他說沒關(guān)系,別人無從查證。”陳華說。
在陳華看來,像廣東等地將審判委員會全體委員的姓名及履行職務(wù)的信息對外公開,可能會起到一定作用,“但對于他們跟案件之間的利害關(guān)系的掌握卻是另外一回事,若審委會委員的社會關(guān)系十分復(fù)雜,這些社會關(guān)系人從事法院以外的工作,社會脈絡(luò)比較多,別人就很難知曉。”
在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的官方網(wǎng)站上,靠近左側(cè)一欄設(shè)置有“審判委員會委員”名單,共16位,排在第一個的是王信芳,打開鏈接后看到關(guān)于他的信息介紹為“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院長、審判委員會委員、一級高級法官”,并配有照片。
審委會委員往往首先就是院長,但陳華認為,“若實行審委會回避制,最應(yīng)回避的可能就是院長,因為院長一表態(tài),其他委員隨聲附和的可能性較大。”
北京某法院專管刑事案件審理的李姓法官認為,審委會回避制在實際中會遇到執(zhí)行障礙,“上審委會討論的案子,一般提前半個月告知當(dāng)事人,如果有申請回避環(huán)節(jié)的話,當(dāng)時也應(yīng)告訴當(dāng)事人哪些人會參加討論。但真到討論那天,本來10個人參加的,可能只來了8個。”
李法官對《瞭望東方周刊》說,因為審委會委員大部分是院長、副院長或各庭長,都有行政職務(wù)上的工作,“被申請回避的委員當(dāng)天開會就沒參加,臨時又改了幾位委員參加,那是否要再告知當(dāng)事人呢?此外,審委會討論,當(dāng)事人是不在場的,回避沒回避,當(dāng)事人怎么能確認呢?”
“我認為這項制度的推行,關(guān)鍵在于實際效果。”上述李姓法官說,比如申請了院長回避,“其他委員是副院長和庭長,如果院長打了招呼,雖說他本人回避了,但有沒有解決問題呢?”
審委會有把握政策的特殊功能
陳華從上世紀80年代起一直擔(dān)任刑事法官,“審委會還沒有發(fā)生實質(zhì)變化。”陳華說,他感覺對于審委會改革的“風(fēng)聲還不夠大,雨點也不夠大”。
作為人民法院審判組織改革的重要內(nèi)容,審委會改革曾在人民法院1999年發(fā)布的《“一五”改革綱要》、2005年發(fā)布的《“二五”改革綱要》中被重點提及。
《“二五”改革綱要》提出,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設(shè)刑事專業(yè)委員會和民事行政專業(yè)委員會;高級人民法院、中級人民法院根據(jù)需要在審判委員會中設(shè)刑事專業(yè)委員會和民事行政專業(yè)委員會;要求高水平的資深法官能夠進入審判委員會,審判委員會由會議制逐步改為審理制。
“專業(yè)委員會的設(shè)計很好,比如知識產(chǎn)權(quán)的案子,刑事庭庭長不太懂,有專業(yè)委員會就好辦了。”陳華說,但他本人所在的法院在這方面一直沒有什么變化。
2007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印發(fā)《關(guān)于改革和完善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制度的實施意見》,對審判委員會的性質(zhì)、專職委員、審判專業(yè)委員會、討論案件的程序、表決等內(nèi)容,提出了指導(dǎo)性意見。
對此,媒體當(dāng)時普遍認為最高法院旨在為審委會一直備受詬病的“高度行政化”開出藥方。當(dāng)年,各地法院審委會也紛紛設(shè)立專職委員,而實際運行還不理想。由于專職委員比原有職務(wù)高半個行政級別,該位置成為一些法院安置一些快到退休年齡的法院領(lǐng)導(dǎo)的特殊通道。
2008年,中央新一輪深化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改革部署了完善審判委員會討論案件的范圍和程序、落實并完善檢察長列席審判委員會、規(guī)范審判委員會職責(zé)和管理工作等三項改革任務(wù)。
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制度改革課題組成立,研究審判委員會的現(xiàn)狀及存在的問題。
2010年,《關(guān)于改革和完善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制度的實施意見》重新制定并發(fā)布。
“審委會改革還沒有真正落到實處的一個很重要原因是,審委會有一個很大的功能是要掌握、把握各種政策。”張燕生曾在北京市中級法院刑一庭當(dāng)過15年法官,1994年離開法院在刑事訴訟領(lǐng)域做律師,“比如這段政策上要求嚴打,主審法官認為不用給重刑,但審判委員會在考慮當(dāng)前政策情況下進行適當(dāng)糾正。”
“又比如,這段時間醉駕或非法集資等社會影響比較大,這類案子即使比較明確也會上審委會討論。對審委會改革必須考慮到它的這一功能。”上述李姓法官說,“自上而下的審委會改革尚有漫漫長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