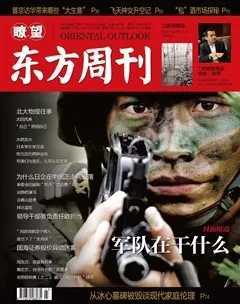崔琦這棵“萌”大樹

杜瑞瑞師承崔琦。1990年,杜瑞瑞成為崔琦的博士后,跟隨崔琦做了4年研究。
在量子輸運這一研究領域,作為全世界的領先者,美國學界近幾十年來是單脈相傳。這一脈,便是崔琦、斯托爾默及其弟子們。崔琦就像一支主干,支撐起量子輸運研究這棵大樹。在這棵大樹上,有不少中國學生成為枝干。
1998年,瑞典皇家科學院授予霍斯特·斯托爾默、崔琦和羅伯特·勞克林當年諾貝爾物理學獎,表彰他們對在強磁場和超低溫實驗條件下的電子進行的研究,其學術名稱為“分數量子霍爾效應”。
時至今日,這項研究對于大眾仍顯得高深莫測。按照常識,宇宙中的自由基本粒子所帶的電荷皆為一個電子所帶的電荷的整數倍,而崔琦及其合作伙伴的研究顯示,在特定條件下,電荷可分裂——他們發現了帶有1/3電荷的準粒子。這項研究至今仍然是凝聚態物理領域最重要的成就之一。
杜瑞瑞告訴《瞭望東方周刊》:“因為這些研究我們才發現,原來書本上已知的理論不能解釋這些現象。我們不但要考慮單個電子的運動,還要考慮所有電子的運動。”
從理論上講,崔琦的研究將可應用于研制功能更強大的計算機和更先進的通信設備。然而目前上述發現尚未得到實際應用。曾有記者就此發問,崔琦說:“我還沒有資格去提如何應用這個新效應。但它是客觀存在的,量子物理的電子有其新的特性。”
從另一個角度看,崔琦等的發現已經有了實際作用,那就是沖擊了人們的世界觀。杜瑞瑞說,從教育的角度來說,以前的教科書是不完整的。隨著崔琦等的研究發現,現在教科書都在做這方面的修改。
事實上,崔琦在獲得諾獎之前已經是上述研究領域內的領軍人物。
早在1985年,德國物理學家克勞斯·馮·克利欽由于在1980年提出和發現了整數量子霍爾效應而獲得了當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分數HDItPixc7z8ZVwIXAb+YvFjtvetGYIqZW6eNWW5S6NA=量子霍爾效應比整數量子霍爾效應更深刻,所以1998年崔琦獲獎一點不讓人覺得意外。”杜瑞瑞說。
一篇廣為傳播的報道描述了崔琦得知獲獎后的反應:1998年10月13日清晨,崔琦像往常一樣來到學校,當大家向他表示祝賀時,他像平常那樣微微一笑,只說了句“謝謝”就離開了。
“崔琦是非常有平常心的人,他并沒有因為獲得諾貝爾獎而改變。”杜瑞瑞說,崔琦和朋友在一起時頗健談,常講笑話。但他并不喜歡成為公眾人物,除了討論專業問題的時候。
在北大發表講座的開場白時,崔琦甚至略顯羞澀。當場有學生發微博稱:崔琦好萌。
在提問環節,當記者提出“為什么華人諾貝爾自然科學獎獲得者基本都集中在物理學領域,而且又多與量子物理有關,這是否和中國物理學的人才梯隊建設有關時”,崔琦先是笑了笑,然后緩了緩說,“我覺得這個問題沒有統計意義,不要回答了吧”。
隨后,當面對專業學術問題時,他展現了不同的神采。相比此前的開場白,雖然要用到更多專業詞匯,但他的中文卻變得輕松流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