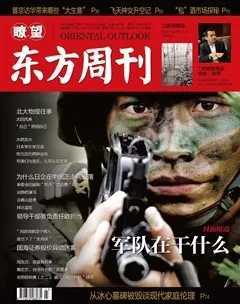日本學生學漢語
自從1868年明治維新以來,日本的高等學府主要從歐美國家吸取先進知識。因為最初來日本的專家學者里有德國人,也有法國人,所以直到今天,日本醫生用的術語中,有不少是源自德文的,例如,karte(病歷)、gaze(紗布)、kranke(患者)等等;藝術方面的術語,則有不少是源自法文的,例如,atelier(工作室)、ensemble(合奏)、avantgarde(前衛藝術)、crayon(蠟筆)等等。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經過了民主化學制改革的日本大學,還保持了所有學生得念兩種外語的規定。
具體而言,大家都學英語以外,也要念德語或者法語。當年,專修醫藥理工學的學生大多選擇了德語;專修文學法律的學生則一般選擇法語。在各大學提供的第二外語課程中,亞洲語言出現則是相對晚近的事。
1972年中日建交后,開辦漢語課程成為一種潮流,接著部分大學也開設了韓語課程。另外,也有少數大學開俄語、西班牙語、意大利語等課。
總的來說,“念過第二外語”曾很長時間是大學生的標志。畢竟,多一門外語,就多一些關于世界的知識。而中學文化程度的人始終只有學英語的機會。
類似的情形延續到了上世紀90年代初。那個時候,柏林墻倒塌、蘇聯解體、冷戰結束,世界出現了以美國為唯一中心的新局面。同時,通訊技術的發達導致金融經濟的全球化,英語很快就獲得了世界語言的地位。
為了應對國際情勢之變,日本進行教育制度改革,其中一項就是加強大學本科的專業以及英語教育。結果,一所又一所大學取消了第二外語課程,或者把英語之外的“外語”從以前的必修課改成了選修課。
不過,如今在日本,學生念得最多的第二外語是漢語。
以我任職的明治大學理工學院為例,就有超過一半新生選擇學漢語。他們異口同聲地說:問了父母和高中老師的意見,大家都推薦學漢語,因為中國在國際政治、經濟舞臺上的地位日趨提高,所以學了漢語對日后找工作一定會有利。
另一方面,日本社會曾對歐陸國家擁有的憧憬,似乎已經慢慢消失。千禧年前后歐元誕生后,歐洲各個國家的形象變得模糊不清。為什么要學德語、法語?今天的學生想不到理由。
不過,諷刺的是,大家學漢語并不意味著越來越多的日本人會說漢語。
首先,大學的第二外語班一年只有45到90個學時,即使有認真的學生每節課都上,也僅僅是一年級和二年級總共上了135個小時的漢語班而已,最后能期待的學習效果非常有限。
其次,雖然日語也用漢字,但讀音跟漢語不一樣,為了講漢語,非學羅馬拼音不可。但是多數日本學生覺得,直接看漢字就能猜得七七八八,何必通過辛辛苦苦學拼音去繞道?結果,漢語發音始終擺脫不了日語發音的干擾,對聲調的掌握也遠遠不準。
再說,如今的學生選修漢語,乃是為了得到經濟利益,他們對中國的社會、文化并不一定有興趣。正如大家把英語當作工具一樣,漢語也被當作技術。跟從前的日本大學生心懷浪漫憧憬地學習德語、法語相比,這是多么不同的境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