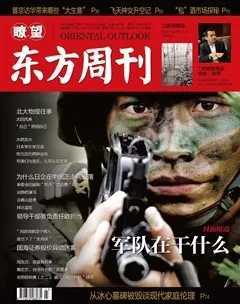歐元區的兩種走向
歐元區的本質是一個政治項目。根據最優貨幣區理論,只有經濟周期趨同的國家才適合一起組成貨幣區。然而,1999年歐元區成立之時,歐元區成員國間經濟差異巨大,一體化程度與理論假定前提相去甚遠,歐洲的政治家卻背離經濟學的基本法則,建立了歐洲貨幣共同體。
歷史經驗表明,建立貨幣區是一項高風險的事業,一旦貨幣區內任何一部分出現嚴重的財政問題,若缺乏有效的調整機制,就會導致政府赤字的貨幣化融資,貨幣大幅貶值,聯盟分崩離析。
歐債危機之所以愈演愈烈,最主要的原因正是由于在經濟結構差異較大的成員國之間,缺乏必要的調整機制化解歐元區內部的失衡。一些專家認為,在緩慢的調整路徑上,歐元區正步入分崩離析的邊緣。
內部實際匯率出現錯配
歐元區陷入危機的緣由之一,在于其內部實際匯率出現錯配,經常賬戶失衡迅速增長。
歐元區成立后,鑒于各國無法單獨通過貨幣貶值或者通脹來減少負債的比率,投資者降低了歐元區各國國債的風險溢價,減少了各國融資成本。這相當于對邊緣國家實施過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引發其工資成本急劇上升,在全球市場中的競爭力逐年下降,經常賬戶出現大量逆差。
與此同時,來自順差國的資本不斷涌入逆差國的工程項目,維持了逆差國的低儲蓄率。國際收支失衡反映了歐元區內部各國存在實際匯率錯配,按照剔除通貨膨脹的實際匯率計算,2000~2008年間,愛爾蘭相對德國實際匯率升值約50%,希臘、西班牙、意大利和葡萄牙分別升值27%、31%、34%和24%。
同期多國經常賬戶均為逆差,截至2007年危機爆發前,希臘、西班牙和葡萄牙經常賬戶赤字占GDP的比重分別高達14. 6%、10%和10. 1%,德國的經常賬戶盈余卻達到7. 4%。這表明,歐元區各國的成本與物價出現了系統性扭曲,亟待調整。
調整機制出現誤判
同時,歐元區設計者對調整機制出現了誤判。
如果貨幣區內某一個國家的名義經濟活動與整個貨幣區的整體情況存在差異,就必須進行某種調整來糾正這一狀況。
調整手段主要有以下三種方式:勞動力轉移、價格調整或自動財政穩定措施。此前歐元區并沒有對內部失衡問題表示過度擔憂,是因為歐元區設計者認為,在最優貨幣區內,只要勞動力可以完全流動,逆差國就能夠自由地吸引來自順差國的工人,將勞工成本保持在低位,維持歐元區整體經濟的平衡。
但是,現實和理論有不小的差距。在危機前,順差國的工人沒有去逆差國謀求工資更高的職位,逆差國的對外凈債務也一直在不斷累積,直至難以為繼,爆發主權債務危機。
而危機爆發后,調整機制再度陷入了僵局,南歐國家的工人并沒有降低工資,涌入強大的北歐國家,反而是遷往昔日的殖民地或者是美國、加拿大,或者是呆在家里抗議降低工資,歐元區各國失業率的差距迅速擴大。以勞動力轉移為主要手段的調整機制在歐元區遭遇失敗。
價格調整的療效差
一般而言,陷入債務危機的國家需要降低本國商品的相對價格,出口更多的商品來償還外債,提高主權信用水平。但由于陷入困境的歐元區成員國無法選擇貨幣貶值,它們只能在不改變匯率的情況下進行“內部貶值”,即通過降低工資,壓低本國相對物價水平,提高競爭力。這也是德國要求南歐各國執行嚴厲的財政緊縮政策的基礎。
而作為歐債危機標準藥方的價格調整,過程非常痛苦,無異于刮骨療傷,療效卻不顯著。
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工資下降提高競爭力的前提是經濟體內的價格富有彈性,工資的變化可以很快傳遞到物價。而研究表明,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和希臘等國,盡管通過結構性改革增加了工資的靈活性,但由于存在價格黏性,工資的下降并沒有伴隨著物價的下滑,反而直接降低了國內總需求。
第二,歐元區是一個相對封閉的經濟體,從失衡走向均衡的過程,需要逆差國和順差國同時付出代價,在西班牙、意大利等逆差國緊縮經濟,降低物價的同時,德國等順差國應該擴張經濟,增加通貨膨脹。但德國沒有動力去做任何的調整。德國在約束重債國財政緊縮的同時,缺乏動力去執行調整計劃。事實上,當前歐元區各國的通脹率較為平衡,相對價格調整的差異非常有限。
根據高盛的研究結果,考慮一種相對樂觀的情況,假定重債國和德國的通脹率的差異為4%,歐元區各國仍然需要很長的一段時間來實施外部調整:葡萄牙和希臘要用15年,西班牙10年,意大利5至10年。能否保證在如此漫長的調整期不讓各國民眾喪失信心?也許內部貶值的價格調整機制只能算是歐元區領導人描述的“海市蜃樓”,可望不可即。
財政聯盟阻力大
以財政聯盟為基礎的自動財政穩定措施,同樣被證明效果不盡如人意。
財政聯盟實際上是一種國家層面的財政風險分擔機制,它可以有效避免貨幣區中某一部分因為資不抵債而陷入主權債務危機,不需要過多考慮是否符合最優貨幣區的前提條件。假如希臘是美國的一個州,那么在陷于危機時,它可以收到大量源于自動轉移支付的支持,華盛頓方面會不斷送來社會保障及醫療保險支票,保證政府的正常運營。
2011年底,歐元區各國推出的財政契約被認為是向財政聯盟邁出了一大步。
如果歐元區真的能夠建立一個財政聯盟,那就可以避免歐元區瓦解的結局,維持歐元的正常運行。
但這其中存在不小的阻力:其一,缺乏政治動力,歐元區本身就是一個政治產物,目的是避免戰爭的威脅,而柏林墻倒塌后,世界的經濟聯系越來越緊密,爆發大規模戰爭的概率越來越低,因此,政治和商業高層以往推動歐元區一體化的邏輯已經失去效力,現在維持歐元區的原因僅僅是因為歐元區分裂的成本太高,而不是歐元區的前景有多么美好,重債國完全是被脅迫著向前,順差國的民眾也已經不再心甘情愿埋單。大家難以想象德國人在危機后愿意無償幫助希臘人或西班牙人交養老保險。
其二,歐元區領導人的缺失。由于歷史原因,二戰后,法國是政治領導者,德國是跟隨者,一般僅僅通過自己重新獲得的金融能力來支持歐洲項目。然而,現在法國和德國領導人各自面臨不同的國內政治使命,雙方的政策方向也出現了較大偏倚,歐元區何去何從充滿不確定性。
可選擇的挽救路徑
挽救歐元區,還剩下一條赤字貨幣化的不歸路。
赤字貨幣化即央行開動印鈔機,直接向財政注資,對于一國暫時渡過難關可能有效,但是對于貨幣區而言,只是“可口的毒藥”。它也是過去在歐洲和美洲各個貨幣區崩潰前走過的最后一段路程。
在歐債危機的演進過程中,也一直有人呼吁歐央行執行寬松的貨幣政策,甚至直接購買歐元區困難國家的國債。這實際上就是在將歐元區實施赤字貨幣化。雖然現階段歐元區整體債務和通貨膨脹水平較低,能夠承擔一部分成本,但這只是一個治標不治本的藥方,寬松的貨幣政策并不能幫助歐元區提高債務可持續性,而只會讓其沿著以往其他貨幣區崩潰的必經之路越走越遠。
從目前情況來看,歐元區已經陷入失衡的泥淖,自拔乏力,原有的調整機制已失去了應有的效力。
未來歐元區的發展可能存在兩種結局:一是奉行緊縮政策,通過痛苦的內部價格調整過程,穩定債務水平,最終建立以財政聯盟為基礎的自動財政穩定措施,只有這樣才能夠在一個貨幣區內容納各種經濟結構差異巨大的國家。
另一種可能是,將歐元區縮小至經濟周期相似的成員國,回到歐元區成立之初的設想,而這種結局的概率可能比第一種要更高一些,畢竟長期刮骨療傷不如來一次腫瘤切除。
(作者單位: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室國際金融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