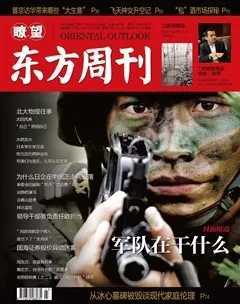周汝昌:寂寞身后事
2012年5月31日凌晨,周汝昌先生在北京紅廟家中去世,享年95歲。
當天下午6時許,獲悉消息的本刊記者趕到周汝昌先生家樓下。一切仍如往日般寧靜,周家二樓窗臺透出泛黃的光亮,窗臺上的一束白花在無聲訴說著一位老人的故去。
周汝昌先生的女兒周倫玲告訴外界,家屬決定不開追悼會,不設靈堂,“讓他安安靜靜地走”。
當天晚些時候,周汝昌先生的兒子周建臨在電話中告訴本刊記者,此前幾天,父親進食困難,離去時并無其他病癥,沒有痛苦。
兩個月前,本刊記者曾走進周汝昌先生家中探訪。當時,即將迎來95歲壽誕的周汝昌精力充沛,思維清晰。在一個多小時的訪談中,老人的談話邏輯縝密,說到高興處撫掌歡笑。談及紅學現狀,先生不無憂慮,認為近年紅學并無大突破;談及自身,先生也仍不忘呼吁“國家多給我些關心”。(詳見本刊2012年18、19期相關報道)
這竟是周汝昌生前最后一次接受媒體采訪。周建臨透露,本刊稿件刊發后,他曾為父親讀過多遍,父親頗為自己的心聲能順利發出而高興。

留給世界的最后文字
6月6日上午,在周汝昌先生去世后的“頭七”,本刊記者再次來到北京紅廟周老家中。
局促的客廳里,一張紅漆斑駁的折疊圓桌上擺放著先生遺像,兩盆綠植從旁依偎。遺像中的周汝昌先生微笑著,一臉慈祥。兩個月前,他就是坐在這張桌子前,接受本刊記者的采訪。
“我活到100歲沒問題。”生前,周汝昌曾不止一次向來訪者表達他的樂觀。
就在去世前的5月23日,已經無力起床的周汝昌還把周建臨叫到床前,讓其在一旁讀書給他聽。他告訴兒子,又構思了一本新書,暫定名為《夢悟紅樓》。根據父親的口述,周建臨將新書大綱一條條記下來。
大綱第一、二條分別是“沒有曹振彥、曹璽就沒有大清國”;“康熙大帝重視漢族文化”;第七條是“要懂得《紅樓夢》的內容,就必須懂上列諸條內容”。全文200余字——這是著作等身的周汝昌留給世界的最后文字。
耄耋之年的周汝昌雙眼僅能識別模糊光亮,聽力也需借助助聽器,講述也多口齒不清,即便是身邊的子女也無從聽懂。每當這時,周倫玲、周建臨等不得不打斷他。正沉浸在自己思緒中的周汝昌先生因此而甚為不滿,會生氣地大聲責備“不要打斷我的思路”。
盡管目不能視耳不能聽,但周汝昌記憶力極好,精力也極充沛。周建臨回憶,近幾十年周汝昌幾乎每天都要口述,不是為新書內容就是為查證各種史料。時日一長,讓子女心力交瘁。
“按照我們的想法,好身體才是第一重要的。他這樣太辛苦了,好多次都不想讓他講,讓他好好休息,他一聽就很生氣。”說到父親晚年治學的辛苦,周倫玲頓覺感傷,“我們還是不了解父親的。”
周汝昌先生有五名子女,周倫玲排行第三,曾下放到陜西寶雞市一工廠當工人,1980年8月,經胡耀邦批示奉調回京,經組織安排進入紅樓夢研究所,任父親的助手。周建臨排行最小,也已年屆60,前些年從北京市大觀園管理處退休。五個子女散住在北京市各處,由周倫玲、周建臨等子女輪班守護在父親身邊,照顧其生活起居。
周汝昌去世后的第三天,周汝昌遺體被送到北京東郊火葬場火化時,胡耀邦長子胡德平通過秘書跟周家聯系,希望親自前往送別。
6月6日下午,周汝昌先生去世后的“頭七”,北京曹雪芹學會在西山黃葉村曹雪芹紀念館舉行了一場低調的周汝昌去世追思會,北京曹雪芹學會會長胡德平出席。周建臨發言時,突然站起身來,離席向坐在身旁的胡德平深深一鞠躬,“謝謝耀邦和德平先生對我父親的關照”。
“不能喝著周汝昌的奶,還罵周汝昌的娘”
周汝昌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是《紅樓夢新證》。自1947年至1953年間,周汝昌窮盡數年心血,搜羅到當時幾乎所有能找到的史料,細致地展開了對曹雪芹身世及《紅樓夢》的考證。
盡管書中一些觀點引發學術界爭鳴,比如他倡導紅學的四大分支,極力將紅學提升到“中華文化之學”,對林黛玉、史湘云等最終命運的推斷,以及對“程甲本”后四十回的否定,等等,但誰也不能否認這是一部“任何有志于紅學研究的人都無法繞行”的巨著。
在6月6日的追思會上,紅學家胡文彬說,今天某些學者通過上網搜索一夜之間就整出上萬言,而當年周汝昌大部分時間都埋首于浩如煙海的故紙堆中,“那都是一個字一個字抄出來的。”
北京曹雪芹學會正是以周汝昌奠定的曹學及紅學為研究基礎。會長胡德平說,今人研究曹雪芹和《紅樓夢》,就離不開周汝昌和《紅樓夢新證》。
“他從來不是容不得不同意見的人。”追思會上,胡文彬回憶起數十年前和周汝昌一起開會的場景:周汝昌講完后,轉過身對一旁比自己年輕20歲的胡文彬說:“文彬,我知道你觀點跟我不同,你講講。”在胡文彬看來,學術觀點不同本是正常現象,但極為詫異的是紅學界一些人士竟與周汝昌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不能喝著周汝昌的奶,還罵周汝昌的娘。”胡文彬說,新中國的紅學從一開始就陷入政治斗爭,現在不能再繼續下去,“否則紅學會死。”
“清貧一生、寂寞一生”
6月1日下午,周汝昌去世的第二天,文化部副部長、中國藝術研究院院長王文章到周家致哀。紅學家、原中國紅學會會長馮其庸先生也向周汝昌子女發來短信表示哀悼和慰問。
當天,中國藝術研究院的工作人員還送來周汝昌先生去世的訃告、生平及治喪委員會名單,請家屬過目。周倫玲提筆將周汝昌名字前羅列的一長串生前社會兼職全部劃掉,僅保留“著名學者、著名紅學家”兩項。
盡管子女一再表示不搞任何追悼活動,但輿論關注的熱忱很高。“這是我們始料未及的。”周建臨說,那幾天他們姐弟倆接聽了來自全國各地數十家記者的求證和采訪電話,“要是父親知道有這么多人關注,他會很高興的。”
6月2日,周汝昌先生遺體在北京東郊火葬場火化,在場的只有親屬,沒有外人。此后,外界的關注漸趨沉寂。至本刊記者發稿時為止,周倫玲說她尚未見到父親去世的官方訃告,只在中國藝術研究院官方網站上看到由中國紅學會、《紅樓夢學刊》分別署名的兩篇表示悼念的官方消息稿。本刊記者就此致電中國藝術研究院辦公室,工作人員告訴本刊記者,訃告在院機關內部發布過,未向外界公開。
上文提到的6月6日下午在曹雪芹紀念館舉行的那場小規模追思會,是周汝昌去世后唯一一場公開悼念活動。
本刊記者作為少數的媒體代表獲準參加了這次追思會。胡德平在發言中說,追思會是對周汝昌先生清貧一生、寂寞一生的很好紀念,“作為一位公眾人物,如果外界(對周汝昌先生去世)沒有任何表示,太不正常了。”
生前,周汝昌甚少談及身后之事,據其子女向本刊記者透露,他臨終前也未留有任何遺言。2002年,周汝昌先生夫人去世,骨灰已寄存了近十年,周建臨曾數次跟父親商量是否購置一塊墓地,但周汝昌每次均表示拒絕。
在周汝昌先生生前經常使用的客廳沙發上,擺著幾尊木雕佛像,據周倫玲介紹,那是父親生前最愛之物。由于目盲耳聵,在口述書稿之余,撫摸這些物件就成了晚年周汝昌的最大樂趣。
周汝昌在世時,從未停歇的學術熱忱曾讓子女疲于奔命。“那種生活很辛苦,但我愿意再延續,只是可惜再也沒有機會了。”周倫玲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