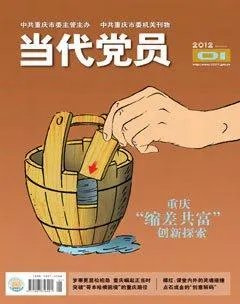傅紅:課堂內外的靈魂碰撞
2011年冬季的一個早晨,大一新生的宿舍里一片靜寂,當時針指向6:30時,樓棟里響起了此起彼伏的短信聲。
“傅老師的短信來了!”
整棟樓瞬間興奮了起來,大家紛紛掙扎著起床。
“不能辜負了傅老師每天早上這200多條短信呀!”有學生說。
學生口中的“傅老師”,就是重慶交通大學最受學生歡迎的重慶市敬業道德模范、“十佳教師”、思想道德修養課教師——傅紅。
案例教學 情滿課堂
2011年10月的一天,傅紅的一堂“思修”課上。
“這是我大學四年看的400多本書的書單,寢室還有100多本自己買的……”周保伍在講臺上將自己在圖書館看過的書單打印出來,展示給學弟學妹們看,他還憑借這份書單在英語四級沒過的情況下,被中鐵八局錄用。
“還有,這是我的書法作品,我從大一就開始練習,每天晚上睡覺前無論多忙都會堅持,直到今天。”周保伍一邊講述自己的故事,一邊將自己龍飛鳳舞的書法作品送給傅紅老師和學弟學妹們。
講臺下,學生們看著書單和書法作品都張大了嘴巴,無不被師兄的毅力所震撼。
這堂“思修”課的主題是教育學生無論做什么事情都要堅持,要有毅力。
“如果是單純的說教肯定沒人聽,所以我就把我能利用的資源,把生活中鮮活的案例搬到課堂上,這樣才真實、才有感染力,讓學生自己去感悟、去反思。”傅紅說,“周保伍同學的事跡首先讓我特別震撼,我相信同樣能感染學生。”
周保伍是重慶交通大學2007級測繪專業的學生,2011年剛畢業,在中鐵八局工作,曾是傅紅“思修”課的課代表,他上學時酷愛讀書,經常把自己的讀書筆記拿來跟傅紅交流,這一交流就是四年。
“我特地請了兩天假來幫傅老師上這節課,因為我們當年的課就是這么上的,我感覺受益頗深。”周保伍說,“很榮幸能成為傅老師的‘案例’。”
很明顯,這堂課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很多時候,傅紅也拿自己當案例。
2008級和2009級的同學都還記得傅紅講的一堂課——關于人的理想和信念。
傅紅講述了自己與父親生死離別時的情景:父親當時身患重病,彌留之際,為了見到還在外地的她,整整一夜都在苦苦支撐,一直保持非常微弱的心跳,直到她趕來……
“人是靠精神支撐的,人活著要有一點精神,人需要為自己的信念而活。”在學生感情被激發起來的時候,傅紅適時地將這一思想傳遞給學生。
課下,一名學生在作業中這樣描述自己的感受:“上這堂課時,大部分人都眼含淚花。我在想,一個人如果失去強大的精神、信念,生命對于他來說已經沒有任何意義。”
很多人都還記得傅紅的第一堂課。
“當她兩歲時的照片出現在PPT上時,整個課堂都沸騰了,立即感覺到這個老師的真誠,一下子就記住了她。”現在讀大二的學生謝謙誠笑著說。
“我就是要把自己赤裸裸地、真實地展示在學生面前,把生命融入課堂。這樣的課堂才有感染力,‘思修’課才能真正‘修’到學生心里。”傅紅說。
傅紅充滿感情的案例教學課幾乎是場場爆滿,然而她的情感互動不僅僅在課堂上。
課外互動 心靈交流
“我知道你是在應付我,我布置作業是想讓你們學會認真地對待每一件小事,不需要多華麗的語言,只要你是真誠的……”在一份不知從哪里抄了幾百字的作業上,傅紅洋洋灑灑批了整整一頁。
“作業是學生心靈的窗口,是我跟學生課下交流的一個很好的媒介,學生會在上面講述自己的情感困惑、家庭的困難、對未來的迷茫等等,這些都亟待老師的引導。但其中不乏應付的,我也會真誠地跟他們交流、解釋,也往往能在下一次的作業本上看到學生的真誠。”傅紅驕傲地說。
傅紅每學期都會上五六個學院近500名學生的“思修”課,跟其他老師不一樣的是,她每學期都會給學生布置3—5次作業,不會固定出什么題目,學生可以自由命題。
每次精心批改500份作業,幾乎占據她課下所有的時間:“我知道學生都很期待,所以都會及時反饋給他們,一旦拖延,就會辜負他們的信任,打消他們的積極性。”
為此,傅紅常常工作到凌晨一兩點鐘。
“靈魂的感召是教育的最高境界,這是我一直以來的追求。”傅紅說,“教師就是為學生而生的,教書應不分上下課,育人應不分上下班。所以,無論是在課堂上,還是在課外,我都非常真誠地與學生進行心靈的互動。”
很多學生不滿足于作業本上的交流,還通過QQ、飛信、電話等方式找傅紅談心。“我的QQ已經加滿了,很多新生要求加入時,我只好忍痛將一些平時不說話的號刪掉。學生的每一條留言、每一條短信,我都會在最短的時間內回復。”
對此,傅紅很驕傲,并慷慨地將自己所有的時間都奉獻給了學生,并用自己的生命感染著學生。
只是,她覺得前行的路上有點孤單。
“期待同伴”
“老師的天職就是教書育人,可在現有的評價制度下,很多老師都患上了‘不育癥’,這究竟是誰的悲哀?”
“每個‘思修’課的老師都應該先給自己上課,給自己測試,覺得真正對得起自己的言行,再給學生上課,才能真正地育人而非誤人。”
…………
這是2011年6月份期末考試學生的答卷,是傅紅特地出的題目“談談對思修老師的期待”。
“與其說是考學生,不如說是考我們老師自己。”傅紅說。
學術研究和教學是大學教師面臨的一對矛盾:前者可以幫自己評職稱、拿項目,后者則可以贏得學生的喜歡,很多人選擇了前者。
“其實在我個人的發展與學生的發展之間,我曾經也是很糾結的。”傅紅說,“現在看到很多同行過上非常富足的物質生活,我也眼紅,但是在兩者之間,我還是選擇了學生。”
由于所有的時間都花費在學生的身上,傅紅自己的職稱評定一直擱淺了下來,十年前與她一起評上副教授的同事都早已評上了教授,而她卻一直“止步不前”。“有時候我會覺得很孤單,在現有的教育評價制度下,很少會有老師把全部時間和精力花在學生身上,但是我覺得我所做的這一切都值得!”傅紅堅定地說,她在付出的同時也不斷收獲著心靈的回報。
“傅老師,我從家里給你帶了棗子,我們家今年的棗子被蟲子咬了,但您放心,給您帶的都是我媽媽一個一個挑出來的。”大二學生薛杰在電話里說。
“傅老師,我從家里給您帶了我媽媽親自種的綠豆。”大二學生謝謙誠說。
…………
每次學生放假返校,尤其是寒假回來,家里都會堆滿全國各地的特產。
此時的傅紅,內心無比溫潤,也更加堅定,同時也盼望著前行的路上多一些同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