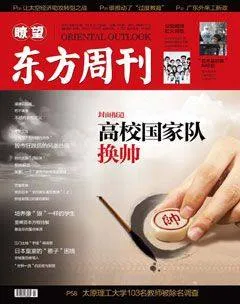拒絕標簽
有些心理治療師把太多心思花在診斷上面,只是為了給對方貼上一個看上去“很科學”的病理標簽,甚至他們把心理治療變成一個病理研究的過程。
這就出現了一個問題:如果心理治療只關注來訪者的問題,而缺乏對來訪者這個“人”的關心與理解,就不能與之建立關系。在這種情況下,不管診斷如何準確,都不會產生好的治療效果,甚至反而會強化“問題”,使“問題”固化下來。因為,當事人會把自己與診斷標簽畫上等號——“我=抑郁癥患者”。
有關研究發現,沒有證據表明診斷標簽對來訪者解決問題有幫助,相反,許多心理治療專家發出警告:慎用診斷標簽。美國心理學家杰伊·賀萊就曾明確表示:“任何判斷一個人有變態傾向的診斷,都會使問題永遠成為問題。”
我有病
剛開始做心理咨詢的時候,有一件事給我的觸動很深。
一天,我接待了一位50歲的女性,她來尋求心理咨詢是因為與丈夫的關系存在問題。更讓她困擾的是,兩年前她被一個心理學教授貼上了一個“精神不正常”的標簽。
這個“權威”的診斷讓她陷入更深的焦慮,以致她重新鼓起勇氣前來尋求咨詢時,我不得不花了很長的時間來處理這個診斷標簽,才讓接下來的輔導變得暢順起來。
我做的是:關心她,體諒她的感受,了解她的生活,跟她一起探討問題及其產生的根源,讓她看到自身好的方面,以及生活中有利的資源,然后尋求具體的處理辦法,并鼓勵她采取行動,嘗試改變。
事情就是從這里開始發生變化。結果是,有一天,她帶丈夫來向我表達感謝,說她跟丈夫的關系已經很好了。
生活中,我們會不自覺地給別人貼標簽,也常常被別人貼標簽。
一個孩子,因為沒有把一件事情做好,父母說他“笨”。其實,說孩子“笨”并不會讓孩子變得聰明,反而會損傷他的自我。因為一件事情就被貼上“笨”的標簽,他就會不自覺地用這個標簽來看自己,把自己跟“笨”聯系起來、等同起來。這樣的情況多了,就會凝固成他的自我評價。
我發現,很多人,不是他們的問題有多糟,而是他們會把自己的情況描述得很糟,而這反映他們對自己的看法很糟。如果這樣一個人去尋求心理幫助,再遇到這樣一個“專家”或“權威”,給他貼上一個“科學的”病理標簽—— 如強迫癥、抑郁癥,或精神不正常之類,他從此就會覺得自己更糟了——“我有病”。
心病的形成
心理問題的形成,往往是“非正常化”的結果。
“非正常化”過程主要包括這樣幾種反應方式:
一是擔心。一般情況下,生活中發生了什么事,頭腦出現了什么念頭,自身做出了什么行為,即使有什么異常,也是可以過去的。但是,當事人太害怕它是不正常的,太在意別人會怎樣看,便會抓住它不放。
二是比較。因為擔心它是不正常的,反而會更加關注它,就會不斷拿這個跟別人比較,拿這個跟自己的過去比較,比的結果是,別人沒有,自己過去也沒有,比來比去,比出更多的“不正常”來。
三是性急。反復比較之下,越發覺得自己“不正常”,就試圖加以掩蓋和壓制,急于除之而后快。因為消除不了,就更加焦慮。在焦慮之中,當事人會四處尋找方法以求自救,便去讀許多心理治療的資料,看到心理癥狀的描述,就開始對號入座,不斷給自己貼標簽,便更加認定自己是不正常的。
最后,當事人可能會帶著他的“不正常”前來尋求心理咨詢,想了解自己到底出了什么問題。表面上,他在要求治療師給他一個明確的診斷。
如果遇到一個不明就里的“專家”給他下了診斷,他會更加焦慮,仿佛他先前的擔心變成了事實;而這診斷恰恰加強了他的宿命感(讓對方認定自己就是一個病人,他的問題是改變不了的)和依賴感,進而損傷他嘗試改變的內在動力。
同時,因為長期遭受痛苦的折磨,加之急于消除痛苦的心情,當事人會期待某一種神奇“外力”(藥物或某種根治方法)來解決一切。如果他再遇到一個只知用藥的“醫生”,讓他相信除了吃藥,沒有其他辦法,就更加把他拋入一種持續性的病態感覺之中。
當事人并不知道,他一路過來,經過自己持續不斷的“感覺性”努力,加上“醫生”只見“病”不見人的“病理化”合作,他終于“生病”了。而在治療上,診斷用藥的單一模式是消極的,因為它在實施“治療”的同時,在強化著當事人的不正常感和無助感。
問題也是機會
我們對一件事情可以有不同的闡釋,不好的闡釋給我們造成困擾,好的闡釋給我們帶來好的心態和積極的行為。
我遇到過這樣一個學生,他考試失敗了,很難過,在雨中走路。對于孩子的這個行為,可以解釋為“他太難過了”,老師和家長給他一些安慰和支持,便會幫助他從這個困難里走過去。但是,老師很緊張,他們把孩子的行為解釋為“神經錯亂了”,便報告給孩子的媽媽。媽媽更加緊張,就把孩子送進了精神病院。
接下來的治療簡直成了孩子的“宿命”。他從此開始吃藥和反復住院,從學校退學,此后,他也曾嘗試去工作,可因為藥物的原因,他的反應能力受到抑制和削弱,不得不從單位退回到家中,之后,與生活隔離開來。
30年之后,當事人的媽媽把他帶來跟我談話。坐在我眼前的他已經45歲,成了一個終生吃藥的精神病人,生活中的支持資源已很稀薄了,自身的適應能力也很薄弱,內心的改變動機也微乎其微。這往往就是單一的診斷用藥模式造成的結果。
還比如,有一位老母親,她有時會獨自一人喃喃自語。她的兒女們會如何解釋這個行為呢?他們可能把母親的自言自語解釋為“母親感到孤獨”,繼而的反應就是多關心一下母親,多花一些時間陪伴母親;他們也可能把母親的自言自語解釋為“母親癡呆了”,結果就是把母親送到精神病院,把她隔絕起來,讓她變得更加孤獨。可見,解釋不同,處理方式也不同,結果會大不相同。
負面標簽會強化一個人的不正常感,心理治療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需要幫助當事人撕掉生活中的負面標簽,撕掉那些迂腐褊狹而又剛愎自用的“專家”的診斷標簽,消解當事人的不正常感。
好的醫治者總是能夠做到“從不好中找到好的”,幫助當事人去反思他的存在,從中看到自身的條件和生活中的資源,對問題有新的理解,樹立解決問題的信心,并且重新選擇。
有時,人們生活在片斷受傷的經驗里,不能全面看待自己的生活。其實,可以這樣理解:“有了問題”也可以被解釋為“有了機會”。當一個人有了問題,他可以沿著問題,讓自己的生命經歷一次深度的分析從而獲得生命的覺察。幸,還是不幸,經歷了,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