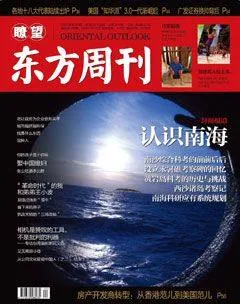相機是贊嘆的工

時隔30年,臺灣攝影師阮義忠還記得那次在臺東馬蘭郊區拍攝的經歷。
那天烈日當頭,一位老農站在水渠中洗澡,一頭牛拴在路邊的橋頭。多么難得的畫面!阮義忠想把這一幕拍下來,便慢慢走過去,和老農搭訕,獲邀后,他卷起褲腳下水,裝模作樣地洗手洗臉,滿心卻在想如何說服對方同意拍照。
后來他什么也沒說,只在取毛巾時特意將相機拿出,放在顯眼處,再緩緩舉在胸前,讓老農有拒絕的機會。老農倒是鎮定自若,只用雙手輕掩“重要部位”。快門“咔嚓”一響,阮義忠一頭冷汗,如同告解的罪人等待發落。誰知老農竟向他鞠躬,說了聲:“真多謝!”
“他永遠是我的老師。”直至今天,阮義忠還記得當年的震動,“他教會我書本上學不到的智慧:做人本分,做事實在,知足,感恩……我何其有幸!”
秉承著從老農那里得到的智慧,阮義忠一步一步在攝影領域做了許多事情:30年來,他拍攝了大量以臺灣傳統農業社會的日常生活為題材的照片,出版影集《北埔》《八尺門》《臺北謠言》《四季》《告別二十世紀》《人與土地》等;1980年代陸續撰寫《當代攝影大師》《當代攝影新銳》《攝影美學七問》,將西方攝影引介至華語世界,尤其對當時信息匱乏的大陸攝影界影響巨大;1990年至2000年主辦《攝影家》中英雙語雜志,影響力及于歐美。
2012年2月,他的新書《人與土地》出版,將當年同名畫冊中的照片一一配文,與更多人分享影像背后的故事和因緣。在序言中,阮義忠寫道:“我在拍照時,最想留住的正是人性的美好:人與人的互信互助,人對土地的依賴感恩,人對天的敬畏、對物的珍惜。這些價值在今天還留下多少?”
日前,《望東方周刊》采訪了正在北京參加相關活動的阮義忠先生。
相機是贊嘆的工具
鄉間孩童的開懷玩耍、農人們的辛勤勞動、拜佛敬神的虔誠信仰、老人家的滄桑智慧,構成《人與土地》的主要內容,從不同角度講述著鄉土社會中樸實純良的風景與民情:
南投魚池鄉的頭灶村,農民們趕著壞天氣來臨之前栽秧。午餐攤在田埂上,足足五菜一湯,田主一直等到所有幫忙干活的村民都吃飽了,自己才進食;
漁鄉大豐收的時候,漁人們會趕緊敲鑼吹螺,希望鎮上的人都聽到。只要趕來投入拔河隊伍,雙手拿得動的魚都算自個兒的……
“我喜歡拍真摯、美善的事物,假的、惡的、丑的,我就不拍。無論到哪里,我都努力去發現那里的好,不愿意揭傷疤。”阮義忠說。對于那些假、惡、丑,或者讓人感到不公、憤恨的事情,他總是抬不起相機,寧可一走了之。
他的作品打動了不少人,但也有批評家認為這是僅停于感動層面的“濫情主義”,說他美化了充滿社會問題的原住民村落,說他對農村與都市,有著過于簡單的善惡二元判斷。他不以為意,娓娓寫道:“證嚴法師說:‘道德是提升自我的明燈,不是鞭打別人的鞭子。’對我來說,相機是贊嘆的工具,不是批判的利器。”
他自稱從來不與臺灣攝影圈子打交道,攝影道路、理念都自成一路,屬于獨特的個人經驗。
臺灣攝影在早期的幾位大師如郎靜山、張才、鄭桑溪之后,進入相對貧瘠和空白的時代。上世紀50年代開始到80年代中期,資訊閉塞。與之相應的,60年代的西方現代思潮、70年代的回歸鄉土吶喊、80年代“解嚴”后的解放、90年代島內逐漸興起的“統獨之爭”與族群矛盾,也都給文藝創作者們以影響和挑戰。
但在出生于1950年的阮義忠身上,似乎看不到什么痕跡。他始終將鏡頭對準那些恒定不變的價值與可貴的人性,用英國攝影師布萊恩.坎貝爾對他的評論來說,他的照片“有一種永不妥協的尊嚴和正直”。
從土地逃離又回歸
很難想象這么熱愛土地的人,早年間最大的愿望就是逃離土地。
阮義忠出生在臺灣宜蘭縣,家里世代都是木匠,有幾分在河堤附近的薄田。孩童時期,他最常做的事情就是跟兄弟姐妹去田里撿石頭,扔出去,等下次大水把石頭沖回來之后再重復一次。“就像西西弗斯。我那時厭惡透了這種生活,一心想離開土地,做個知識分子。”
祖父擅長神案雕花,家里放著各式圖樣,由此引發了阮義忠繪畫的興趣。初中二年級時,他曾花一整年畫了三本連環漫畫書,向臺北出版社投稿。當然未中。所幸后來得到高中美術老師的鼓勵,他畫了許多鋼筆畫,參加各種比賽,同時拼命讀書,讀了小鎮上幾乎所有能找到的讀物,連羅素的《數理哲學》都不放過。
這些積累打下很好的基礎,高中一畢業,自知考不上大學的他前往臺北求職,很快受到詩人痖弦的賞識,留他在其主編的《幼獅文藝》繪制插圖。《幼獅文藝》當時在臺灣所有大學、中學每個班級必須訂閱,堪稱當時臺灣最普及的文學雜志。阮義忠因此迅速成名。
“太早成名使我變得目空一切,以為這全是因為自己才高八斗,完全不知道其實與時代背景相關。”如今回首往事,他認為痖弦“是我生命中第一個貴人”,并遺憾自己從未當面對痖弦說出這句話。
這段工作被兵役打斷。服役結束,他到《漢聲》雜志(當年還是英文版
這是1973年,接觸攝影徹底改變了阮義忠的人生。當他第一次外拍,拿著相機到了臺北手工業者聚集的萬華社區時,發現自己站在那里完全傻了眼,對著這么多形形色色的人,他卻不知該拍什么。
“那時我有一種巨大的羞愧心,因為發現以前從來沒有認真看過別人,完全在自己的理念中打轉。”
那一天是他人生中重要的轉折點,從此他開始學著正視自己所見,落實于現實生活。而由拍攝臺灣鄉村而來的對土地的情感,也恰成為對自己成長時代的反思。
辦雜志是一生最驕傲的事
聊天時,阮義忠常常用的一個句子是:我何其有幸!他的有幸在于,總是在合適的時機,做成最想做的事。
與太太袁瑤瑤的相遇應該算是最有幸的事情之一。那時阮義忠與詩人管管相熟,后者正與臺灣的散文作家袁瓊瓊戀愛,阮義忠見面時便央她幫忙介紹女朋友,沒想到她將自己17歲的妹妹介紹來了。兩個人之前都沒談過戀愛,從初戀到結婚,一直相守到現在,覺得對方“越來越可愛”。
《攝影家》雜志的創辦也是不可思議的因緣。
1990年阮義忠夫婦去法國南部圖盧茲市參觀“水之堡”攝影畫廊,那里正舉辦攝影誕生150年特展,全世界數百張重要的大師作品都在此匯集。阮義忠與畫廊創辦人尚.杜杰德一見如故,并表示希望有朝一日能見到這些重要展覽出現在臺灣。沒想到回臺灣第三天,就有文化官員打來電話,問有沒有什么辦法在半年內組織一場國際攝影活動。阮義忠心下暗喜,一口答應下來,第二天就發傳真給杜杰德,希望能把“水之堡”的展覽全部搬來臺北。對方驚喜不已,居然有這么快的行動力!
談定展覽事宜,阮義忠突然想到,自己一直希望能辦一本雜志,現在有這么多優秀資源在手,何不就此跨出第一步?念頭一起,他就停不下來了,先是決定拿半期內容刊登展覽作品,另外一半刊登華語世界最好的攝影作品。他找到大陸的攝影師呂楠,選用了他的作品《被人遺忘的人:中國精神病人生存實錄》—— 這是這位如今在國內首屈一指的攝影師第一次在華文刊物亮相。
有了好作品,阮義忠決定必須用最好的紙、最佳的開本,必須中英雙語,向全球發行……
“他最大的特點就是像孩子一樣,非常單純,遇事不考慮太多。”袁瓊瓊這樣評價阮義忠。辦雜志就是例證,那時為了籌款,他們連房子都抵押了,而且第一期辦完,還不知道第二期的內容在哪里。阮義忠卻不發愁,他總是全心投入,有完美主義者的要求。他相信歌德作品里描述的理念,“只要你態度正確,很多人都會愿意助你一臂之力。”
《攝影家》一辦就是十年,僅憑他們夫婦及三四位工作人員。62期刊物在數碼時代到來之前,對世界范圍內的膠片攝影做了系統梳理,在國際攝影界逐漸占據了重要地位。
“如果說我做過什么可以驕傲的事情,就是這本雜志了。”阮義忠說。
他本來期許能做到100期,沒想到1999年9月21日,臺灣大地震突如其來。“我覺得我的照片成了一片廢墟。你拍了半天也沒辦法幫助別人,藝術工作者有用嗎?”他回憶當時自己的困惑。

沒有希望更要做事
在北京的5天時間里,阮義忠要參加4場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