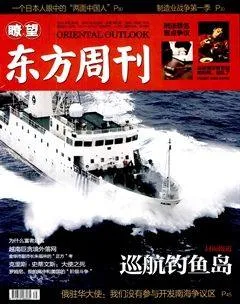甲骨四堂
在抗戰流亡四川南溪李莊的時候,傅斯年每提到羅振玉,總是咬牙切齒,以“羅振玉老賊”相呼。
1912年2月,著名古器物與古文字學家羅振玉,按照世間流傳和自己調查的線索,委托他的弟弟羅振常到河南安陽訪求甲骨。羅振常不負所望,在安陽小屯逗留五十余日,不僅弄清了甲骨出土地的準確位置,而且搜求甲骨多達1.2萬片,動用火車分兩次運往北京。
羅振玉通過對這批甲骨深入細致的研究,從《史記·項羽本紀》“洹水南殷墟上”的記載中得到啟示,認為安陽小屯之地就是《史記》記載中商朝“武乙之都”。后來羅振玉在其所著《殷墟書契考釋》自序中,確定了小屯為“洹水故墟,舊稱嬗甲,今證之卜辭,則是徙于武乙去于帝乙”的晚商武乙、文丁、帝乙三王時的都城。這個考釋,無論是當時還是之后,均被學術界認為是一項了不起的具有開創性的重大學術研究成果。
1928年,傅斯年派34歲的河南南陽人董作賓前往安陽小屯殷墟進行調查,并主持首次科學考古發掘。至1937年春,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在殷墟共進行了九年十五次發掘,出土有字甲骨24918片,另有大量頭骨、陶器、玉器、青銅器等器物出土。其發掘規模之大,牽涉人員之多,收獲之豐,前所未有,世之罕見。
這一創世紀的偉大成就,正如后來著名考古學家、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張光直所言:“在規模上與重要性上只有周口店的研究可以與之相比,但殷墟在中國歷史研究上的重要性是無匹的。”
最后一次殷墟發掘始于1937年3月,一直延續至6月。此時,整個華北已是戰云密布,日本人磨刀霍霍,即將血濺中原、飲馬長江。面對一觸即發的中日大戰,為防不測,殷墟發掘不得不于這年6月19日匆匆結束——這是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之前最后一次發掘,也是國民黨政權屬下的考古者在殷墟的最后一次有組織的發掘。當發掘人員于匆忙中將出土器物整理裝箱,風塵仆仆地押運到南京欽天山北極閣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大廈時,震驚中外的盧溝橋事變爆發。
自此,史語所全體人員開始了戰時流亡生活,先長沙,后昆明,再遷往四川南溪李莊。抗戰勝利后,史語所重返南京大本營,但喘息未定,內戰又起,1948年底,史語所隨敗退的國民黨政權遷往臺灣,這是中央研究院屬下13個研究所中唯一一個較完整遷臺的大所,主要骨干傅斯年、李濟、董作賓、勞干、石璋如等均隨之遷臺。當年殷墟出土的數十萬片帶字甲骨和大批器物,成為流亡孤島的學者們研究的主要對象。
且說自甲骨文被認識和釋讀之后,隨著史語所科學發掘的進展和有字甲骨的不斷出土,學者們對其研究的興趣大增,漸漸形成了一項專門的學問——甲骨學。這門學問若以王懿榮為起點,直至20世紀結束,其名聲最顯赫、貢獻最大者乃是三十年代國學大師錢玄同、陳子展所說的“甲骨四堂”,即羅振玉(字雪堂)、王國維(字觀堂)、董作賓(字彥堂)、郭沫若(字鼎堂)四位甲骨學家。
這四人中,當年殷墟發掘的總主持、史語所所長傅斯年對羅、郭二人頗為不滿。據史語所研究員屈萬里說,在抗戰流亡四川南溪李莊的時候,傅斯年每提到羅振玉,總是咬牙切齒,以“羅振玉老賊”相呼,其緣由是“因為他不滿羅振玉后來保溥儀搞出‘滿洲國’那一套事情,對于羅的學術地位他并不完全加以否定。他所以罵羅振玉,也許因為羅在節操上很不夠,很使他看不起,正好像他不滿意他的祖先傅以漸一樣”。
清王朝倒臺后,羅振玉作為遜帝溥儀的“寵臣”,曾追隨溥儀跑到滿州搞了一個“滿州國”,并墮落成日本的傀儡漢奸。而傅斯年的高祖傅以漸乃滿清入關后第一位狀元,歷任順治朝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掌宰相職。傅斯年認為在明朝崩亡之際,作為讀書人的傅以漸應舍身保國,也就是要奉明王朝為正朔,與朱家王朝共存亡,不應屈服于滿清夷族并任新朝官職,傅以漸的所作所為,乃傅氏家族與天下讀書人的大恥辱。
正是置于這樣一種觀點,傅斯年在人前從不談他的高祖傅以漸,后來他自己不惜一切代價追隨蔣政權流亡臺灣并發誓“歸骨于田橫之島”,皆與這一思想態勢有關。傅對羅的態度緣由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