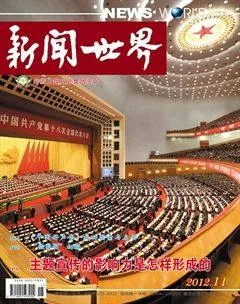突發事件的對外報道與國家形象塑造
【摘 要】在社會轉型時期,突發事件的發生越來越頻繁,而突發事件的報道離不開新聞媒體。國外民眾主要是通過大眾傳媒來了解和認識中國的,因此,突發事件的對外報道和傳播對建構國家形象具有重要意義。本文從國家形象與媒體應對突發事件的態度之間的關系出發,談談媒體應如何做好突發事件的對外報道,進而提升我國的國家形象。
【關鍵詞】突發事件 對外報道 國家形象
一、國家形象的含義
按照中國傳媒大學賀文發的說法,“國家形象”其實質是人們從自己的人生體會,包括直接經驗和間接經驗,或借助主動或被動的閱讀和聽說,尤其是借助于大眾媒介所獲得的感知中對于一國的閱讀、理解和因此得出的關于該國的印象。①國家形象被認為是國家“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每個國家都希望在國際社會樹立一個正面的形象,而國家形象很大程度上是靠國際輿論環境塑造的。
至于國際輿論環境,按照前國務院新聞辦主任趙啟正的說法,“國際輿論環境就是國際社會對一個國家的評論和總體印象,國際上多數媒體的報道和評論形成對該國的輿論傾向。”②在信息社會,國際社會對一國的印象和評價,主要來自于新聞媒體的報道,特別是突發事件中媒體報道的態度、報道的方式、報道的客觀公正性,將直接引起國際人士及國際媒體的高度關注,形成對該國的國際輿論環境,進而影響國際社會對該國的整體印象及評價。
二、突發事件的特點
按照楊保軍教授的觀點:“所謂突發公共事件,就是指在一定范圍內突然發生的危及公眾生命財產、社會秩序、公共安全甚至國家利益的事件。”③《中華人民共和國突發事件應對法》將突發事件分為自然災害、事故災害、公共衛生事件和社會安全事件四大類。
當前,我國正處在社會轉型時期,容易引發突發事件,突發事件主要有以下幾個特點:
1、突發性
突發性是突發事件最顯著的特點。突發事件往往是出人意料、打破常規的事件,如地震、非典、群體性事件等都屬于突發性事件。突發事件大多無法預測,事件的持續時間比較短,政府來不及周密思考處理方案,早一秒鐘采取措施也許就能轉變事件的發展方向,或是抑制事態的進一步惡化,所以,突發事件的反應處理也具有突發性。
2、破壞性
一般來說,大多數突發事件都具有破壞性。突發事件一般是以突變的、激烈形式出現的,如海嘯、車禍、泥石流等,突發事件一旦發生,將會使人們生命財產安全造成嚴重損失,甚至造成大量人員的死亡。另外,突發事件還會給人們的心靈帶來極大傷害,精神受到重創,長時間難以從事件的陰影中恢復過來,影響人們的正常生活。
3、焦點性
突發事件一般是非正常的、偏離正常生活軌道的事件,它會在一定時間內破壞社會平衡,擾亂正常的生活秩序,同時其突發性和破壞性使得其具有強烈的刺激性,富有較高的新聞價值,極易引發人們的高度關注,形成社會熱點。在當今媒體競爭激烈的時代,通過集中報道突發事件來提升自身的競爭力,已成為新聞媒體的共識。
三、在對外報道中如何塑造良好的國家形象
1、媒體要正確理解“以正面宣傳為主”的方針,樹立良好的國際形象
過去,我國的對外傳播過分強調“家丑不可外揚”,對“以正面宣傳為主”的理解即報“喜”是所謂的正面報道,報“憂”則是所謂的負面報道。因此,我國傳媒經常在重大新聞事件對外報道中“失語”和“缺席”。其實,“‘以正面宣傳為主’有一個報道數量的比例問題,其實質看效果,是實現‘于我有利’原則的具體化,即力求達到與國家于人民有利的正面效果。”④
“以正面宣傳為主”并非只報道積極的方面,對負面的信息一概閉口不言。其實,正面報道如果報道不當,完全可能產生負面效果;而負面報道如果報道得當,也可能產生正面效果,“以正面宣傳為主”歸根結底是要看其報道是否產生了積極的、正面的效果。“正面宣傳”不是不報道災難事件,而是要整體報道。其目的是通過報道解除受眾對突發事件的信息渴望和焦慮,進而做到應變而不亂,臨危而不懼,使新聞報道真正發揮其應有社會警示和監視作用。
如果我國傳媒在重大突發性事件中,經常出現失語和缺席,外國受眾將會對我國傳媒以至于對我國政府的可信度產生懷疑。在信息時代,任何掩蓋重要信息或者推遲重要信息披露時間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假裝“若無其事”是難以奏效的,一旦被證實,將會嚴重損害我國對外傳播的可信性,進而嚴重損害我國的國家形象。
2、快速準確地公開信息,第一時間搶占輿論制高點
“流言止于公開,謠言止于透明”。很多突發事件的案例告訴我們,突發事件發生后,政府應及時搶奪“話語權”,在第一時間發布權威信息,先入為主,掌握主導權,使不實的傳聞和謠言沒有產生、傳播的空間和機會。因此,政府必須改變先前對待信息的沉默與控制處理的方式,改變過去一味地“壓”新聞的做法,做到勇于公開、及時公開、善于公開。
如果新聞傳媒對突發事件刻意地“漏報”、“瞞報”、“誤報”,新聞傳媒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義,尤其是在重大突發性危機事件面前,媒體的失語與沉默會使新聞媒體的公信力大打折扣,長此以往,必然會影響國內外受眾對媒體的信任感,進而影響到政府形象和國家形象。
在“哈爾濱水荒事件”發生后,政府發出公告稱“要對全市供水管網進行檢修”,但市民并不相信,懷疑與猜測開始出現,有的說是水源被污染了,也有流言說是恐怖襲擊甚至地震來了,導致了民眾的恐慌。CNN報道稱,“哈爾濱900萬城鎮居民中蔓延的恐慌,主要是因為政府在針對潛在的健康威脅而發布信息的時間太過于延誤。”“哈爾濱水荒事件”使社會的信任機制遭到破壞,公眾開始不信任媒介,并由此波及到對政府的不信任,國際社會對中國政府的不信任,進而波及到國家的海外形象。相反,在2008年的汶川地震和2009年“7·5”烏魯木齊打砸搶燒暴力事件中,中國政府和媒體吸取了經驗教訓,在第一時間公開了災情,有效防止了各種小道消息的傳播,一個高效、有作為的正面的國家形象也隨之傳播到國際社會。
3、注意突發事件對外報道的“針對性”
突發事件的對外報道要有針對性主要是指報道的表達方式。過去我國媒體在對外報道中往往是向外國受眾宣傳中國的觀點、立場,意識形態色彩太重,觀點太直白,語氣太生硬,還一味地“只報喜不報憂”,使很多的國外受眾對我們的報道產生了不信任感。因此對外報道要一切從實際出發,用事實說話,通過組織有針對性的報道,擺事實、講道理,把正確信息傳遞給國外受眾,爭取輿論上的主動。
新華社對外部主任嚴問斌認為,在突發事件的對外報道中,要想方設法引導國際輿論,主要表現在:一是爭搶先機,中英文發稿量是日常的三倍以上;二是注重細節,以真情“大愛”展現人性之美;三是貼近用戶,廣泛使用專業化的通訊社傳播手段——特急電、快訊、簡訊和滾動發稿、現場特寫,綜合利用各種消息源播發長篇報道;四是增加英文評論;五是增加新聞背景。六是使用“數據盒”、“數據與事實”等方式,為外國媒體提供急需的新聞背景。⑤在汶川地震的報道中,媒體較好地引導了國際輿論,也讓國際社會對中國的媒體刮目相看,樹立了良好的國際形象。
4、開發互聯網等新媒體的潛能
網絡媒體在新的輿論格局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對許多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來說,互聯網已經成為他們的第一信息來源。事實證明,很多突發事件首先是從網上傳播,然后再擴展到傳統媒體的。
在突發事件的對外報道中,國家應注意做好網上輿論宣傳。其中重要的一環就是暢通信息渠道,確保第一時間發布權威信息,阻止流言和小道消息的傳播,把握報道的主動權,搶在國外媒體報道之前發布準確信息。及時、主動地發布權威信息,一方面保障了公眾的知情權;另一方面可以減少流言和謠言的傳播特別是網上傳播及其負面影響,避免出現不利的輿論導向,有利于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爭取廣泛的理解、合作與支持,同時,有利于引導境外輿論,使西方媒體的一些鼓噪之音、猜測之言、攻擊之詞沒有生存和傳播的空間。
5、為媒體做好突發事件的報道建立制度上的保障
突發事件的對外報道,其根本問題不在于媒體的報道技術,而在于報道的制度上。隨著中國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經濟的發展要求政治體制的變革,而政治體制變革的突破口又集中表現在對社會各方的權利安排和界定上,表現在新聞實踐上則要求新聞理論和新聞法的逐步跟進。⑥
2002年南京湯山投毒案的信息發布既不及時也不充分;震驚全國的廣西南丹礦難如果不是媒體的強行介入,真相幾乎被掩蓋。這些都造成了不良的政治影響,損害了我國政府的形象。SARS事件中媒體的普遍“失語癥“和“失真癥”的問題,損害了公眾的知情權,造成疫情蔓延的嚴重后果。由于長期的“壓新聞”的慣性,使得政府對疫情的防范和控制被延誤了,如果一家媒體在突發事件的報道上出現失語,還可歸結為技術性的操作失誤,而對于集體性的沉默,則不只是技術失范的問題。《人民日報》原副總編輯周瑞金認為:“這主要不是媒體的責任,責怪媒體有失公允;但無論如何,媒體并沒有盡到自己的社會責任。”
其實這就涉及到制度性問題。其一,行政權力的過度膨脹導致媒體功能性發揮的萎縮,對此,《信息公開法》的出臺從制度層面上有利于媒體真正發揮其作為民意代言人的角色;其二,媒體本身在突發事件對外報道上雖然有一些制度性的保障,但由于不成體系,所以目前非常需要一部完備的新聞法來進一步充實和保障媒體在關涉公共性危機事件的對外報道中的權力行使。
參考文獻
①賀文發:《突發事件與對外報道》[M].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8:97
②④劉洪潮主編:《怎樣做對外宣傳報道?》[M].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5:154、173
③楊保軍,《簡論“突發公共事件”中的媒體角色》[J].《理論視野》,2009(7):46
⑤⑥賀文發、李燁輝:《突發事件與信息公開》[M].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0:255、215
(作者:湖北大學2010級新聞研究生)
責編: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