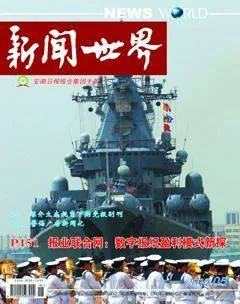如何讓網絡輿論回歸理性
【摘 要】從近年網絡輿論的發展來看,網絡上的言論表達多了自由,少了理性。網民在通過網絡參與公共議題的討論時常常超出言論在法律和道德層面上的尺度,帶有極端的感情色彩。本文選取了近幾年網民熱炒的幾個典型事件進行分析,認為網絡輿論存在極端情緒化傾向,這種情緒化網絡輿論扭曲了言論自由的內涵。并就網絡輿論如何“去情緒化”提出一些建議,讓網絡輿論回歸理性。
【關鍵詞】情緒化 網絡輿論 輿論引導
網絡技術的發展給網民提供了巨大的信息空間和意見平臺,也創造了強勢的“輿論場”。但與此同時在這個“草根狂歡”的年代,“情緒化網絡輿論”的肆意彌漫,扭曲了真正的言論自由,而網絡輿論“去情緒化”將凈化網絡輿論場,化解網絡民意過度表達造成的被動局面。
一、情緒型輿論與網絡輿論情緒化,孰輕孰重
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謝新洲指出,“通過網絡,來自社會底層的信息、意見、觀點、聲音找到了一個出口”①。有學者提出,“網絡上的輿論多是處于潛輿論形態,多是一種情緒型的宣泄……隨著言論的開放,越來越多的‘敏感話題’開始出現——案件真相、內幕、隱情,一件比一件聳人聽聞。網絡上的這些新聞引導了一種民意的情緒性宣泄,即情緒型輿論的彌漫。”②筆者認為,“情緒型輿論”的提法,不足以反映當前網絡輿論常常“激情有余而理性不足”的現象。從現實來看,帶有情緒宣泄特征的網絡輿論往往表現為直截了當的情緒發泄、偏激的語言甚至謾罵等特點。這里的“型”字,更像是向學科劃分一樣對網絡輿論的進行簡單的歸類,中性而不形象。所謂“情緒化網絡輿論”是一種基于某種利益驅使或不良信息的刺激,網民在網絡上散布的一種觀點片面、言辭偏激、語言粗俗、暗含仇恨心理的、異常情緒化的言論。這里的“情緒化”帶有貶義色彩,比“情緒型”更具有警世性,因此,用“情緒化網絡輿論”更合適形容我國當前網絡輿論形勢。
二、從全民喜好到全民“嗜好”
2012年1月發布的《第29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表明“截至2011年12月底,中國網民規模突破5億,達到5.13億,全年新增網民5580萬。互聯網普及率較上年底提升4個百分點,達到38.3%。”③互聯網在中國的強勢不在于它的規模,而是其社會影響,尤其是培養了數億樂于并善于網絡表達的網民。
2008年6月國家領導人陸續做客人民網“強國論壇”,以互動的形式了解民情、解答民疑、解決民難,將親民形象通過互聯網傳送到網民面前。這一互動激發了網民參與公共事務的熱情,網民對用網絡輿論來行使“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的熱情空前高漲。
2008年末,周久耕“嚴肅查處低價銷售房產的開發商”的言論,引起網民的質疑、聲討,并通過“人肉搜索”曝出這位房管局長“抽高檔香煙、戴名牌手表、開奢華轎車”的種種腐敗作風,事隔18日后,這位 “史上最牛房管局長”被“拉下馬”。
“中國人在現實中經歷30年巨變,在網絡里經歷15年的巨變,網民從看客變成演員,成了互聯網的內容制造者、現實社會的監督員。”④越來越多的網絡輿論中摻雜著功利化、暴力化、低俗化、情緒化的因素。汶川大地震發生后,很多網站都設立了“企業捐助愛心榜”,將各企業的捐款金額公之于眾。網友們根據每個被公布企業的規模、贏利情況、社會地位來判斷捐款額與該企業的現實狀況是否相符合。一旦某家企業在抗震救災中的現實表現辜負了網民對它的期望,網友們會通過公開“黑名單”、網絡聲討、網絡倡議等形式要求消費者抵制該企業的一切產品等手段對其進行輿論懲罰,這給企業的形象、營銷帶來重大破壞。
網絡輿論的情緒化火焰又燒進了法庭,“網絡輿論審判”愈演愈烈。當“深圳梁麗案”、“湖南羅彩霞案”等案件還處在偵查環節,法院都尚未開庭審理時,“網絡輿論”就搶先一步把裁決書下達到當事人了。某些“網絡意見領袖”別有用心地發貼,網民基于某種心理需求——譬如好奇、正義感、尋求一種認同感,瘋狂跟貼,以帶有強烈感情色彩的語言描述案件或當事人,給審理案件的法官、陪審員施加了無形的壓力。
網絡輿論的種種表現折射出散布于網絡公共空間的一種失衡失準的情緒,“網上發言”演變成一種不良“嗜好”。
三、情緒化網絡輿論的特征
1、情緒化網絡輿論的主體是有條件的年輕網民,而這些發起者往往是基于某種利益驅使或不良信息的刺激
根據統計,我國網民的人員結構如下:第一,從年齡結構來看,我國網民主要是10-39歲的青年人,約占網民總人數的83.5%。其中,10-19歲的占33%;20-29歲的占29.8%,30-39歲的占20.7%。第二,在城鄉分布上,我國的網民主要集中在城鎮地區。據報告顯示,我國農村網民的規模是9565萬人,城鎮與農村的網民各占網民總人數的71.7%和28.3%。第三,在職業構成上,超過5%的職業群體依次是:學生(31.7%)、企業/公司一般職員(13.9%)、黨政機關事業單位工作者(10.5%)、無業/下崗/失業者(7.4%)、專業技術人員(7.1%)、自由職業者(6.9%)、個體戶(6.9%)。⑤
根據我國網民的人員構成與分布情況來看,網絡輿論的主要參與者是生活在城市、有一定的經濟能力和足夠閑暇使用網絡,關注社會新聞樂于發表意見的年輕人。在我國近年來的網絡事件中,我們也可以感受到,這群年輕網民明顯具有以下群體特征:沖動、善變和急躁;易受暗示和輕信;群體情緒的不穩定。
2、情緒化網絡輿論與一般的網絡輿論相比,呈現出多樣的、異常的、極端的情緒化心理
通過分析凱迪社區、天涯社區、貓撲論壇、豆瓣論壇等主流論壇上,在2008年1月至2009年11月期間,點擊率最高、跟帖量最大的網絡事件,網絡盛傳的輿論事件中情緒氣焰最高的不外乎四類,分別為:對社會不公的不滿、對社會道德缺失的不滿、對教育問題的憂慮、高漲的民族情緒。
3、形成網絡輿論的熱點事件,均有明確的攻擊對象和攻擊點
網絡輿論中的“直接攻擊對象”是當事的一方或是幾方,而在輿論形成的過程中“攻擊對象”往往擴大到當事方所代表的利益群體,形成所謂的“身份符碼”。攻擊點也擴大到事件背后的種種社會現實問題。
4、引發情緒化網絡輿論的往往是社會最新事態,包括個人私事和公共事務
現在許多所謂的“網絡熱點”,都是集中于社會陰暗面、腐敗案件、突發事件的一些負面效應。網絡公話語空間開始出現這樣一種現象,會唱反調的人容易出名。
四、“去情緒化”,網絡輿論引導責任重
情緒化的網絡輿論帶有一種強烈的顛覆欲望,其目的不僅僅是監督,而是置“被輿論的對象”于死地而后快。此時,若不及時引導輿論,不迅速對曲解的事實進行澄清,不對情緒化輿論進行合理疏導,必將會煽動更多不明真相的群眾的非理性情緒,造成社會民意的假象,最終導致社會不和諧因素增加。“去情緒化”,讓網絡輿論回歸理性。筆者認為,以下幾項措施值得考慮:
1、健全針對網絡媒體的法律規范體系
網絡本身的平等性、去中心化、反權威特性決定了硬性的規章制度在互聯網中都是行不通的,網絡立法要從網絡特性出發,制定針對網絡傳播的法律法規應具體界定公民的隱私范圍,對濫用自由表達,隨意威脅、中傷、誹謗、侮辱他人的行為及觸犯國家利益的行為,應當進行嚴厲查處;明確網站的監管義務和相關法律責任。
2、強化網站的監管職責
現實中,很難從微觀層面對網絡輿論實行全面監控,各個網站的自覺監管就顯得很重要。網站可以制定詳細的規則加以規范,并使之有效滲透。例如運用信息抓取與分類的技術方式、“對網絡媒體實行7×24小時的全職管理模式,及時掌握負面信息、不適合發表的言論,并針對其進行快速反應”⑥。
3、培養高素質的意見領袖
培養高素質的“意見領袖”,利用這些“意見領袖”來引導網上輿論,已成為一些主流論壇和社區的普遍做法。這些“意見領袖”有見地、有代表性的發言一般被版主用醒目的字號和色彩加以強調,放在網頁的突出位置,以強化主流言論。針對情緒化網絡輿論的特點,“運用理性力量和情感因素來進行輿論引導,從認知、情感入手,曉之以理、動之以情,通過所報道的事實和評論來引導網民思考,以清醒的分析、負責任的指點和睿智的預示,將‘網絡暴民’領出‘視覺盲區’和‘認識誤區’,使之產生認同與共鳴。”⑦
4、加強網絡把關
網絡把關人應設置有意義的議題,吸引網民參與到公共話語空間,通過自由熱烈的網絡交互,加之網站及時、準確的權威報道和專家評論“以正視聽”,對不同空間的話語進行整合,在交流中引導網絡輿論,讓真理愈辯愈明,促成正確輿論的形成。
5、增強網民自律
基于網絡輿論的特性和網絡輿論的情緒化的成因,網民自律相比外在的約束力,對網絡輿論“去情緒化”有著更強效和持久的作用。筆者認為,這里的網民自律除了寄希望于網民自身文化水平、道德水準的提高,還要重視網絡使用經驗的積累和媒介素養的提升。
網絡輿論作為大眾情緒宣泄的一種渠道,其本身無可厚非。許多網民挖掘出的熱點事件,與社會現實問題切實相關,在客觀上促進了社會的健康發展。但這并不意味著情緒的宣泄就可以為所欲為、 不受限制。傳統媒體“做有責任的媒體”,但是在如今網絡輿論越來越情緒化的形勢下,我們也呼吁網民“做有責任的網民”。
參考文獻
①謝新洲,《應充分發揮網絡輿論監督作用》,新華網新聞教育,2009-3-2,
http://news.xinhuanet.com/edu/2009-
03/02
②彭鵬,《如何調控網絡情緒型輿論》,《軍事記者》,2004(10):37
③《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2012年1月
④陳漠,《2009年中國網絡生活紅皮書》,《新周刊》,2009年(20):50
⑤《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2012,12-16
⑥劉銳,《人肉搜索與輿論監督、網絡暴力之辯》,《新聞記者》,2008(9):49
⑦陳明、楊國煒,《中國網絡輿論現狀與輿論引導》,《瞭望》,2004(9):33
(作者單位:河海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新聞傳播學系)
責編:姚少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