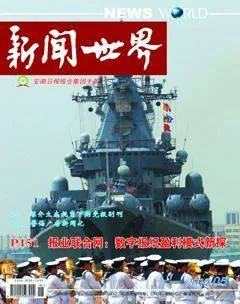“網絡圣戰”中的信息傳播特征
【摘 要】近年來,“網絡圣戰”常有發生,并以其規模巨大嚴重影響網絡安全。本文試圖運用網絡群體事件的理論來具體分析“6·9圣戰”中的信息傳播特征。
【關鍵詞】圣戰 群體性事件 網絡 信息
“網絡圣戰”指的是網絡空間中發生在網絡團體之間雙方因意見、觀念等不同而產生的一種對抗方式。挑起圣戰的主動方向其所認定的目標群體的網絡社區發起進攻,主要是通過不間斷地大量發帖或恢復帖導致對方的交流平臺秩序混亂,使其不能達到正常的信息交流的作用。本文試圖運用網絡群體性事件的理論觀點,來具體分析“6·9圣戰”這場網絡圣戰。
一、事件回顧
“6·9圣戰”事件源起2010年5月30日為獲得韓國人氣天團Super Junior(以下簡稱“SJ”)當晚的演出入場券,數千歌迷擁擠在世博演藝中心取票區域,一度造成混亂引發踩踏,園區方面不得不出動大量武警維護現場秩序,現場一片混亂。事件網絡上曝光后,引起了網友的極度反感,隨后以“魔獸世界吧”為發源地,在天涯、貓撲等各大網站出現了網友有組織的反對SJ及粉絲的活動,引爆反哈韓網民同SJ粉絲的大混戰。
數萬名網友打著“腦殘不死,圣戰不息”的旗號,相約于6月9日晚7時,在知名網站和論壇對韓國明星團體及粉絲進行爆吧、聲討等行為。截止6月10日上午10時,已有數十家韓國網站被中國黑客攻擊,400多個與韓國明星相關的QQ群被“刷爆”,同時多個同韓國明星相關的百度貼吧遭到“爆吧”。據資深互聯網從業人員表示,天涯、貓撲、百度貼吧同時在線人數暴漲50%。
“6·9圣戰”源于部分網民對世博會韓國館發生踩踏事件暴露出的某些“哈韓族”惡劣言行的不滿。就此事的論戰由原先歌迷與主辦方之間的矛盾,轉向了愛國和民族尊嚴的討論,參與者除了事件當事人,原本不相干的網民也加入了這個已脫離事件本身的“愛國圣戰”中來。
二、“網絡圣戰”中的信息傳播特征
“網絡圣戰”是網絡群體性事件的一種形式,指的是在一定社會背景下形成的網民群體為了共同的目的,利用網絡大規模地發布和傳播某一信息,以制造輿論、發泄不滿。因其信息傳播的載體和參與的主體的不同,它與現實群體性事件有很大的不同,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1、群體極化嚴重
群體極化,是指群體的討論可以使群體中多數人同意的意見得到加強,使原來同意這一意見的人更相信意見的正確性。這樣,原先群體支持的意見,討論后會變得更被支持;而原先群體反對的意見,討論后反對的程度也更加強,最終使群體的意見出現極端化的傾向。
在網絡中,用戶傾向于鏈接、登陸與自己的價值觀相一致的網站、論壇、貼吧和QQ群。美國法學教授斯·桑斯坦在其所著的《網絡共和國:網絡社會中的民主問題》中說道,“志同道合的人在網上頻繁的溝通,但聽不到不同的看法。持續暴露于極端立場中,聽取這些人的意見,會讓人逐漸相信這個立場”。一方面,由于相對立的兩個立場中的群體缺乏除語言暴力以外的溝通,很容易導致群體本身視野的狹隘或者強化本身的信念、態度,出現群體極化的傾向,極端的聲音表達被無限放大。在這種情況下,原本中立的聲音在輿論中就顯得微乎其微,形成沉默的螺旋。另一方面,網絡的匿名性使得沒有人能知道數量龐大的互聯網用戶的真實身份,也沒有人能夠對如此多的網民追究責任,不論是法律責任還是道德責任,無需承擔任何不良后果的情況下,人們的行為就更容易走向極端。
回歸此事件,據當時鳳凰網調查顯示,約700多萬網友就此事件參與了投票,94%的網友認為該行為是愛國行為、1.8%的網友認為是炒作行為、4.2%的網友認為該行為和哈韓者沒有什么差別。在人人網的投票中,有86%網友對“圣戰”表示了強烈支持。
2、群體思維顯著
群體思維,是群體決策的一種現象,指的人們為了維護群體和睦而壓制異議。而群體思維的形成主要由以下幾個方面構成:
首先,集體無意識狀態的存在。瑞士心理學加榮格認為:“集體無意識指的是尤遺傳保留的無數同類型經驗在心里最深層幾點的人類普遍性精神。”集體無意識是群體行為發生時的基本心理狀態,也是構成群體的普遍性格特征的重要因素。在網絡中亦是如此,只要某件事情觸動了人們共同的社會準則或者牽動了網民的某種熱情,原來散落在各個角落的網民就會聚集在一起,形成網絡心理群體。 “6·9圣戰”中網民的愛國主義的熱情被迅速點燃,促成了網絡群體意識的形成。
其次,從眾壓力和對群體無懈可擊的錯覺。人們通常對自己所屬的群體表現得過分自信,以致常常被假象蒙蔽眼睛。而網絡中,從眾行為往往表現為通過言論來贏得同組成員的認可。社會學家對于從眾行為的研究顯示:群體的凝聚力、群體成員對于群體組織共同信念的認同度、群體規模大小與否對于成員追求群體認同的愿望強度具有重要的影響。在此次事件中,成千上萬人同時行動充分體現了這一特點,圍觀群眾受到轟轟烈烈“圣戰”之勢的感染而不由的參與到其中,追求價值認同。
第三,對某些群體的刻板印象。刻板印象是指按照性別、種族、年齡或職業等進行社會分類形成的關于某類人的固定印象,是關于特定群體的特征、屬性和行為的一組觀念或者說是對與一個社會群體及其成員相聯系的特征或屬性的認知表征。網民對與“哈韓族”的成見促成了此事的發生。““6·9圣戰”領導人莫離在回答“為何將Super junior的粉絲歸為‘腦殘’行列”時,說道:“他們不尊重我們的祖國,有一部分人還打武警,還有踩踏武警。他們為了看一場偶像的演唱會,會付出各種代價,用各種招數。SJ組合的成員曾說過,‘地震是很好笑的’。這樣面對中國的地震災害,導致了我們很憤怒。東方神起(韓國人氣組合)也曾在中國毆打過孕婦,但那些粉絲卻聲稱東方神起沒做錯,聲稱中國人民有劣根性,這是我們接受不了的。本身身在中國,那就是華夏兒女。身體里流淌的是華夏五千年的熱血,卻幫其他國家的人辱罵祖國,我們絕對不能認可。”
研究顯示,厭惡和反對的情感,如果發生在孤立的個體身上,沒有任何力量,若是群體中的個人,卻能變得勃然大怒。“圣戰”在數小時內便聚集幾十萬網友共同執行爆吧和聲討的行動足以說明群體思維的強大力量。“圣戰”二字更是顯示出參與行動狂熱性和煽動性。有些專家指出:“其實‘6·9圣戰’就是借愛國之名的新一輪網絡炒作事件。”作家韓寒也表示:“‘6·9圣戰’不過是一場大學生欺負初中生的事件。”極端的追星事件其實屢見不鮮,但這次卻能在網絡上引發數十萬人的“圣戰”可見網絡群體意識的力量。
3、去個性化和語言暴力
去個性化是指個人在群體壓力或群體意識影響下,會導致自我導向功能的削弱或責任感的喪失,產生一些個人單獨活動時是不會出現的話語和行為。去個性化的外在條件有兩個:一是身份的隱匿;二是責任的模糊化。正如法國社會學家勒龐在其《烏合之眾》一書中說道:“孤立的他可能是個有教養的人,但在群體中他卻變成了一個野蠻人——即一個行為受本能支配的動物。他表現得身不由己,殘暴而狂熱,也表現出原始人的熱情和英雄主義,和原始人更為相似的是,他甘心讓自己被各種言辭和形象所打動。”
與現實生活中去個性化所不同的是:現實群體條件下的匿名主要是通過隱去個體的身體特征來達到的,而網絡中則由于網絡本身去身體的特性,而通過隱去個體的姓名來實現;現實群體條件下個體往往由于責任的模糊性和分散性感到責任的消失,網絡中卻是由于匿名帶來的責任無法落實而給個體以責任消失感。
由于“去個性化”導致網絡群體的行為常表現出非理性的狀態。僅僅是一場因組織不力導致的秩序混亂事件,卻在網上被人打上了愛國的旗幟,引發網絡上的混亂。韓國明星及其中國粉絲被貼上“棒子”、“腦殘”的標簽。各種惡語相向的文字刻薄、惡毒甚至殘忍,已經超出了對于這些事件正常的評論范圍,不斷對事件當事人進行人身攻擊,惡意詆毀,更將這種討伐從虛擬網絡世界轉移到現實社會中,對某些粉絲進行“人肉搜索”,將其真實身份、姓名、照片、生活細節等個人隱私公布于眾。
4、樸素的正義感、泛政治化思維與權利意識
就參與動機而言,網絡群體性事件與現實中的發泄型群體事件有相似之處。絕大多數參與者與原事件并沒有直接的利害關系。他們之所以參與進來,完全是源于道德沖擊,源于樸素的正義感。社會學家拉德克里夫·布朗曾說:“人類有序的社會生活依賴于社會成員頭腦中某些情感的存在,這些情感制約著社會成員相互發生關系時產生的行為。”在網絡群體事件中,主體接受了精神的洗禮,從而獲得了充盈的真實,群體也借此鞏固了內在秩序,實現了凝聚和整合。
依照網絡群體性事件的性質,大致可以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集中于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的認同和表達;另一種是基于社會不平等與階級分配不均的爭論、行動。本文所討論的“圣戰”顯然是前者。
5、明顯的群體娛樂特征
在網絡群體事件中,常常帶有群體娛樂的特征。在“6·9圣戰”官網上,赫然寫著:腦殘不死,圣戰不息。類似的“網絡圣戰”雖然披著“愛國”的外衣,但實質上又帶有強烈的群體娛樂的特質。它最終演變成與組織者初衷完全背離的集體狂歡,甚至是被某些利益集團操縱的網絡營銷,大批的網友在幕后推手的操縱下“被憤怒”、“被愛國”,這與原本追求的公民言論表達相距甚遠,倒像是一場跌宕起伏的滑稽劇。
結語
近年來,類似“11·28圣戰”、“6·9圣戰”、“李宇春吧被爆”等以影響網絡正常運行秩序為主要方式的網絡“圣戰”常有發生。“網絡圣戰”的日益增多和影響力日趨擴大給社會穩定帶來了極大的沖擊和挑戰,其中的網絡暴力也不斷叢生。面對由此給社會帶來的嚴峻考驗,除了利用技術手段,還應該采取積極措施應對此類事件。網絡監管部門應時刻關注社區論壇動態、了解輿論動向,盡量將一些可能激化的矛盾解決在萌芽狀態。就傳統媒體而言,及時介入事態的調查,還原事實的真相也是不可缺的,以免主流媒介缺位造成的信息空缺、謠言四起。而對于每一個網民來說,也應用理性的態度判斷網絡上的言論、事件,提升自身的網絡道德,避免成為網絡推手操縱的“棋子”。
參考文獻
①曾慶香、李蔚:《群體性事件:信息傳播與政府應對》,中國書籍出版社.2010
②宋嘉庚、徐晨霞,《淺析網絡非理性輿論的成因及對策》,《新聞世界》,2010(1)
③蔣郁青,《百度貼吧中的群體沖突分析》,《新聞世界》,2010 (2 )
④毛新青,《虛擬世界的儀式狂歡——網絡突發事件中的個體自由與社會控制》,《山東社會科學》,2011(8)
(作者:中國傳媒大學電視與新聞學院新聞系研究生)
責編:姚少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