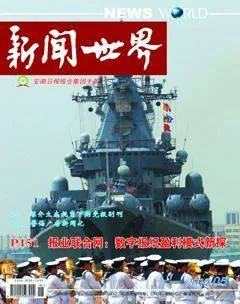《時務報》和它的讀者
【摘 要】本文運用“使用與滿足”理論分析了《時務報》的讀者構成及與其有關的閱讀活動,認為讀者在《時務報》的發展過程中扮演著和其主辦者同樣重要的角色。
【關鍵詞】使用與滿足 《時務報》 讀者
使用與滿足理論集中關注個人如何使用大眾傳播媒介、人們使用媒介的方式與他們從中尋求到的滿足之間的關系,考察了大眾傳播給人們帶來的心理和行為上的效用。傳播學者伊萊休·卡茨的使用與滿足模式指出,具有社會和心理根源的需求,會引起人們對大眾媒介或其他信源的期望,這些期望導致媒介揭露的不同形式,最后會產生需求滿足的效果,以及其他(往往是非有意的)結果。①在使用與滿足理論看來,受眾是大眾傳播內容的積極解讀者,受眾通過選擇性接觸、選擇性理解、選擇性記憶等一系列心理上的自我選擇過程,在不同程度上完成著自我認知層面、情感層面、態度層面乃至行為層面上的加強或是轉變。作為十九世紀末中國維新派最重要、影響最大的機關報《時務報》,高舉變法圖存的大旗,態度鮮明,議論透徹,且文筆大多清新流暢,富有激情。鼎盛時期的《時務報》曾經“一紙風靡海內,數月之間,銷行至萬余份,為中國有報以來所未有,舉國趨之,如飲狂泉。”②這足以說明其讀者群之龐大,影響之深遠。
1896年8月創刊于上海的《時務報》,初創時每期銷售量即達到4000份左右,半年后增至7000份,一年后達到13000千份,最高銷到17000多份,創造了當時報刊的最高發行紀錄。③如果以每份平均十人閱讀,那么該報擁有的讀者至少四萬人以上,最高時可達到十幾萬人。把《時務報》與同時期的其它報刊的發行量相對照,更可看出《時務報》是怎樣的一紙風行。“《國聞日報》現在每天銷一千五百張”。《國聞匯編》“每期僅銷至五六百份”。就連當時影響比較大的廣學會所辦的《萬國公報》從1896到1897年的銷售數量也僅為《時務報》的四分之一左右。“貴報風行之廣且速,足見中國風氣之已有轉機,亦諸公提倡之力也”。可見,《時務報》在當時非常的暢銷,創造了當時中國新聞出版史上的奇跡。
《時務報》的風靡一時,在筆者看來,首先應該歸功于其言論。因為人們接觸傳媒的目的是為了滿足他們的特定需求。正如鄒代鈞所說:“《時務報》能暢銷,‘雖賴汪康年之擘劃周詳,亦賴卓如大筆如椽,足以震動一時耳’。”④包天笑在《釧影樓回憶錄》中也追敘說:“《時務報》在上海出版了,這好像是開了一個大炮,驚醒了許多人的迷夢。……尤其像我們那樣的青年,最喜歡讀梁啟超那樣通暢的文章。……不但是梁啟超的文章寫得好,還好像是他所說的話,就是我們蘊藏在心中所欲說的一般……一班青年學子,對于《時務報》上一言一詞,都奉為圭皋。”⑤盛況空前的《時務報》熱是一個封建思想壟斷的社會突然遭到巨大異端思想沖擊所產生的必然反應。梁啟超及其同仁在《時務報》上發表的一系列要求變革、要求變法的文章順應了時代的要求,滿足了讀者的心理期望,這是《時務報》發展的關鍵。
《時務報》能取得如此驕人的業績,與內容有關,但也離不開報館的各項發行措施,這在某種程度上增大了讀者媒介接觸的可能性。汪康年的促銷手段有二:一是通過各種關系請求地方大吏發行公文,以行政命令的形式,自上而下提倡閱讀《時務報》,并由官方負責報貲;二是在基層廣大讀者中間做踏實的推銷工作。據告白《時務報》第26冊登載,派報處(代售處),計國內外63縣市,共95處,到光緒二十三年(1897)七月間,代售處增為70縣市,109處。遍布大小城鎮的銷售網絡的建立,為提高《時務報》的銷量奠定了基礎,其讀者遍布全國各地乃至國外,傳播范圍極廣。除此之外,作為一份民辦報紙,《時務報》的成就與時務報館的成功經營也是分不開的。《時務報》出版以后,銷量日升,報貲已代替捐款,成為報館主要收入來源,報館資金運作逐漸走向正常化。
《時務報》是一張應時代要求而誕生的報紙,對社會造成了極大的沖擊,來自各個階層的人們,出于不同的目的,都匯到了《時務報》的旗下。呼吁變法的士大夫是報紙的當然讀者;商人們感受到了時代的潮流,也購買報紙,就連那些矢志場屋、頭腦陳舊的舊士子,受風氣所趨,竟然也將《時務報》作為科舉考試的參考書,仔細研讀起來。⑥從報刊所登載的捐款者名單上我們可以略窺一二。從總督、學政等高官大員到底層知識分子如秀才監生,從汪康年師友到與報館諸人少有往來或陌不相識的讀者,涵蓋了上中下諸階層諸知識群體,顯示出《時務報》極強的社會滲透力。吳炳覺得《時務報》“拓我聞見”,雖與彼方全不相識,卻“愿捐英洋一百元,以期擴充此報。……此上《時務報》館主人青察”。又如,欽使呂海寰“外英洋伍拾元”。另外,從《時務報》的“口碑”中我們亦可看出其讀者的多樣性與廣泛性。湖廣總督張之洞曾稱贊《時務報》“識見正大,議論切要,足以增廣見聞,激發志氣……實為中國創始第一種有益之報”。廣東舉人葉爾街說:“伏讀報章,其體例之雅馴,議論之切實,采摭之宏富,抉擇之謹嚴,洵為毫發無憾,足與倫敦《泰晤士報》相頡頏。”上海學生王鵬飛評價道:“《時務報》中外畢備,巨細兼收,辟四萬萬人之心思,通歐亞美澳之風氣,至矣至矣。”讀者是報紙生存發展的原動力,而他們一旦獲得了“媒介滿足”,報紙在他們的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就會越重要,對他們的影響力也就越大,最終形成“媒介依賴”。這樣一來,報紙的“遲滯”就會惹來讀者的抱怨:潘祖蔭“《時務報》第29冊遲了三、四個月”,毛慈望“如能設法求速,則更善矣”,王延齡、江瀚等也曾致函汪康年談到此事。可以說,讀者通過媒介來理解社會的同時,媒介也會塑造讀者的期望。至此,依賴于《時務報》得以聯系的上至帝王督撫下至紳士甚至布衣在內的十分龐雜的社會群體逐漸形成。
讀者閱讀《時務報》涉及的活動主要圍繞 “批評建議”展開。《時務報》欄目豐富,大力宣傳維新變法,論說部分尤其鼓動人心。汪康年與梁啟超所發表的大部分論說,及其他作者的一些論說,都引發了讀者的感觸。如對于汪康年發表的《論中國參用民權之利益》,吳品珩就褒揚道“昨登參用民權一篇,尤為透徹,痛下針砭,佩服佩服。”。除此之外,讀者對于《時務報》的批評建議還包括誤字太多、紙張更換、譯文語言等多方面。吳品珩指出上諭內有誤字,如:第七本所登碭山縣知縣守最之“最”誤“卓”字,知縣羅宗美落一“羅”字,李紱藻轉補翰讀學,“李紱”二字誤“幬繡”二字,諸如此類。針對印刷紙張的質量問題,一位署名為“留心時事人”的讀者來信建議改用紙張,認為“此紙質極粗劣,一經潮濕,即易腐朽,這不如本國紙之堅潔。”“請貴館以后將此紙永遠摒棄勿用”。《時務報》中的譯報,也格外受讀者青睞,意見也不少。讀者汪立元就認為譯報話太繁,指出“不甚愿看”,建議“譯報照西文,自當就原文譯出,能再刪潤,則辭簡意明矣。”讀者對媒介提供的內容進行有選擇性的接受過程顯示了讀者的能動性。其實早在《時務報》籌建之初,就引起了痛感國事日非和要求維新變法的有識之士的強烈關注,之后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呵護它成長的隊伍中來。從《時務報》被閱讀后的這些反饋信息中,我們可以感覺到讀者們的真誠之心,他們或擔憂或非議,但無非都是希望這份承載他們救國夢的報紙能夠良好生存發展下去,建構起真正完善的公共輿論空間。
汪康年等人創辦的《時務報》儼然已成為民眾的精神食糧,時務報館也成為維新運動的資訊中心和服務中心。《時務報》所傳播的維新思想和所倡導的維新活動使舉國上下頓時間一片沸騰,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民族覺醒,各種維新團體如雨后春筍般在各地破土而出,維新事業轟轟烈烈的開展起來。例如《時務報》的告白欄常常大篇幅登載不纏足會董事和捐款名單,捐款數目雖然經常低至一二元,但捐款人數眾多,反映不纏足運動受到人們的踴躍支持。又如中國女學堂正式開學之際,初時學額暫定四十名,結果“報名者爭先恐后,幾數倍于定額,咸以不得入門為憾”。⑦一些知識分子也不再沉迷于功名,在調整自己行為的同時,逐漸意識到“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他們開始走出書齋,撰述論說、譯書,宣傳新思想;還有一些人開始辦學社、創報刊、開公司等,杭州府署的太守林迪臣就是其中一位。在致函汪康年的信中他便委托求助:“議欲招集商人創設公司,將土貨運往外洋推廣銷路,托為籌劃辦法”。可見,《時務報》給人們帶來了心理和行為上的效用。讀者的思想得到了解放,視野更加開闊,變法的態度愈加的堅決,并以實際行動參與到維新運動中來。
總之,讀者在《時務報》的發展過程中扮演著和其主辦者同樣重要的角色。《時務報》的創辦“滿足”了讀者的需求,《時務報》的健康發展離不開讀者的持續關注和呵護。特別是讀者的積極反饋有助于《時務報》的主辦者調整傳播的內容或方式,優化其傳播效果。《時務報》出版的目標是為了影響它的千千萬萬的讀者,使他們支持變法并參與維新運動,好為政治改革造就人才并搭建起群眾基礎。《時務報》能作用于讀者在認知、態度及行為上的有益變化是其真正意義價值之所在。
參考文獻
①董璐:《傳播學核心理論與概念》,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175
②梁啟超:《本館第一百冊祝辭并論報館之責任及本館之經歷》,《清議報》第100冊,1901年12月21日
③方漢奇:《中國近代報刊史》(上),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83
④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265
⑤包天笑:《釧影樓回憶錄》,香港大華出版社,1971:150-151
⑥廖梅:《汪康年:從民權論到文化保守主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66-67
⑦湯志鈞:《近代上海大事記》,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9:525
(作者:山東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2010級新聞學碩士)
責編:姚少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