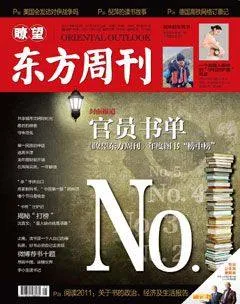微博薦書十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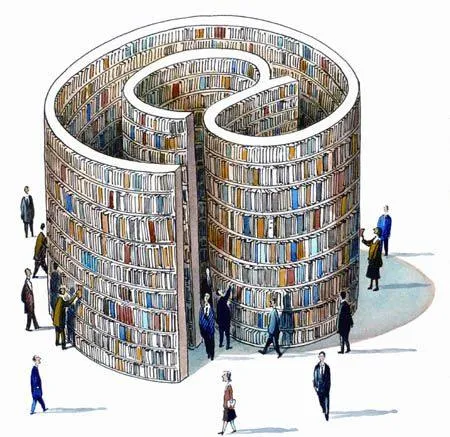
我們并不知道自己有哪方面的需求,直到喬布斯打開亮麗的屏幕指給我們看,于是,我們的需求便被黏合于其上,他靠這個賺我們的錢。
微博也是一個這樣被憑空創造出來的空間。
每一個賬號背后都是一個活生生的人,實名制后,這種對應會更加明確。這是微博上一切有價值的活動的原點。
他(她)可以是意見的發表者,可以是商品的消費者,當然,也可以是讀者,一個可以向其薦書的讀者。
微博薦書忙
新浪微博、騰訊微博、網易微博都有專門的薦書賬戶存在。優米薦書、廣漢薦書、末末薦書、方姐薦書、浦東圖書館讀者薦書、大學生村官薦書、薦書房等,以“薦書”為關鍵字搜索新浪微博用戶,得到賬戶50個,其中9個帶V用戶。
微博除了賬號薦書,還有活動薦書,下面是來自新浪微博的一組數據:
#2011讀過的好書#,該話題共有“764572”條相關微博;
#推薦一本好書#,該話題共有“195360”條相關微博;
#好書榜#,該話題共有“52888”條相關微博。
還有#曬曬你在旅途中最愛看的書#、#2011曬書單-話讀書#、#拍下你最近看的書#等活動。
而在傳統公共書榜的形成中,也有微博參與:
新浪讀書頻道、深圳好書榜等都將微博嵌入好書榜的評選流程,最終形成的公共書榜中就有了微博的因子。借助新浪微博,新浪讀書頻道每月公布的榜單,微博的轉發數達到千條以上,半年榜揭曉,單條微博轉發就超過61000條。
誰在微博上薦書
是誰在微博上薦書?
一是書商。在圖書出版市場上,涌動著一股由微博主導和推動的閱讀潮流。微博不再被傳統出版商視為可進可不進的領域,從 2010年起,國內出版人集中開微博,并有專人料理微博,每天平均發布20至30條最新的微博,回復200至300條評論。在新浪微博“文學.出版”板塊,駐扎著中國主流的出版單位、圖書公司,及出版人,都通過微博或介紹旗下新書,或談論出版界熱點現象及事件。
中信出版社總編輯@潘岳 有89萬粉絲,熱衷于在微博中與粉絲頻繁互動,中信出版、中信出版第一分社、中信出版第二分社、中信出版第三分社、精致時光ITIME(中信出版旗下雜志)、中信出版社副總編、中信出版社新媒體總經理等也都加入微群,形成一個“中信出版系”的微博方陣。
許多圖書企業鼓勵全部員工開通微博。編輯開通微博,可將作者、發行信息等周轉給書店;書店店員開通微博,可將與讀者的互動信息周轉給出版社各編室、乃至圖書的作者。
二是圖書編輯。出版社凡有新書推介,微博方陣中的編輯和宣傳人員往往會大力轉發相關信息,采取群狼戰術,這類微博比較熱鬧的有@上海譯文、@中華書局、@新星出版社、@廣西師大出版社理想國,等。其中一些編輯,會在微博上努力搜索自己編的書,凡是提到自己編的書的微博,就轉發過來。
圖書編輯@陳笑黎 編了一本《腸子》,圍繞著這本書,他除了轉發,還策劃了許多活動,像曬《觀音山》電影票送《腸子》等。電子月刊《綠茶書情》的作者@綠茶 就此編了一個段子:“@陳笑黎的微博打一菜名- - -炒腸子”。
@綠茶本身就是書單控,其微博就是各種圖書榜單的索引:“羊城晚報2011年度贊書榜、彈書榜”、“美國舊金山紀事報2011年度十大好書”、“《經濟學家》雜志2011年度最佳傳記”,等等,將角角落落里的書榜一網打盡。他還發起 #2011私人閱讀書單#,不僅草根賬號應者云集,還吸引了@朱學東 等“大賬號”。
三是圖書作者。有人戲說,一些作者的微博簡直成了圖書售后服務中心,@作家岳南不僅介紹圍繞其所著的《南渡北歸》等大師遠去系列的售書、活動,還提供著與讀者分享見解等“增值服務”;@作家金滿樓的《辛亥殘夢》上市后,不定時地在微博上“匯報”其售賣情況,或被某單位指定為推薦讀物等消息。余秋雨專門為其新書《中華文化的47堂課》開通了微博,發了一條出書預告、一條活動預告,兩條微博就吸引了4萬粉絲。
第四是“V字特攻隊”。新浪微博名流云集,加V是他們的標志。在這個看似平等自由的舞臺上,不平等才是真實的微博,只不過共處于這個場域中,又有在評論中罵大佬的可能,給了網友虛幻的平等感。
加V名人在微博薦書上也存在著天然的話語權優勢,乃至可以“提升”圖書品位,讀者會將偶像的一些優點投射到其推薦的書上。因此,一些圖書公關公司為“大賬號”微博用戶開出了不菲的價格,有的轉發一次甚至有幾萬元的酬勞。而出版社對于通過人情請來的名人推薦腰封,“答謝費”通常在500至1000元之間。
不管怎樣,名人薦書正從“腰封”向“圍脖”進化,格調從腰到脖同步升高,雖然兩者同是精煉的微博體,但是相比“腰封”上常常顯得不那么著邊際的推薦語,微博上的薦書語顯得坦誠不少,至少豆瓣上的“恨腰封”小組找過微博上“虛擬腰封”的麻煩。
第五是圖書館。新浪微博中入駐的圖書館超過500家,其中既有實體圖書館的官方微博,又有虛擬的以“圖書館”稱謂的圖書組織。研究微博在圖書情報學中的地位、作用,成為一門“顯學”,論文連篇累牘。這些圖書館微博發布的內容以新書推薦、圖書活動預告等為主,并通過與微博用戶的交流、互動,吸引更多的“粉絲”讀者。
六是“草根”。普通讀者出于純個人閱讀興趣的推薦或渴望得到認同的推薦,由于往往是他們真正讀過自己推薦的書,加上以草根的語言、智慧、幽默所進行的推介,容易打消讀者對廣告的心理防范,反而更易形成效果不錯的傳播。
第七是推銷特定價值觀的機構。日本僑報社在該社注冊的新浪、騰訊、網易、鳳凰和人民微博上都開設了“每日一書”專欄,系統介紹有關中日關系的書籍。
第八,B2C中的B。@快書包 在微博上薦書,是因為不少人直接在微博上下單。目前“快書包”有三到四成的業務是來自新浪微博的,更有5%左右的業務是在新浪微博上直接下單的。
薦書和社交
在微博上薦書,主要出于三種需要:社交、推銷、客服。
其中,社交最符合微博這款社會化媒體的本意,微博也被稱為“社交媒體”。推銷、客服的需要則屬于純商業范疇。
閱讀的社會化屬性是濃厚的。當你看到一本好書的時候,常想分享給更多的人。在微博上的薦書許多帶有明顯的社交色彩,無論自薦還是代友推薦,一本好書,它的信息很快能夠傳達到你的朋友圈,以及和你愛好相同的人中。“讀一百本好書,認識一百個好友,去一百個好地方”可以在微博上一次性實現。
名人圈子里這種色彩尤甚。名人出書,更容易得到其他名人的轉發,李開復出了本《微博:改變一切》,就有學者劉墉、詩人沈浩波在微博“抬轎子”。明白這一點,很多時候,為社交而進行的微博圖書推薦,不必太過當真,而推薦的真心度、應酬度也能從推薦的措辭中看出來。
基于新浪微博開發的社交閱讀工具切中了普通人在這方面的需要,iPhone的應用程序“微書架”是其中之一。用戶在“微書架”上可以微關注、擁有“微粉絲”,構筑一個社區,將自己的書架、圖書與朋友分享,比如你最近上傳了什么書到書架、添加了哪本書到自己的書單、查詢自己好友的書架、查看一本書有多少人讀過,此書又有多少人想買或者想讀,當這種分享消息更加日常化的時候,用戶會可能有機會因為圖書而結交到一些朋友。
還有機構社交。杭州市委組織部微博就與杭州圖書館建立互通,他們希望在杭州圖書館微博的“圖書推薦”上獲取適合向他們的博友推薦的書目。上海閔行區圖書館通過微博,成功聯系到譯文出版社、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等出版社為圖書館提供當月最新的出版信息,以方便圖書館的工作。
微博薦書本身也迎合了現代人信息焦慮的需求,在短時間內迅速了解自己身邊及整個世界正在發生的事情,讓人們得到了一種信息滿足。從文本上,中國人習慣用三言兩語甚至只言片語來表達自己的看法與觀點,甚至對某人某事的評價也是如此。微博薦書語正切合這種訴求。一位白領表示:“微博讓我有一種節奏感,而且可以從別人的口碑中得到自己的結論。我上次在機場等飛機的時候在微博上發現有人推薦的一本書,就在旁邊的機場書店,我去找來看看,果真寫得很好。”
在陳坤的微博上,一來就拋出了“什么是真實”的議題,隨后,陳坤又請大家推薦好書,他還推薦了自己最近在看的書《一只牧羊的金剛經筆記》、《圣嚴法師講金剛經》、《你可以不怕死》。
突破傳統營銷的局限
微博上的任何人可以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發布任何事情。微博薦書與媒體書榜的一大區別,是沒有出版時間的限制、沒有出版地的限制,一些陳年舊書會反復在薦書的微博中出現,而書榜常常針對的是最近一段時期出版的圖書。
針對抹平時空邊界這一特點,一些賣書微博賬號按照早、中、晚不同的時間段發布不同層次內容的微博,突破了傳統營銷方式的單一和局限。
《大國海盜》、《親愛的甜橙樹》、《流螢谷》、《太后與我》……這些難登公共媒體書榜的書頻現于私人薦書的微博中。而除非有跟此書相關的大事件發生,否則,這些書一般不會形成熱點話題,沒有集中效應,它們也便很難進入公共媒體榜單。
有人熱衷于系列推薦,“女孩子必讀的十本書”、“推薦十本經典育兒書”,@當時我就震驚了 一下子推薦了香港中文大學書單上的87本書。這仍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書榜。
據一個法國人統計,人的一生仔細閱讀2500本書就非常了不起了。面對微博上的浩瀚洶涌的書海,你才感到碎片化的不是微博,而是一個人的人生,書多如許,能取幾瓢飲?
私人薦書幾種
小S在微博推薦了一本書,《相助》(英文版名《The help》,臺灣版名《姐妹》),是小S在“康熙來了”化妝間看的,小S的姐妹范瑋琪、張惠妹也都在自己微博里推薦了這本書。這種閨密式的情趣薦書在微博上占有相當比重。
@雷軍 在微博上推薦了特勞特的新書《與眾不同》,并稱“當年特勞特的《定位》是我們的營銷教材,每個人都需要精讀。”這本書正好說了他的經營理念,既是其閱世閱己的階段性總結,也是在自我宣傳、標榜。
薦書一般是圍繞自己熟悉的領域。@譚飛的《影視界的知道分子》剛在微博上宣布,@馮小剛、@王中磊、@姚晨、@陸毅、@趙薇、@鄭淵潔等“大賬號”紛紛轉發,陣容如此豪華強大,在微博史上還是第一次,堪稱最牛微博新書推薦。
愛心薦書也是一個熱點。《爸爸愛喜禾》得到了@胡淑芬、@劉儀偉的推薦,崔永元說:“喜禾小友:你是我交的唯一的一個得‘自閉癥’的朋友,可能我也是你認識的唯一的一個有‘抑郁癥’的叔叔。咱倆,天天,病并快樂著。”
怎樣薦書
“當時裕子穿著和服,姿態美妙,……酒席進行到最熱鬧的時候,燈突然熄滅,……”這是文匯出版社為渡邊淳一的《何處是歸程》所做的誘導性預覽,以故意“走光”的方式薦書。
“他14歲娶了19歲老婆;24歲時娶23歲的妓女為妾;34歲時娶16歲的小蘿莉;40歲時為了政治利益,搞定了30歲的御姐,并聲稱此生只有御姐一人。”此人是誰?蔣介石!這是《蔣介石自述》一書在微博上的宣傳語之一。
大部分薦書微博使用的依然是傳統的推介方式:把媒體報道轉載到微博上,讓信息流通起來;在微博上發布新書的精彩內容,通過這種碎片式傳播引起讀者好奇;轉載讀者對圖書的評價,與讀者進行有效溝通,積累固定的讀者群。
但是,搏出位的、耍花樣的越來越多。
新書發布會搬到微博、推薦名家名作、組織書友會、就出版業熱點現象與事件發表觀點……一個名為《走吧,張小硯》的視頻在微博上也很引人關注,而這不過是一本同名新書的廣告。制作水平非常精良,完全是按電影大片的路數來拍攝。此書,3個月不到賣了10萬冊。
營銷進階
對微博的研究,主要沿著兩個視角切入,一是新聞傳播學,二是電子商務。前者因為新媒體演進的一日千里,常有“追不上”之感,后者由于與賺現金結合得緊密,動力也足,反而更加前沿。
將“粉絲”轉化為實際購買者是電商要解決的一個核心議題。圍繞這個問題,進階很快。
最初,許多圖書人并沒有抓住本質,哪兒火就往哪兒撲。在文本上,也非常“土”,發個圖書鏈接,發布個信息,沿襲了傳統營銷中企業主導這個舊做法,而沒搞清楚什么是“客戶主導”。
無數次的零轉發、零評論,讓一些人痛定思痛,改進文本、溝通互動,又整合了視頻、音樂,采取有獎轉發等等活動。
事件營銷、名人效應和人物打造是現階段漸顯成熟的微博圖書營銷方式。
最高境界則是口碑營銷,由讀者發表的圖書微博評論,雖然語言簡單,帶有明顯的個人感情色彩,可往往能影響微博上同類讀者的取向,對圖書的宣傳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目前,圖書領域中還沒有微博營銷產生轟動效應的案例出現。但是,框架和模式越來越明確,也形成了“內容為王”等業界的共識。
微博薦書的兩種效果
相對而言,小眾圖書是微博薦書的最大受益者。經典而大眾的書,比如《百年孤獨》,反而鮮有人在微博上推薦。
@綠茶 評論@阿乙的《鳥,看見我了》、@赳赳的《北京的腔調》和@葉三的《九萬字》,“這三位典型大齡文藝男女青年的書,要在以前,一萬冊都很難賣出去,而借助微博,在自己和朋友們的合力忽悠下,現在每本銷量都在三萬以上,都步入了‘三萬俱樂部’行列。”
類似例子還有@蔣一談的《魯迅的胡子》、@瓦當的《多情犯》、@楊葵的《百家姓》、@五岳散人的《亂翻書》、@韓皓月的《愛如病毒,需要潛伏》等等。“從千篇一律的排行榜上,很難看到以上這些小眾書的影子,因為排行榜就不是為這些書準備的。但是,作為排行榜之外的這些書,我們很高興有新的載體能供提升它們的受眾。” @綠茶說。
不過,蔡康永有不同的發現:在電視節目中推薦書,當期的收視率就會很低,在微博里推薦一本書,這條微博的轉發率也會很少。
微博成書
從《尸子》到微博書,中國人的話語方式轉過了一個輪回。
微博的勃興與信息時代資源密集同時呈現出碎片化的趨勢有關,而在文本上又與中國傳統的批評鑒賞判斷論贊的語言形式“撞衫”。
《尸子》是先秦諸子著作中除《論語》之外最接近微博體的,書中各段獨立成篇,既有治國大道,也有生活竅門,時不時還穿插一些冷笑話。
現代版的《尸子》也便應運而生。余華集結了他所有微博和部分博客的數字版圖書《余華@》,無紙質版。這一出版創舉的背后,有著紅旗出版社的影子。
微博成書正成為一種流行,《大頭條》、《發財說史》等都是從線上走到線下。除了小說之外,許多適合摘錄、切割、改編、傳播評論的雜文、詩歌等都有微博版圖書。
而以目前看來,這類圖書并不暢銷、更無一能上榜,雖然它們在微博上面推薦得很熱鬧。
微博薦書的功與過
什么都在終結。
海德格爾提出“歷史的終結”,丹托提出“藝術的終結”,微博,將是“傳媒的終結”,還是“圖書的終結”?
大量閱讀群體被功能強大的網絡所吸引,地鐵人群讀屏多、讀報少。然而,微博又通過薦書等方式以淺閱讀的方式來帶動著深度閱讀,微博薦書語成為書的導讀,那么,微博對于謀殺現代人的閱讀,是功?是過?
關鍵是“物物而不物于物”,要控制微博而不能讓微博控制你。
微博只是一種工具,不是紙書的殺手,而是紙書可用的一把刀。可以互殺、可以自殺,就看怎么用了。
技術即思想,工具即理性。我們既要以敬畏之心對待的“技術的擴散”理論,又要看到一路走來,人還是那些人,工具則隨用隨扔,并不留戀。隨著下一種新媒體的登場,無數的喃喃自語會像泡沫一樣,消失得無影無蹤。
微博很強大,又很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