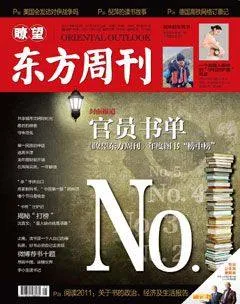逃離平津
這是一個注定要寫入中國乃至世界戰爭史的祭日。
1937年7月7日,日本軍隊經過長期密謀策劃,終于采取了武力占領平津,繼而征服整個華北和中國的侵略行動。“盧溝橋事變”爆發,日本全面侵華戰爭由此開始,中國軍民八年抗戰的悲壯序幕隨之拉開。
在隆隆炮火和日機的轟鳴聲中,平津地區人心惶惶。以北大、清華、南開、燕京等著名高校為代表的教育界,同樣呈現出一派驚恐、慌亂之象,一些人悄然打點行裝,拖兒帶女,呼爹喊娘,隨著滾滾人流,頂著盛夏酷暑和彌漫的煙塵,紛紛向城外擁去。來不及逃亡或因特別情形而不能逃亡的各色人等,則在恐懼與焦灼的煎熬中苦苦等待與觀望。
是時,正在九江岸邊廬山的蔣介石分別邀請各界人士火速趕往廬山牯嶺,頻頻舉行談話會及國防參議會,共商救國圖存大計。 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文學院院長胡適、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天津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所長傅斯年等一批學界要人也應邀出席。
平津兩地各高校正逢暑期,被邀請到廬山參加會議的各大學校長、院長與著名教授,以及部分在外地的教職員工,由于遠離平津,對戰事真相難辨真偽,而混亂的時局伴著恐怖的謠言,如同風中野火在中國大地上四處流竄飛騰。
面對來自四面八方的消息,在廬山的蔣、梅、張等三校校長坐臥不安,憂心如焚,其情狀正如梅貽琦所言:“實屬腸一回而九折”。
7月29日晨,天津守軍紛紛撤退,日軍開始反攻,地處城西的天津南開大學突然遭到日軍炮火猛烈轟炸,校園內的木齋圖書館、秀山堂、思源堂和教師宿舍區均被日軍炮彈擊中,頓時樓塌屋倒,giIicDeqsvFEyJAUI6mAGw==幾十萬冊寶貴圖書資料灰飛煙滅。緊接著,日軍派大股騎兵和汽車數輛,滿載煤油闖入校園,四處投彈、縱火焚燒。這所經過千辛萬苦發展起來的中國當時最為出色的私立大學,在戰火中化為灰燼。
時在南京的張伯苓聞訊,當場昏厥,爾后老淚縱橫。當天下午,張伯苓強忍劇痛發表談話:“敵人此次轟炸南開,被毀者為南開之物質,而南開之精神,將因此挫折而愈奮勵。”
7月31日, 蔣介石約見張伯苓,頗為悲壯地表示“南開為中國而犧牲,有中國即有南開”。
蔣介石與張伯苓的談話,給茫然四顧的平津教育界注入了一支強心劑,由此增添了一份慷慨悲歌之氣。由廬山轉入南京繼續參與國事討論的北大、清華、南開三校校長及胡適、傅期年等學界名流,日夜奔走呼號,與國民政府反復商討如何安全撤退和安置各校師生。一時,南京與平津高校間密電頻傳,共同為之出謀劃策。
8月中旬,傅斯年在同北大、清華、南開等三所大學校長及學界名流反復商討后,力主將北大、清華和南開等三校師生撤出平津,在相對安全的湖南長沙組建臨時大學,這一決定得到了南京國民政府的同意。9月10日,國民政府教育部發出第16696號令,宣布由北大、清華、南開三校校長蔣夢麟、梅貽琦、張伯苓等三人為長沙臨時大學籌備委會常務委員,籌委會主席由教育部部長王世杰親自擔任。
9月13日,籌備委員會召開了第一次會議,確定租賃地處長沙市韭菜園原美國教會創辦的圣經書院作為臨時校舍。十五天后,正式啟用國立長沙臨時大學關防,校務由三校校長及主任秘書所組織的常務委員會負責。
此前,由教育部發出的撤退命令已在平津三校師生中秘密傳達,翹首以盼的北大、清華、南開三校教職員工和學生們接到口頭傳達的通知后,紛紛設法奪路出城,輾轉趕赴湖南長沙---中國現代歷史上最為悲壯的一次文化知識分子大撤退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