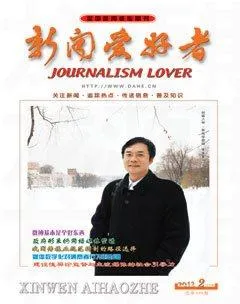選擇性報道視閾下的媒體輿論導向
【摘要】媒體在報道新聞事件時,會根據事件的新聞價值進行選擇性報道。基于受眾需求、價值判斷、眼球經濟等原因的選擇性報道往往忽視了媒體的社會責任,造成不良的社會影響。本文以最近媒體頻繁曝光的一系列“老人倒地”事件為例,分析了媒體選擇性報道機制的動因及產生的輿論影響,以發揮選擇性報道在輿論引導中的積極作用。
【關鍵詞】選擇性報道;社會責任;輿論導向
一、事件回放與選題背景分析
2011年8月,天津“許云鶴案”塵埃落定,當事人“好心反被誣”引發了輿論關注。此后,媒體對各地“老人倒地”事件的關注度持續升溫:2011年8月28日,武漢市電動車主胡師傅扶起一名摔倒的八旬婆婆時,反被婆婆稱是被他的電動車撞倒;2011年8月30日,《揚子晚報》報道,江蘇南通大巴司機攙扶摔倒的老太太,卻被誣為肇事者,幸虧有大巴上的攝像頭還原了事實真相;此后,在9月2日的《楚天都市報》、9月7日的《齊魯晚報》等媒體上又相繼報道了武漢、濟南各地的類似“老人倒地”事件……
一系列“老人倒地”事件的連續報道,引發了社會公眾普遍的“救助恐慌癥”,甚至產生了社會道德滑坡的論調。“老人倒地”事件的井噴式出現,與媒體的選擇性報道行為不無關系。媒體作為社會環境的“瞭望哨”,堅持客觀、全面、平衡的報道是媒體所肩負的社會責任得以實現的基礎。但是,在外部壓力和事實的新聞價值的取舍中,選擇性報道已經成為媒體的一致趨向,導致輿論導向的失衡。因此,在新聞操作中掌握選擇性報道的規律,從而承擔起媒體引導輿論的社會責任,消除對輿論的負面影響,是我們研究“老人倒地”事件的意義所在。
二、選擇性報道行為的動因分析
(一)媒體商業化:選擇性報道行為的外部誘因
選擇性報道來源于媒體記者、編輯對信息的選擇性關注、取舍,與新聞報道的客觀、全面要求并不沖突。在新聞操作中,記者、編輯也都認同客觀、全面、公正地記錄事實是媒體應盡之責。事實上,媒體不可能對所有的信息做到全盤記錄,媒體的選擇性報道是發揮把關人職能的結果。但是在日益激烈的媒體競爭中,媒體的商業化導向開始主導媒體把關的標準,事件本身的價值讓位于新聞報道的價值。
根據把關人理論,新聞價值主要是“把交換價值作為衡量新聞的標準”[1]。由于媒體面臨著內、外部的多種制約因素,新聞價值的衡量標準是多維性的。日益商業化的新聞生產線上,媒體在操作中主要應考慮兩個標準:一是新聞制作中的業務標準(事件適合于媒介進行新聞處理的各種條件),二是新聞傳播中的市場標準(事件能夠滿足受眾新聞需求的諸條件以及吸引受眾興趣的諸條件)。[2]這些價值標準外化為滿足受眾需求,迎合受眾的興趣點,就形成了一切以吸引眼球為標準的模式。但是,過度注重新聞價值的業務標準、市場標準的結果是,媒體忽視了其應承擔的社會責任,喪失了其力求客觀、全面的新聞專業主義精神。從2008年“彭宇案”報道以來,類似的“老人倒地”事件便引發了持續關注。基于這種現狀,媒體為吸引受眾而陷入集體無意識狀態,在議程設置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側重這類選題。在媒體報道信息容量一定的情況下,對此類信息的過度關注將必然造成輿論導向的偏離。
(二)事件特殊性:選擇性報道的內在動因
信息進入媒介議題進而形成輿論強勢,事件本身的新聞價值也是基本條件。一系列的“老人倒地”事件之所以進入媒介議題并引起廣泛的關注,成為選擇性報道的對象,其特殊性表現在:
一是事實本身的爭議性。類似的“老人倒地”事件被稱作“羅生門”,即當事雙方各執一詞,即使第三方審判也難以下定論,令事件的真相不為人所知。這從去年8月“許云鶴案”的二審判決中可見一斑,并沒有充分的證據證明各方提供的說辭是否真實。道德與法律孰是孰非,給受眾以裁判、討論的話題空間。
二是事件在時間跨度上的連續性為報道提供了轟動效應。2009年10月“許云鶴案”事發,二審判決進入公眾視野并引發了公眾的廣泛討論。議題引發的轟動效應或許是媒體始料不及的,此后各地的“老人倒地”事件使媒體趨之若鶩。2011年下半年,與“老人倒地”相關的報道頻現各大媒體,“好心反被誣”、“社會道德滑坡”、“這么大一個中國扶不起一位倒地老人”……類似選題或單獨出現,或以專題、專版的新聞策劃形式出現,接近半年的連續性報道形成了積聚效應,并提高了傳媒引導輿論、制造議題的能力。
三是顛覆常理的沖突性。助人為樂、扶弱濟貧是傳統的社會美德,也是媒介和社會輿論長久以來宣揚的主流價值。當公眾對主流的宣傳出現“審美疲勞”的時候,各地“老人倒地”事件的當事人被貼上了“好心沒好報”的標簽登場,刺激了大眾的神經,挑戰長期以來形成的道德規范,拷問著社會良知。事件顛覆主流價值觀的沖突性必然能吸引廣大受眾的參與和討論。
四是體現受眾的心理動向。社會轉型期,法律制度的漏洞、社會保障的不完善、道德滑坡等問題長期引起受眾的關注,與此相關的公共事件自然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每一次輿論熱點的引爆都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會公眾的普遍心理動向。一系列“老人倒地”事件引發的熱議,則反映了社會道德滑坡和信任危機。
三、選擇性報道引發的輿論效應分析
(一)“標簽化”與“合理想象”,輿論集體“一邊倒”
筆者在對各地報道的文本分析中發現,對“老人倒地”事件大都選擇了顯要版面、專題性、大篇幅、事件鏈接等方式進行處理。對這一選題的側重處理明顯表現出媒體近乎作秀的圍觀心態。媒體在揭露事實時普遍采用了兩種方式:一是“貼標簽”,即在事實還不明晰的情況下,媒體就已預設了其立場態度,施救者都被貼上了“好心反被誣”的標簽,而被救者都是以“誣陷”和“無良”的形象出現。而事實是大多數被救者在事后都感激施救者,給受眾帶來“救助恐懼癥”的認識。二是“合理想象”。由于事件的突發性以及時空限制,記者無法親歷這些事。因此在報道中,記者只能引述當事雙方的相互指責或“合理想象”,以常理來推定的情況較多,而忽視了不同事件的特殊性。這樣的報道使新聞的真實性大打折扣。
“標簽化”與“合理想象”式的選擇性報道造成了輿論的偏離,進而影響了公眾的價值判斷。針對報道掀起的道德大討論,人民網輿情監測室首創了“輿論指數”調查。[3]此次調查針對“該不該扶跌倒老人”的問題,調查了資深媒體人、門戶網站和網絡社區負責人、專家學者、知名網友和草根網友5類人群。調查將輿論信心指數分為9級,得出的結論是“輿論信心總指數0.5278,輿論信心不足”。
(二)信息量失衡,擬態環境的構建偏離現實
美國傳播學者沃倫·布里德提出“潛網”概念,他認為任何處于特定社會環境中的傳播媒介都擔負著社會控制的職能,而這類控制往往是一種潛移默化、不易察覺的過程,用一個形象化的詞來概括就叫“潛網”。處于“潛網”中的受眾,他們對客觀現實的認識、對環境的監測,都是基于媒介提供的“象征性現實”,并在潛移默化中受其影響。正常狀態下的大眾媒體,其構造的“象征性現實”應該是整個世界、整個社會的縮影。但是,由于受到內、外部因素的制約,媒體在信息的把關過程中自動地過濾掉了不符合其價值標準的議題,轉而報道關注度較高的議題。高關注度下的信息流一旦匯聚成意見流,就會形成輿論強勢,左右受眾主觀現實的構建。但是經過過濾的主觀現實是片面的、與客觀現實相偏離的。例如,近年來媒體對“富二代”、“官二代”的井噴式報道,媒體的出發點或許在于聚焦社會問題、促進公平正義,但也同時給公眾塑造了當今社會貧富差距拉大、權力財富極度膨脹的主觀現實,刺激了草根階層的仇富心理。這種情緒一經放大,就會偏離社會的主流價值觀,一定程度上影響社會的和諧和公民信心。
助人為樂、扶助弱勢群體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媒體在力求客觀、公正報道“老人倒地”事件的同時,其形成的輿論強勢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社會恐慌。扶危濟困的社會負面效應被夸大,甚至產生了普遍的“救助恐慌癥”。但事實是,這個社會并沒有那么多的“無良老人”,向弱勢群體、危難者伸出援手仍是社會價值觀的主流。
(三)形成公眾的“刻板成見”,丑化老人形象
傳播學家李普曼在《公眾輿論》一書中提到過“刻板成見”的概念,指“常以高度簡單化和概括化的符號對特殊群體所做的社會分類,或隱或現地體現著一系列關乎行為、個性及歷史的價值、判斷與假定”[4]。“刻板成見”也被稱作“刻板印象”,在信息爆炸、生活節奏越來越快的現代社會,受眾對信息的處理傾向簡單化,更容易依靠“刻板成見”來形成意見。這種意見必然會帶來認識的偏見,各種人群被貼上標簽來加以認識。例如,在媒體報道中80后、90后代表了不同年齡的人群特征,“富二代”也不再簡單地是一類人群的代稱,更成為“炫富”、“垮掉”的代名詞。
各地“老人倒地”事件曝光以來,在事實真相并不明晰的情況下,媒體的審判往往先于事實的追討。在圍觀心理下,社會道德的力量正在漸漸隱去,一時間“老人”成了“欺詐”、“無良”的代名詞,在公眾心目中形成了刻板成見。媒體的評論鋪天蓋地,有些評論的標題甚至讓人震驚:江蘇殷紅杉事件中,當事人的馬路善舉并沒有遭到誣陷,事后老人還送上錦旗致謝。《三湘都市報》針對此事的評論標題《無良“老者”請別再摧殘我們有限的善良》,在缺乏對事實的充分查證下,這樣的言論明顯誤導了受眾的價值判斷,有丑化老人的嫌疑。
四、“老人倒地”事件選擇性報道的啟示
有學者認為,選擇性報道是“輿論引導的濫觴與流變”,并批判其造成了媒體倫理的失范,主要是認為其有違新聞報道的客觀、公正原則。[5]選擇性報道是否有違新聞操作的規范不是本文要討論的重點。但是,在信息大爆炸和媒體商業化的競爭中,選擇性報道已經成為媒體新聞運作的常態,唯有趨利避害,才能減少其對輿論引導產生的負效應。
我們看到,一系列“老人倒地”事件報道引發的“社會道德滑坡”論調以及普遍的心理恐慌感對輿論引導起到了負面影響。媒體有意放大了類似事件的輿論影響和價值示范意義,其本質是違背了應承擔的社會責任。時至今日,大眾傳媒在社會輿論構建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一個自由而負責任的新聞界”的呼聲也越來越高。重建公眾的社會輿論信心、弘揚優秀道德風尚,仍然是媒體義不容辭的責任。在商業化的媒體環境下,更要求傳媒業為客觀、全面的新聞報道提供良好環境,為新聞戰線培養出具有責任感和新聞專業主義的從業者。
同時,“老人倒地”的新聞“羅生門”事件考驗著媒體從業者對新聞真實性的追求。新聞價值的衡量標準應該是事實本身的價值而不應是其吸引眼球的籌碼。一個負責任的報道應該避免“合理想象”和跟風報道,以專業主義的精神追求新聞真實,讓更多的事件真相大白于天下。在輿論的激烈博弈和生成過程中,對真、善、美的弘揚永遠是輿論的主流,也是媒體社會責任的體現。
參考文獻:
[1]成美,童兵.新聞理論教程[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53.
[2]郭慶光.傳播學教程[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164.
[3]http://www.baojinews.com/_info/content_197648.htm.
[4]約翰·費斯克等.關鍵概念:傳播與文化研究辭典[M].李彬譯著,新華出版社,2004:273-274.
[5]姚必鮮.選擇性報道:輿論引導的濫觴與流變——2009年新聞報道倫理失范現象研究[J].長沙鐵道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