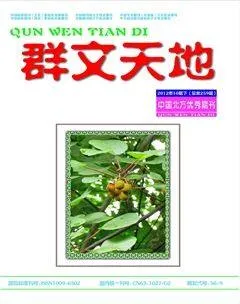淺析古典詩學之“飄逸”范疇
摘要:“飄逸”是我國古典詩學一個重要的美學范疇,用來指詩歌風格乃至意境的清新自然、灑脫不羈。晉陶淵明的詩歌和盛唐時期李白的詩歌是對詩學領域“飄逸”范疇的最好踐行和詮釋。
關鍵字:古典詩學;飄逸;范疇;陶淵明;李白
一、“飄逸”之詩學內涵
“飄逸”是我國古典詩學一個重要的美學范疇,用來指詩歌藝術乃至審美境界的灑脫自然、清新高遠。晚唐司空圖在其著作《二十四詩品》中首次明確地論述“飄逸”的美學內涵:“落落欲往,矯矯不群。緱山之鶴,華頂之云。高人畫中,令色氤氳。御風蓬葉,泛彼無垠。如不可執,如將有聞。識者已領,期之愈分。” “緱山之鶴,華頂之云”是說詩歌風格超然脫俗,猶如緱山上悠緩徐飛的仙鶴,又像華山上悠悠飄動的流云。而“御風蓬葉,泛彼無垠”二句,又指出“飄逸”的另一層含義為清秀自然,韻味無窮。這樣的詩歌境界,“如不可執,如將有聞”,令人難以捉摸,但是有時卻可以頓然領悟。而領悟的方法,則是“識者已領,期之愈分”,只能依靠心領神會,強求則會適得其反。宋代嚴羽繼承司空圖把“飄逸”視為詩歌風格特征之一的觀點,在《滄浪詩話·詩辨》中說道:“詩之品有九:曰高,曰古,曰深,曰遠,曰長,曰雄渾,曰飄逸,曰悲壯,曰淒婉”, 把“飄逸”列為詩的九品之一。姜夔則認為,“飄逸”是專用于描述詩歌的“韻度”的,“大凡詩,自有氣象、體面、血脈、韻度。氣象欲其渾厚,其失也俗;體面欲其宏大,其失也狂;血脈欲其貫穿,其失也露;韻度欲其飄逸,其失也輕。” (《白石道人詩說》)既然“韻度”是構成詩歌藝術的重要因素之一,那么“飄逸”對于詩歌來說是不可或缺的,少了飄逸,就是少了韻度,詩歌就會淪于輕佻膚淺。在這里,姜夔指出,“飄逸”不僅僅是詩歌應當具備的一種外在的特征、風格,更重要的是“飄逸”顯示了詩歌內在“韻度”,即詩歌的內蘊應是深厚有味的,散發出來的精神氣才會因為厚重的內涵而更顯超脫自然,風姿搖曳,而不會流于淺薄。
二、“飄逸”之詩歌體現
“飄逸”在詩學領域既是指詩歌外在風貌的清新自然,意境的杳渺高遠,同時又強調詩歌內涵應當韻味無窮,有實質的精神氣,這種精神氣,應當要如“仙鶴”、流云一樣灑脫超然。縱觀中國古代詩歌,最能體現出“飄逸”之美學內涵的莫過于陶淵明的詩和李白的詩。
1.陶淵明詩之“飄逸”
魏晉南北朝朝代更迭頻繁,政局混亂、腐敗,社會動蕩不安,許多文人目睹、親身經歷官場的黑暗殘忍,又無力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實現“治國平天下”的理想,只能被現實逼回“修身”的境地,選擇歸隱,遠離亂世。這些放棄仕途的文人,成日流連往返于山林水澤之間以排遣心中苦悶,漸漸心態平和,恢復無欲無求的自然本性;或棄文從耕,在安貧中獨享清幽寧靜。他們的詩歌所呈現出來的風格,自然是與他們心境一致,顯得清新自然,自有一股超越俗世自醉于純凈自然的心靈園地的意味。而陶淵明,正是寫作這種風格清新灑脫、內容韻味無窮的“飄逸”詩歌的好手。
陶潛之詩語言質樸純凈,字字句句流露出一股享受歸隱田園生活的安逸和清心;詩歌內容平淡日常,卻處處充滿著詩意、趣致;詩人感情真切單純,對黑暗官場的厭惡、對遠離世俗、超然“世外”的農耕生活的偏愛溢于言表。其詩意境清新灑脫,同時充滿著耐人深思的哲理。這正是“飄逸”范疇審美的深層體現。“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歸園田居·其一》)“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涂口》)是詩人對自由、寧靜的歸隱生活的向往,“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飲酒·其五》)“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歸園田居·其三》)是這種隨心所欲、不拘于世的生活的踐行,而“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飲酒·其五》)“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歸園田居·其四》)則是作者發出的深沉感慨,言語灑脫而意蘊綿厚。正是因為身居山林、田園之間,遠離丑惡動蕩的亂世,陶淵明才看透萬物榮盡枯至,四季更迭輪回,明白世間一切生死榮辱都會“幻化”、“空無”,唯有一顆自由、不受羈絆的心,一份恬淡、安然的生活才是人生的真諦。
陶淵明詩語言的清新質樸,內容看似平淡卻余味無窮,散發出超然脫俗的精神氣。這種精神氣使得其詩歌直達“飄逸”的核心內涵,詩歌境界純凈高遠。
2.李白詩之“飄逸”
唐朝是我國詩歌發展最快、最興旺的時期,也是詩歌創作達到頂峰、完美的時期,后世難以超越。特別是盛唐時期的詩歌,與繁榮昌盛、自由開放的社會風氣相適應,詩風大體上呈現出激昂開闊、積極向上、飛揚飄逸的特點。李白是這種詩風的集大成者,最能代表盛唐時期詩歌的特征、風貌,人稱“詩仙”李太白。“詩仙”一方面指出李白詩歌藝術造詣的高超,另一方面指的是李白桀驁不羈、特立獨行的個性。正如葉燮所說:“每詩以人見,人又以詩見”(《原詩》),李白的高傲灑脫、不羈于世的個性使得其詩歌也散發出超然脫俗的“飄逸”之風,而且李白在其詩歌中把“飄逸”之風發揮到極致,無人能及。清代潘德輿在《養一齋詩話》中稱贊道:“荊公云:李白歌詩,豪放飄逸,人固莫及’”,實是中肯之論。
李白詩歌之“飄逸”,是與杜甫之“沉郁”相對的。“子美不能為太白之飄逸,太白不能為子美之沈郁。”(嚴羽《滄浪詩話》)“若太白子美,行皆大步,其飄逸沉重之不同。” (謝榛《四溟詩話》)“暨觀太白少陵長篇,氣充格勝,然飄逸沉郁不同。”(王士禎《藝苑卮言》)杜甫的詩歌向來言辭厚重,詩歌內容大多傷國憂民,情感哀傷憂郁到極致,是為“沉郁”;李白則恰好相反,詩歌語言豪邁激昂,感情熱烈奔放,不可遏制,詩歌所表達的意旨,又大多是雖受厄而不掛于心,蔑視俗世,渾然一超凡脫俗的“仙人”。最能體現李白“飄逸”詩風的詩作是《夢游天姥吟留別》。《夢游天姥吟留別》是一首游仙詩,是李白于官場中受權貴排擠,被流放途中所作。全詩極富浪漫主義氣息,景物描寫如“天姥連天向天橫,勢拔五岳掩赤城”,抑或“熊咆龍吟殷巖泉,栗深林兮驚層巔”,手法夸張,氣勢雄渾。而詩人于夢中,“一夜飛度鏡湖月”,攀登上天姥山,他看見“洞天石扇,訇然中開。青冥浩蕩不見底,日月照耀金銀臺。霓為衣兮風為馬,云之君兮紛紛而來下。虎鼓瑟兮鸞回車,仙之人兮列如麻”,進入了一個奇誕、絢麗的仙境。直至夢醒,頓覺這一切美景皆是夢,詩人不禁感慨“世間行樂亦如此,古來萬事東流水”,于是,對官場中的不快之事,頓時看開,發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的豪邁宣言!縱觀全詩,詩歌語言跳躍活潑、飛揚飄逸,貼合激昂的詩歌情感;詩歌主旨表達了李白及時享樂,蔑視權貴,“仙人”般孤傲灑脫、不為俗世掛心的思想,這正是其“飄逸”詩風的精髓所在。李白的其他詩歌諸如“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將進酒》)“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云帆濟滄海”(《行路難》),也都是“飄逸”豪壯之作。
綜上,“飄逸”之詩學范疇可指清新自然、意境渺遠之詩,也可更進一步,指灑脫跳躍、意境飛揚壯逸之詩,陶淵明詩和李太白詩恰好分別完美詮釋了包含這兩種不同內涵的“飄逸”范疇。陶淵明不堪忍受紛繁亂世,選擇“出世”,以一顆淡然的心書寫清新飄逸之詩,意境純凈高遠;而李白正相反,正因為熱愛繁華盛世,所以一直“入世”,卻不與世中丑惡同流合污,以其桀驁不羈之個性揮寫灑脫飄逸之詩,意境跌宕起伏,超凡脫俗。雖然二人對“飄逸”范疇的領悟不同,但是毫無疑問,他們的詩完美地踐行、完善了“飄逸”的美學內涵。
(作者單位:華南師范大學南海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