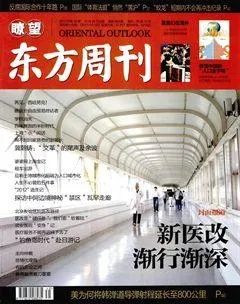應將土地城市化扭轉為人口城市化
接下來若干年內的中國經濟若想保持目前的增長速度、且是可持續的話,同樣需要遵循這一客觀發展規律,需要持之以恒地減少農民數量與消滅“農民身份”
30多年的中國經濟發展取得了年均10%左右的增長業績,為世人矚目和稱贊!但是宏觀經濟始終存在內需不足、環境代價高、收入分配矛盾突出等問題。
粗放式、無法兼顧效率與公平的經濟發展方式已經被公認為不可持續。然而時至今日,盡管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系列政策已經實施,效果卻不太理想。鑒于城市化是帶動經濟高速增長的主要源泉之一,筆者的研究以城市化模式選擇的內在機制作為闡述經濟發展方式粗放與不可持續的制度背景載體。同時,筆者認為,只有轉變現有的城市化模式,才能逐漸推動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
地方政府的職能轉換與城市化模式
不可否認,地方政府在本地經濟發展過程中起了領導作用,這一特征也成為中國模式的核心所在。那么,地方政府的領導作用機制是什么?地方政府是怎樣通過城市化來推動本地經濟發展的呢?
值得一提的是,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地方政府未能從建設型與全能型政府轉變為服務型政府。
也就是說,地方政府職能定位偏離了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其發展目標函數中過于注重GDP,沒能也沒法體現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理念。由此產生的經濟影響是,容易產生國地區之間GDP競賽而出現的各類激進的地方政策,如占耕地、環境保護意識薄弱、征地補償標準低等。
此外,處在轉軌時期的中國,在推進新型工業化與高速城市化過程中,地方政府的目標函數則要復雜許多,對他們來說,有限的財政資源或銀行融資是用于屬于民生工程的公共產品提供,還是用于能帶動當期GDP增長的基礎設施建設?在現有的考核機制下,第二種情況可能更加普遍。因此,在這一意義上說,地方政府的職能定位是建設型的、全能型的,而非服務型政府。
從城市化進程而言,目前進行的城市化模式同樣不能導致土地城市化轉變為人口城市化。
概括而言,土地城市化模式與經濟增長方式是以土地要素的扭曲配置及其衍生出來的土地金融為紐帶,進而帶動整個經濟的快速發展,由此帶來不少弊端,如土地城市化速度遠大于人口城市化速度,在2001—2008年期間,城市常住人口年均增長率為3.55%,城市建成區面積年均增長率為6.20%。
但流動人口在冒進的快速城市化過程中獲益較少,影響了社會穩定與和諧局面。從世界城市發展經驗來看,城市化實際上是農村人口不斷向城市聚集與融合的過程,融合就必須解決流動人口在城市的居住、養老、醫療等后顧之憂,而這恰恰是人口城市化模式的體現。
因此,制約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與城市化健康發展的最重要因素是未能將土地城市化扭轉為人口城市化模式。
應該遵循幾個基本事實
當前我們城市化的方向應該是什么?
在討論這一問題之前,應當先厘清如下邏輯關系:中國近三十多年經濟發展的成功經驗是什么?也許有人會說是進行了市場化改革釋放了大量的生產力。這沒錯,但更為根本的一點是,由于中國龐大的人口基數,只要源源不斷地將農村農業人口轉移到城市非農部門就業,就極易發揮制造業生產的規模經濟,進而使得整個經濟的專業化分工越來越細,經濟效率不斷提高、經濟蛋糕不斷做大!
那么,在接下來若干年內的中國經濟若想保持目前的增長速度、且是可持續的話,同樣需要遵循這一客觀發展規律,需要持之以恒地減少農民數量與消滅“農民身份”。為此,一個重要的政策宗旨與前提是:消除農民從農村流向城鎮的各類障礙。
因此,當前城市化的方向應該遵循以下幾個基本事實。
首先,建設型政府的首要目標是GDP,大量的金融資源、土地資源都被用于有利于提高當期GDP的各種用途,而非用于各類民生建設上。這一行為方式對政府來講,極P22HUXiQfIGRqwAlfmQFeJw+PDAkvfHpNh8S309OoWQ=易產生各類激進政策,是一種現代意義上的城市化“大躍進”。同時,筆者認為推動經濟發展必須是眾多參與者一起參與的、和風細雨式的、潤物細無聲的、基礎牢固的發展模式,僅僅憑地方政府一舉之力、以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大項目的形式來推動經濟增長,顯然是短視的和基礎不牢的!
其次,與產業結構呈現出低端化相聯系的是農村勞動力就業結構與年齡結構。
一方面,從農村家庭收入的構成來看,國內學者發現,家庭成員中的年輕一代在外打工收入與年長一代在農村務農收入各占50%左右,這兩者收入之和正好將目前中國農村家庭生活水平維持在“溫飽之上、小康之下”的區間內,兩種收入來源中任何一項缺失都將對農民的生活與農村穩定產生重要影響。
另一方面,筆者的研究及國內其他學者的研究均發現,2004—2005年以來以農村勞動力轉移進入城鎮非農部門就業為驅動力的經濟增長中的配置效應突然消失了,也就是說,通過勞動力轉移帶動經濟增長的潛力已經被窮盡了。
方向是什么
結合上述特征與土地城市化事實,筆者擬提出以下相應的城市化策略方向:
第一,地方政府退出土地市場。近十多年來的經濟快速增長,雖然得益于土地城市化模式,但更多地產生了現階段收入分配不公平、社會不穩定與環境代價大等弊端。
第二,用人口城市化取代土地城市化。筆者建議,對于醫療、養老、教育等方面的社會保障支出,應該由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共同出資解決;對于流動人口居住需求的解決方式,在地方政府退出土地市場的前提條件下,集體土地在未經國家征用的情況下由市場機制來建設和運營廉租房。當然,廉租房建設必須符合城市土地總體規劃和城鄉建設用地詳細規劃。
第三,不可急速地推進土地市場上的城鄉一體化。目前學界與社會有一種普遍的誤解,既然地方政府扭曲了土地要素的市場化配置、并占用土地出讓的絕大部分收益,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經濟發展方式的不可持續性,那么,為了徹底扭轉這一狀況,索性將土地出讓的所有收益徹底讓渡于農民,使地方政府徹底干凈地退出土地市場。這是一種過于簡單的思維方法與邏輯推斷。
殊不知,目前土地價值高的區位多數是位于大型城市的郊區或者沿海地區,如果將這一區位的土地“私有化”將使收入分配不公狀況更加惡化。更為重要的是,大量資本下鄉使得農村家庭有可能喪失占一半左右的農業經營收入,在城市就業機會不充足、產業結構低端化造成的低工資收入等情況下,這種急速的土地市場一體化完全可能打破目前穩定的農村生活、農業生產局面。
只有在城市廉租房已經大量建成并對流動人口開放的情況下,家庭成員的非農收入能維持其在城市中體面的基本生活,資本下鄉的前提條件才是成立的。需要強調的是,筆者并不否認或降低土地出讓收益中的農民應得份額,相反,合理的、農民應得的土地補償要求對于促進城鄉統籌具有重要意義。
此外,將現有的工業用地存量轉化為住宅用地。在土地城市化模式中,工業用地的供應面積與住宅用地面積之比達到2:1,產生了大量的工業用地浪費、濫占濫用等現象。因此,在不影響生產的前提條件下,完全可以切出一部分工業用地存量,使之變更為住宅用地。
具體操作方法是,先變更這一部分土地使用權的屬性,再依照當年工業用地協議價與同地段商住用地的招拍掛價格,補交兩者之差價部分,最后依照當年招拍掛價格與現階段的商住用地的招拍掛價格,并對于兩者之間的增殖部分征收高額的土地增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