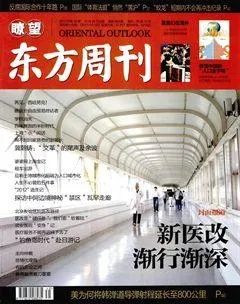悲情代理商
2012-12-31 00:00:00姜智鵬
瞭望東方周刊 2012年40期


“由于歐債危機,引致全球銀行收緊貸款,生物梅里埃亦面臨現金周轉的嚴重短缺。在別無他選的情況下,由即日起所有買賣合同均已先付后運。對上海祥和公司帶來的不便,深感抱歉。”這段話來自2011年11月14日,署名為生物梅里埃集團(以下簡稱“梅里埃”)大中華區首席財務官蔣志豪的一份傳真。傳真中另一項內容是:“上月中提及的第二季度美元代理價上調3%,將于2011年12月1日起執行,請盡快下定單。”
梅里埃是法國的上市公司,為全球醫療診斷及生物制劑產業巨頭,目前全球擁有40個分公司。上海祥和科學技術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祥和”)即是其在華東區域的代理商。
當祥和董事長朱明看到上述傳真時,覺得這或許能緩和與梅里埃公司2個多月來的緊張關系。于是11月28日,祥和向梅里埃支付了1200萬元人民幣的貨款。
這原本應該是個中國代理商與國外品牌共度時艱的感人故事。但就在祥和支付貨款次日,朱明突然接到梅里埃的通知:祥和2012年的代理權被解除了。
“按照行業慣例,解除合作前應先談善后。當時除了新訂單,祥和還有6000多萬元的庫存,但梅里埃未提出任何解決方案。”朱明告訴《瞭望東方周刊》。
2012年5月,事件雙方的最后一次談判仍舊不歡而散。
溝通不暢?過河拆橋?梅里埃與祥和之間的紛爭并非個案,而是國外品牌商與中國代理商之間恩怨情仇的一個生動寫照。
隱形的合同
2011年11月30日,祥和收到梅里埃的“警告信”,稱“自2012年1月1日起,將不再給予貴司所有臨床產品的現有全部區域的銷售授權”。就這樣,祥和此前擁有的梅里埃所有產品代理權突然間被解除了。
梅里埃此舉的依據是祥和沒有完成預定的銷售業績。但朱明堅決否認。他反而認為,梅里埃的真正用意在于用11家新的代理商取代祥和,以便提價。因為梅里埃的銷售策略是訂單量越大折扣越高。因此,11家小代理商分割了一家獨大的祥和的市場后,拿貨價必定會上漲。
梅里埃大中華區高級執行副總裁對此并沒有否認,但他認為,梅里埃對終端有很好的控制,不會導致成本轉嫁到用戶身上。“有了這11家新的代理商之后,梅里埃在華東地區的業績有了明顯的上升。”
早在2007年,梅里埃與祥和之間就發生了代理合同之爭。朱明告訴本刊記者,1995年到2006年間梅里埃從未要求祥和簽訂代理合同,只是每年發一份次年的授權書給祥和。自1995年起,祥和在最高峰時其銷售額占梅里埃在中國總銷售額的40%。隨著銷售額的增長,2007年梅里埃提出了簽訂代理合同的要求。但朱明并不認同。“當時我們認為合同里的一些內容不公平,要求修改。對方不讓步,稱我們不簽就表示放棄代理權。”
“梅里埃拿出的是全球通行的標準合同,我們在全球有150個代理商,有些合作了40多年,不可能因為祥和一家有異議就給他們做一個專門的合同。” Thierry Bernard解釋說。
最后的結果是合同沒簽,模式照舊,祥和依舊像從前一樣代理銷售梅里埃的產品。
2011年12月17日,合作十多年的伙伴分道揚鑣。
梅里埃對祥和拋出了一個解決方案:代理權終止;雙方結清應收賬款;梅里埃回購祥和的庫存;以祥和公司2010年銷售額的14%賠償祥和的損失(而2010年是祥和公司業績最好的一年)。
“我們研究了國際和中國的所有法律,知道終止代理權不需要付1分錢的補償費。但我們還是提出了這個補償方案。” Thierry Bernard表示。
梅里埃方案的核心是:祥和公司的庫存試劑,梅里埃回收有效期在4個月以上的部分(梅里埃產品的平均有效期是1年);梅里埃買下祥和公司與客戶簽署的所有服務合同。
在以往的經營中,祥和都是購買梅里埃的設備免費提供給用戶,雙方簽訂為期5年的投放協議,由祥和公司用固定價格供應所需試劑,祥和靠試劑利潤收回成本并獲利。
現在梅里埃提出的收購方案,是所有設備在折舊后按殘值回收,至于后續的服務合同,則由新的代理商履行。這是朱明最不能接受的條款。因為祥和的盈利模式就是賺“服務”的錢,即靠提供試劑獲利。
朱明認為,梅里埃的補償離祥和的損失相差甚遠。
如今,談判仍沒有結果。現在朱明面臨的難題是,如果接受2012年5月的最后一次談判中梅里埃的方案,就有3000多萬損失得不到補償,但不接受,每拖一天庫房里的試劑都有一批過期。
品牌商的“連環套”
就在祥和與梅里埃僵持的同時,“貝爾多爸爸的泡芙工房”的代理商和日本品牌商之間的代理權大戰也正如火如荼。
2003年,麥之穗(上海)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長蘇悅說服日本麥之穗公司將該品牌引入中國。
2003年8月,麥之穗(香港)有限公司成立,日本麥之穗和蘇悅各占90%和10%。其后麥之穗(香港)有限公司又開設了麥之穗(上海)食品有限公司,到2008年,這家公司虧損600多萬元人民幣。
2006年,日本螞蟻基金收購了日本麥之穗并打算將其包裝在日本上市。而中國市場由于表現欠佳,螞蟻基金打算以不良資產名義將香港麥之穗剝離。
瞅準了這個機會,蘇悅于2008年以1287萬港元接盤香港麥之穗中日方持有的90%股權,并將公司改名為美味優(香港)有限公司,全資控股上海麥之穗。
雖然這個價格是香港麥之穗公司凈資產的近2倍,但他可以獲得品牌在大陸的工廠和供應體系,以及品牌在中國的使用權,這還是令他感到劃算。
2008年2月29日,日本麥之穗與美味優簽訂《特許經營協議》及《商標使用許可合同》,合同期限為5年,即2008年2月29日始至2013年2月28日,在中國對品牌和商標享有獨占使用權。美味優又對上海麥之穗進行了大陸地區的品牌授權。
實際上,在收購完成后,蘇悅曾提出要和日本麥之穗簽訂長期的特許經營合同,取代只有5年期限的格式合同。但多次交涉未果。蘇悅最終只能妥協,卻沒想到這為他失去這個品牌埋下了伏線。
此后,上海麥之穗以連鎖加盟的方式快速擴張。2009年,上海麥之穗才意識到一個致命問題:中國《商業特許經營管理條例》規定,特許加盟期不能低于3年,也就是說從2010年2月28日開始,上海麥之穗就不能發展加盟商了。
2009年,上海麥之穗開始與日方協商續約,仍舊未果。于是蘇悅決定停付管理費。按照當初的協議,美味優在一次性支付1000多萬港元的加盟金后,每個月每家店還要支付幾千元的管理費。
“停付管理費之后對方態度明顯就好很多,這對我產生了很不好的心理暗示。”蘇悅告訴本刊記者。這輪博弈似乎對蘇悅有利了,2010年年初,日本麥之穗擬定了“自動更新、延長期限”的協議,規定特許合同如小于3年就自動追加1年,讓期限永久保持在3年以上,而蘇悅則支付拖欠的管理費。但最終協議一直沒有簽署。
2011年,擴張陷入停滯的蘇悅得到消息,由于日本麥之穗上市遇到困難,螞蟻基金正在尋找接盤者,報價8000萬美元,之后便終止對美味優的授權。
這次蘇悅故伎重施,再次停付管理費,并限期日方3月內必須續約。但這一次日方沒有被嚇倒。2011年9月,美味優發函提出解約,同時建立自己的同類品牌——西樹泡芙。蘇悅打算重新奪回市場,但卻依然逃不出老東家的布局。2012年7月,日本麥之穗專門到上海召開新聞發布會,稱因香港美味優未在約定的期限內開設足夠數量的加盟店,所以香港美味優的特許經營權已經變更為一般(非排他,非獨占)特許經營權。
更重要的是,美味優違反了特許經營合同中的約定的競業禁止義務。當時合同約定,美味優自合同終止之日起兩年內不得以其他品牌從事或授權第三人從事與“貝兒多爸爸”品牌運營及形態類似的競業行為。
2012年1月,香港高等法院責令香港美味優停止競業行為。無奈之下,蘇悅只能把西樹泡芙賣掉。
不久前,蘇悅帶著這個教訓又代理了一個新的甜點品牌,這一次,他提出與對方成立合資公司并利益捆綁,一下簽訂15年的代理權。
然而,失去的終究是失去了。
代理權糾紛為何頻現中國
以上僅是中國眾多代理權糾紛的兩個典型案例。
上海市商務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朱樺告訴《瞭望東方周刊》,近幾年由于全球經濟危機,國外品牌與其代理商之間屢屢發生代理權糾紛,而中國這種例子更多。因為長久以來,國外品牌在中國供不應求,因此大多高高在上,經常出現“過河拆橋”的例子。
但隨著中國市場的崛起,國外品牌紛紛進入中國,情況已有所改善。“這些品牌之間競爭激烈,代理商渠道就成為他們搶占市場非常重要的因素。品牌商一邊倒的強勢時代已經過去了。”朱樺說。
在瞿東看來,這樣的趨勢已經在奢侈品代理行業有了深刻的體現。瞿東是歐洲一個服裝奢侈品牌的大中華區總經理,曾站在品牌的角度與代理商有過“較量”。
瞿東告訴本刊記者,中國的代理權糾紛爆發最早最激烈的行業,應該就是奢侈品銷售。而最早吸引全國關注的,就是萬寶龍與代理商的那場糾紛。2006年,萬寶龍以停止供貨的形式與上海國瑞信鐘表有限公司“翻臉”。很快,一場曠日持久的官司打得舉國皆知,當時的國瑞信一度將萬寶龍投訴到商務部,只為獲得3500萬元的賠償。
“最早時,代理商只能被動接受,因為品牌在一線城市開設直營店易如反掌,很多購物中心甚至愿意貼錢貼租金吸引品牌。那時候代理商沒有任何話語權。”瞿東說,但最近幾年,隨著一線城市網點資源稀缺,再加上進入中國的品牌越來越多,擁有渠道的代理商倒過來挑品牌了。“2009年,美國奢侈品牌COACH對中國代理商的零售業務進行收購, 20多家網點資源,代理商得到了2億元補償。”
瞿東說,品牌商根據自身策略調整甚至取消代理權無可厚非。“業內真正關注的焦點是:以前說代理商吃虧是因為沒有核心資源。但這兩家代理商明明擁有諸多籌碼,例如客戶資源、渠道優勢,可最終在自身利益的保護中依然被動、無力,前車之鑒為何依然沒有成為后事之師。”
這兩件事對業界的啟發在于:中國代理商在弱小時沒有確定平等的地位,在強大之后,卻迷信于自己的實力和不可替代性,又忽略了現代商業社會最重要的契約關系建立。瞿東說,如今的代理商悲情,早已不是實力弱小的原因,其根子還在于代理商企業自身的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