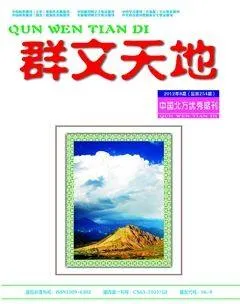論情景再現(xiàn)與通感的關(guān)系
摘要:作為播音有聲語言創(chuàng)作內(nèi)在表達(dá)技巧之一的情景再現(xiàn)在實(shí)際工作中發(fā)揮著重要作用。只有充分調(diào)動(dòng)創(chuàng)作主體的多樣的感受器官,利用心理學(xué)中的概念通感,才能多層次、多角度的實(shí)現(xiàn)對創(chuàng)作文本的深刻理解、對創(chuàng)作客體的較全面把握。
關(guān)鍵詞:情景再現(xiàn);同感;互相溝通;深刻理解
作為播音有聲語言創(chuàng)作內(nèi)在表達(dá)技巧之一的情景再現(xiàn)在實(shí)際工作中發(fā)揮著重要作用。在播音主持教材中,談到情景再現(xiàn)時(shí)基本上都是在強(qiáng)調(diào)創(chuàng)作主體視覺動(dòng)態(tài)上的效果。比如,目前中國傳媒大學(xué)出版的《實(shí)用播音教程》中對情景再現(xiàn)是這樣定義的,“情景再現(xiàn)在播音中具有特定含義,即:在符合稿件的前提下,以稿件提供的材料為原形,使稿件中的人物、事件、場面、景物、情緒;在播音員腦海里不斷浮現(xiàn),形成連續(xù)活動(dòng)的畫面,并不斷引發(fā)相應(yīng)的態(tài)度、感情,這個(gè)過程就是情景再現(xiàn)。”這個(gè)定義側(cè)重于從時(shí)間、因果的角度揭示情景再現(xiàn)的內(nèi)涵,很明顯體現(xiàn)更多的是縱向、動(dòng)態(tài)的特點(diǎn)。而在現(xiàn)實(shí)的有聲語言創(chuàng)作中,從橫向、靜態(tài)的角度入手常常能發(fā)掘出事物更為本質(zhì)的特點(diǎn),展現(xiàn)事物更為細(xì)膩豐富的內(nèi)涵。那么,從橫向入手如何調(diào)動(dòng)內(nèi)心感受,憑借什么具體手段實(shí)現(xiàn)情景再現(xiàn)呢?筆者認(rèn)為,只有充分調(diào)動(dòng)創(chuàng)作主體的多樣的感受器官,利用心理學(xué)中的概念通感,才能多層次、多角度的實(shí)現(xiàn)對創(chuàng)作文本的深刻理解、對創(chuàng)作客體的較全面把握。
什么是通感?百度百科中這樣的定義。“通感修辭格又叫“移覺”,就是在描述客觀事物時(shí),用形象的語言使感覺轉(zhuǎn)移,將人的聽覺、視覺、嗅覺、味覺、觸覺等不同感覺互相溝通、交錯(cuò),彼此挪移轉(zhuǎn)換,將本來表示甲感覺的詞語移用來表示乙感覺,使意象更為活潑、新奇的一種修辭格。”
一、有通感才能使情景再現(xiàn)更深入、更接近本質(zhì)。
下面就以一些具體的實(shí)例來鋪開分析。
現(xiàn)代著名散文家、詩人、學(xué)者、民主戰(zhàn)士朱自清,其散文樸素縝密,清雋沉郁、語言洗煉,文筆清麗,極富有真情實(shí)感,他以獨(dú)特的美文藝術(shù)風(fēng)格,為中國現(xiàn)代散文增添了瑰麗的色彩,為建立中國現(xiàn)代散文全新的審美特征創(chuàng)造了具有中國民族特色的散文體制和風(fēng)格,他的主要作品之一《春》。
其中有一段寫道:“桃樹、杏樹、梨樹,你不讓我,我不讓你,都開滿了花趕趟兒。紅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花里帶著甜味,閉了眼,樹上仿佛已經(jīng)滿是桃兒、杏兒、梨兒。”我們可以看到樹上花團(tuán)錦簇,枝頭上盡是紅的、粉的、白色的各色花兒,還可以感受到,想象中枝頭上已經(jīng)掛滿了累累碩果。春天的景象是繁花似錦的。
但如果我們再運(yùn)用通感,我們就不僅只看到了滿枝頭的花兒,我們可以感受到它們生生不息的生命力,不停地想要努力地向前向前再向前,我們不僅看到紅色的桃花,更能感受到火一樣,炙熱、旺盛的,像火一樣散發(fā)出光和熱;粉色的梨花像霞光一樣,我們仿佛看到了日出、日落時(shí)天空及云層上因日光斜射而出現(xiàn)的彩色光象或彩色的云;白色的杏花兒像潔白的雪,靜靜地,成片成片的。一陣春風(fēng)吹過,花瓣隨風(fēng)落下,樹上、地上全都是各色的花,讓人不禁發(fā)出“那花兒多美啊”的感嘆。
“花里帶著甜味兒”,我們不僅看到了花兒的顏色(視覺),我們更聞到了甜(嗅覺),我們仿佛就聽到了有人在頌唱《春之曲》(聽覺)。“閉了眼”(器官,身體的行為),用心去靜靜地感覺和想像,“樹上仿佛已經(jīng)滿是桃兒、杏兒、梨兒。”樹上的花已經(jīng)變成了秋天累累的碩果,大大地水蜜桃、黃色地飽滿地杏兒還有肉質(zhì)細(xì)膩、多汁兒的大鴨梨。這些都是春天帶給人們的無限美好地感覺。
再看另一段:“吹面不寒楊柳風(fēng)”,不錯(cuò)的,像母親的手撫摸著你……
“吹面不寒楊柳風(fēng)”,當(dāng)春天的陽光照臨大地,楊柳吐出了新綠,微風(fēng)輕拂,吹到人們的臉上(觸覺),是那樣溫暖柔和(身體的感覺),已經(jīng)感覺不到一絲的寒意了。接著朱自清擷取了一個(gè)生活化的令人倍感親切的比喻“像母親(視覺)的手撫摸著你”(觸覺),寫盡了春風(fēng)的氣韻神情。
在上一段文章當(dāng)中,我們不僅身體能夠感受到風(fēng)吹到臉上的感覺,而且還有觸摸到身體之后的感覺,——溫柔地,是一種很舒服地感覺,這是春風(fēng)特有的輕柔和溫暖,仿佛我們看到了自己地母親,慈祥地母親,眼中帶著笑意,花白的頭發(fā)在春風(fēng)的吹拂下?lián)u曳著,坐在家門口的陽光下,用她那長滿老繭,略顯粗糙的手,輕輕地、一遍遍地摩挲著孩子的頭發(fā)和臉頰,那種只有孩子才能感受到的、特有的、母親的愛撫,靜靜地仿佛回到了童年時(shí)光,不知不覺,在母親的撫摸和春光的照射下,即將進(jìn)入夢鄉(xiāng)。
播音者通過情境再現(xiàn),再結(jié)合通感,通過身體、聽覺、嗅覺等細(xì)膩的感受,通過合理的想象,將難以狀寫的春風(fēng)的感覺表現(xiàn)的神韻透徹。
二、情景再現(xiàn)中的通感能使人物形象更豐滿、更鮮活
“感受是關(guān)鍵,是由理解到表達(dá)的橋梁。”是情景再現(xiàn)中重復(fù)強(qiáng)調(diào)的一句話,人的各種不同的感官,只能對事物某些特定的屬性加以認(rèn)識(shí),因此在人們從感覺、知覺到表象的過程中,實(shí)際上也是各種感覺器官相通的過程。人類藝術(shù)活動(dòng)的“通感”實(shí)際上就是人們的認(rèn)識(shí)活動(dòng)的一種藝術(shù)表現(xiàn)形式。
通感,就是在人們的審美活動(dòng)中使各種審美感官,如人的視覺、聽覺、嗅覺、觸覺等多種感覺互相溝通,互相轉(zhuǎn)化。錢鐘書先生說過,“在日常經(jīng)驗(yàn)里,視覺、聽覺、觸覺、嗅覺、味覺往往可以彼此打通或交通,眼、耳、舌、鼻、身各個(gè)官能的領(lǐng)域,可以不分界線……”。可見,通感廣泛的存在于人們的日常生活感受之中,就象你看著滿園的春色,會(huì)哼起《春之歌》一樣。現(xiàn)實(shí)生活的文字的印記也不可避免地打下了“通感”的印記。
如果播音員平日里對于生活的觀察更為細(xì)致,更為豐富,那么,他對事物的感覺也就會(huì)越完整,通過他的感覺,受眾感受到更加豐富的事物和更加鮮活的人物。下面舉一個(gè)例子做更進(jìn)一步的說明。
如《扁擔(dān)的故事》里,“說著,她放下?lián)樱摿诵锕∩弦粩R,“嘩啦嘩啦”地淌進(jìn)了泥水汪汪的稻田里。”我們可以看到單黎英的一連串動(dòng)作,一邊說著話,一邊向稻田里去的情景。
如果我們再運(yùn)用上同感,不僅能夠聽到單黎英的問話(聽覺),看到性格直爽,干活麻利的她很迅速的把鞋拖下,彎腰放鞋(視覺),“嘩啦嘩啦”(聽覺)淌進(jìn)(觸覺)泥水汪汪的稻田里(視覺)。除此之外,還要了解這件事情發(fā)生的地點(diǎn),和時(shí)間。再過過自己的感受,這樣在表達(dá)的時(shí)候,賦予稿件更加具體、豐富的色彩和真切、生動(dòng)的形象產(chǎn)生。
要做到以上所說,就要求播音員要擴(kuò)大知識(shí)面,注意感受和理解能力的培養(yǎng),不斷提高自己的觀察力和分析力。同時(shí)作為播音員要有大量的閱讀和豐富的生活的體驗(yàn)。任何體驗(yàn)無論是好的還是壞的,都是一種經(jīng)歷,一個(gè)成熟的感知敏銳的播音員必然在全息的再現(xiàn)表達(dá)中最能于細(xì)微處見精神。在理解文字稿件內(nèi)容的基礎(chǔ)上,使自己主動(dòng)接受刺激,積極產(chǎn)生內(nèi)心反應(yīng),這就是同感,使之融化在播音語言當(dāng)中。
(作者單位:陜西廣播電視臺(tái)新聞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