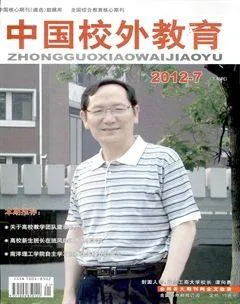論女性自我意識的泯滅
南戲的代表作品——高明的《琵琶記》,是作者根據民間流傳的《趙貞女蔡二郎》的故事改編而成的。《琵琶記》的女主人公是趙五娘,在她身上體現了中國婦女的傳統美德。但是,在她動人的故事背后,我們卻看到了男權社會中女性命運悲劇的一面,在作者宣揚的“子孝與妻賢”的內容中,是女性自我意識的嚴重泯滅。
一、女性自我意識的嚴重泯滅
女性自我意識的泯滅在南戲的代表作品中是一個較為普遍的現象。從《琵琶記》來看,女性自我意識的泯滅是一個非常引人注意的問題,表現為身為女性卻自甘卑弱,缺少獨立人格,認同男性的人生價值觀,在男權的壓迫下,有些女性難以自我認同,“自覺”地變為客體,處于屈從地位,并對現實中歧視女性的做法毫無怨言,意識不到男女不平等的現實。這種自我意識的嚴重泯滅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1.女性容易屈服外界環境壓力
男權社會對于女性的要求是:女性為了實現自己的價值和被男性認可,她就必須放棄自我要求成為客體,這就是說,她就必須放棄成為主體的權利。在《琵琶記》中,在公公強迫新婚的丈夫去考取功名時,而趙五娘不愿丈夫離開自己,但她卻沒有爭辯,最后只能讓蔡公和張太公的“慫恿”成為現實。盡管趙五娘對外界環境壓力本能地進行了反抗,但趙五娘畢竟太弱小,她終于滑向了“他者”——“沒有或喪失了自我意識、處在他人或環境的支配下,完全處于客體地位、喪失了主觀人格的被異化了的人。”
2.女性缺乏自我抗爭精神,面對不幸只是忍受
在作品中,女性面對生活的一切困苦,往往無怨無悔,默默忍受,聽憑命運的安排,對男人的逃避責任決無怨言,也不思考痛苦的根源,無視男女不平等的現實,更不用說抗爭命運的大膽舉動了。《琵琶記》中的女主人公趙五娘積極認同并實踐著男人的人生理想,心中惟獨沒有屬于自己的喜怒哀樂,作者也是按照男人的標準來設計她的生活之路。“總之,在男性中心的宗法社會之內,女性生活處處受男性的操縱、壓迫、欺騙、藐視……而她們也有投降也有反抗;投降者被稱為‘貞女’‘良妻’,反抗者被罵為‘淫女’‘妒婦’;而最后,投降者只能忍辱茍延度日,反抗者到底只有一個失敗”。這樣看來,趙五娘就是“投降者”了,其生活的內容就是忍耐和等待。
3.女性對男性的依附性,主張為男性做自我犧牲
在封建社會中,文人對人生價值的認識與追求,更注重政治前途,在事業與愛情不可兼得時,往往更多地選擇事業。“在封建正統的觀念里,文人舉子的終極追求是著眼于德行的完備與事功的輝煌,‘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被稱為人生追求中的三不朽,這三不朽,都是統一在政治倫理中的,而人生的其他大事包括婚姻也當歸屬于此”。而她們巨大的自我犧牲換來的,不過是朝廷的旌表與“一夫二妻”的結局,這是當時女人真正的悲哀而不是榮耀。女性是男性話語的“傳聲筒”
幾千年來,無論東西方,女性一直被認為是“第二性”或“從屬他人的人”,喪失了自我主體性,其旨意也是參照男性來決定的。女性失去了自己的言語空間,成為男性話語的“傳聲筒”:所言是男人們常說的忠孝節義的話題,所為也是為了夫君的事業,以男人的是非為自己的是非,默默地襯托著他們的成功,而我們卻聽不到她們心底的真實的聲音。中國傳統文化中有“夫者妻之天”之說,意為女性為男性的附庸。
在作品中,趙五娘埋葬了公公婆婆,要更換衣裝前往長安尋取丈夫時,她儼然成了個滿口孝義的代言人。可見,趙五娘在男性話語占主導的社會中失去了表達自我意愿的話語權利,成了男性話語的代傳人。
二、中國封建思想男尊女卑觀念的影響
在“三從四德”“三綱五常”的束縛下,失去獨立的思想和意志。她們必須自甘卑弱,服從男人的意志,才能獲得這個以男子為中心社會的認可與尊重。反思造成女性自我意識嚴重泯滅的原因,應當與中國封建思想男尊女卑的觀念密切相關。
男尊女卑的觀念塑造了女性的依附性格,使女人不能作為獨立的個人而存在,更不用說做人的自由和尊嚴了。可想而知,女人在男權社會中生存下去是多么艱難。《琵琶記》中的趙五娘已接近死亡的邊緣,但她找不到痛苦的根源,只有忍耐煎熬下去,而最終九死一生的她,其結局不過是和牛小姐共同分享了丈夫的情感。“在古代中國兩性對立的社會模式中,一句‘唯女子與小人難養’的儒門古訓,便將男性居主的話語權勢昭示得明明白白,而女性則在這種異己的‘他者’話語強權下被赤裸裸地剝奪了與前者平起平坐的社會地位”“夫為妻綱”“出嫁從夫”的規定,已經賦予了男人對女人的絕對統治權,女性失去自我的悲劇一幕幕上演也就不足為奇了。
三、趙五娘悲劇命運的深層次分析
趙五娘的悲劇命運昭示著女性自我意識的嚴重泯滅。沒有愛情,可以苦等;遭受誤解,忍氣吞聲;生活困難,一肩承受;遭遇磨折,咬牙苦撐。然而,正是在苦難中顯現出她善良、無私、隱忍、堅韌等品質。讓人驚異的是,在那個豺狼當道的世道里,她一個弱女子居然能千里迢迢找到遠在京城的丈夫,這其間有多少辛酸曲折,恐怕是難以詳盡的。
作為一個女人,她首先應該是個人,然后才是女人,她可以成為女兒、朋友、妻子、情人、母親,等等。但趙五娘根本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人,她只是一個附屬物,只是封建男權制度下的一個符號化概念。她在作品中實際上是個對象性的存在,她的所作所為完全是“利他”“無己”的。趙五娘是男人心目中理想的女性,有著天使般的美麗和純潔,內斂、順從并且無私奉獻,她們回避著她們自己——或她們自身的舒適,或自我的愿望,甚或是兩者兼有之。女性在這里成了沒有自由意志的東西,沒有真實人的生活,只是一個美好但沒有生命的對象。
男女本來就是相依同生的,如同“吃糠”一出,趙五娘所唱“糠和米,本是相依倚”,但是在男權統治的社會中卻發生了分裂,“被簸揚作兩處飛”。所以,只有男女平等對話,和諧地生活,精神上合作的時候,才可能實現女性獨立自主的生活。如果女性沒有獨立自主的能力,女性就算是男人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也不過是個附屬品。
參考文獻:
\\[1\\]\\[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
\\[2\\]譚正璧.中國女性文學史話\\[M\\].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84.8.
\\[3\\]孫遜.中國古代小說與宗法思想\\[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12.
\\[4\\]李祥林.他者“話語權勢”中的女性失語——戲曲藝術與女性文化研究札記\\[J\\].四川戲劇,19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