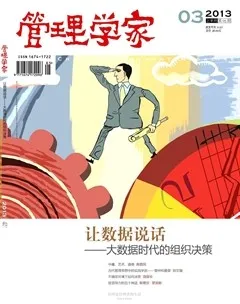靠什么打仗?
領導人在率領部下從事某種事業時,必須要回答一個基本問題:靠什么讓部下為你賣命?《曹劌論戰》有一段很精彩的對話。曹劌問魯莊公:“何以戰?”魯莊公回答了三條。第一條是衣食不敢獨自享受而分給別人;曹劌反駁道:“小惠未,民弗從也。”第二條是祭祀神靈一定誠實無欺;曹劌又反駁道:“小信未孚,神弗福也。”第三條最為關鍵,原文是“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此曹劌予以肯定,稱:“忠之屬也,可以一戰。”
也就是說,在曹劌眼里,惠、信、忠三者,小惠、小信都靠不住,只有忠才是支持作戰的因素。以物質條件惠及別人,肯定不是普惠,沒有得到恩惠的人不會追隨你;祭祀神靈守信,民眾不能受益,只是一種小信,也無法動員民眾;只有司法的公正,才能得到民意的支持,可以作為戰爭的依賴。問題是司法公正如何實現?曹劌贊賞魯莊公的,是“必以情”。但是,正是這個“情”字,當今多有誤解。
按照《說文》的解釋:“情,人之陰氣有欲者。從心,青聲。”作為對照,《說文》對“性”的解釋是:“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從心,生聲。”這種解釋顯然受到古代人性論和陰陽學說的影響,不足為據,但卻提醒人們,一定不能忽視“從心”。從漢字的造字原理看,凡是“從心”的漢字,都同心理有關,是一種主觀狀態。如果要解釋魯莊公這段話,可以這樣說:大大小小的各種案件,雖然不可能一一明察,卻一定要按照人情處理。這樣理解“情”,才能同“忠”對應起來。忠者,敬也,“盡心為忠”,都是心部。然而,當今的解釋中,往往用“實情”一詞,抹掉“情”的心理痕跡,或者干脆模糊處理,輕輕帶過。而“實情”一詞,在當今語境下,很容易把人們引向“事實”。把“必以情”變成“以事實為準繩”,乾坤大挪移就是這樣實現的。
也許有人會批評說,“情”正是司法公正的大害,對司法公正的破壞莫過于徇情枉法。但是,如果徇情而不枉法,還會有問題嗎?法度來自習俗,天理來自人情(宋儒把天理與人情的關系顛倒了)。如果法律不能反映出人情所向和人情所好,法律的意義何在?俗語中的“法不容情”的“情”是有條件的,即不容私情。包公的鍘刀,不容私情,卻要順應民情。把法和情完全對立,是對工具理性的僵化理解造成的。如果承認人類的情感具有某些共性,即所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那么,人情和法律實際上是可以協調的,而且應該協調。在某種意義上,“法不責眾”的困境,正是法律違背人情造成的。魯莊公也承認,各種案件不見得都能明察秋毫;但是,只要“必以情”,人們就不會失去對司法公正的期望,這才是關鍵。南京彭宇扶了老太太而被判罰的案件,有可能沒判錯(因為無法證明不是他撞倒的),但是,失了民情,堵塞了民眾的向善之道,其后果至今還在發酵。
所以,曹劌指出,實際支撐戰爭的動力因素除了利益,還有心理。然而,當今對《曹劌論戰》的解釋,往往抽去其中的心理因素,只談以民為本而不談司法公正。把“忠之屬”解釋為魯莊公忠于職守,還是解釋為建立君民之間的忠誠關系,都可以說得通。以“上思利民”把它解釋為忠于職守,似乎狹隘了些;但即便狹隘解釋,強調也的是心理。最關鍵的是,不能忽視司法中的“情”字。甚至需要強調,沒有通情,就不可能達理。對于今人來說,收拾人心,比物質財富更重要,起碼同等重要。當今有些案件的判決,有些政務的處理,有些經濟爭端的解決方式,有些公司的經營策略,不見得不合章法,但卻會失去人心,就是因為缺乏“必以情”的警誡。對于“情”的缺失程度,恐怕不能低估。這樣說,絲毫不否定法制的作用,而是希望實現法制與人情的一致。在簡化字中,當我們為了書寫方便把“”字的“心”去掉且用制度化方式推廣時,可能制度創立者也沒有意識到,這會使人們無意識地淡化愛心的心理一面,乃至于把愛變成物質滿足。孔子曾經批評把孝道僅僅看作養活老人的做法,說:“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于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論語·為政》)至今仍是必要的告誡。
作為管理者,一個最重要的能力就是權衡和排序。《曹劌論戰》強調“忠”,但并不能因此就把“惠”和“信”棄之不顧。不要看到“弗從”“弗福”,就斷言曹劌否定了二者。曹劌和魯莊公的不同,在于三個因素的排序。魯莊公的排序是物質、神靈、司法,而曹劌的排序把司法列在首位。這種排序差異,是因為兩人對這三種因素影響民心的權重判斷不同。《左傳》記載簡略,實際上,兩人應該有較多討論。假定魯莊公一口咬定“難道衣食不重要”?討論就無法進行,共識也無法達成。這可以說是這篇文章的弦外之音。
另外,《曹劌論戰》的重心,在于因“肉食者鄙”而引發的討論,而不在于長勺之戰的具體描述。曹劌以自己的見解,去校正魯莊公的認知偏差。當然,曹劌也不見得全正確,但由于他同魯莊公的思路和角度不同,所以能夠提供出有價值的觀點。然而,今人在讀《曹劌論戰》時,往往偏重于“齊人三鼓”和“一鼓作氣”的戰術分析,偏重于“視其轍亂,望其旗靡”的戰場觀察。這種偏好,同《曹劌論戰》的流行語境有關。作為《左傳》記載的一個案例,《曹劌論戰》的流行及其收入中學課本,是同毛澤東《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提到它緊密相關的,而毛澤東十六字方針中的“敵疲我打”直接源于此。認識到這一點,可以對如何看待傳統文化進行更深入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