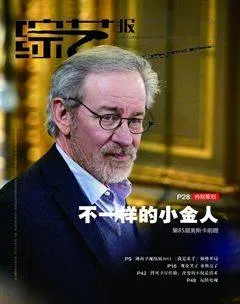漫長的質疑
徐江
詩人、作家、文化批評家
生于1967年
1989年畢業于北京師范大學
現居天津
沒有一種“趣味”敢拍著胸脯說自己代表了絕大多數,而春晚作為央視的最重磅文藝節目,恰恰又是一向“以服務于絕大多數為己任”的。這才是年復一年失望和質疑聲延續的最根本所在。
一年一度,媒體的娛樂版又到了發“天問”體標題的時間——自然是針對央視春節晚會。目前糾纏的話題是主持人、郭德綱師徒與趙家班。
三十年前,人們曾經多么喜歡春晚啊,如果那時有影碟機,我相信每家人都會把當年的春晚刻成光盤保留下來——電視節目單調的年代,春晚的豐富和喜慶,是人們一年的大餐、盛典。就像人們后來比喻的:它是另一種“餃子”“年夜飯”。
可是現在過年,誰家還只吃餃子或只吃年夜飯呢?恐怕有相當多的人,都已經記不起自己前年除夕吃了什么。但是他們照看央視的春晚。所以每年春晚,照例是會幫娛樂編輯們,省去不少找選題的時間:每年十二月、一月是對春晚籌備的猜想;每年一月底、二月是對春晚播出后效果的評論(大家自然愛看那些批評文字)。
其實從1990年代中期開始,春晚每年的反饋市場,一直是負面議論更受歡迎。一來觀眾欣賞口味日漸多元,屬于日益“吃過見過”的主兒了,不太滿足于“中檔偏下的時尚”層面(內地娛樂產品當時確屬這個平均水準)。二來藝人的舞臺日漸多元,央視雖貴為國家電視臺,恐怕也很難在除夕那一刻壟斷所有一線的藝人資源。三是觀眾在用“國家隊”的規格要求春晚,主辦者也在用“國家隊”的莊重自我定位,彼此都少了一點放松:在宏觀上大家都忘了這僅僅是一臺節目,就它所能提供的服務而論,并未見得就能比香港TVB、亞視之類的春節晚會豐富;具體表現就是過審節目偏于拘謹、說教,是中老年人理解的時尚,暮氣重。
就近年的春晚表現而論,2008年之后的幾屆晚會,都在一定程度上,品質好于1990年代的許多晚會。尤其是在服裝、舞美、鏡頭調度等技術環節。舞蹈類節目的現代感也正在跟上潮流。語言類節目大家雖然一直熱捧趙本山,但像黃宏、蔡明、郭達這些藝人的表現同樣很出色。春晚的節目質疑可能更多是相聲類節目的式微,時尚歌曲的空間太少、同時又不能像1980年代那樣在自己的平臺推出新的流行曲目,另外也缺乏強勢的魅力主持人。在商業不發達的年代,人們見明星難,見群星薈萃的表演難,所以新鮮感強烈;而今天連買藥廣告都被明星占滿了——哦,原來明星們也補腎、也鬧婦科病!誰還會一直保有那份好奇感?何況時尚和趣味也都在無限碎片化,沒有一種“趣味”敢拍著胸脯說自己代表了絕大多數,而春晚作為央視的最重磅文藝節目,恰恰又是一向“以服務于絕大多數為己任”的。這種接受趣味與生產意愿間的錯位,才是年復一年失望和質疑聲延續的最根本所在。對于社會而言,這正表明了內地的進步;對于晚會生產者而言,“眾口難調”也正說明了這個行業的制作難度在增加。
接下來的問題或許僅僅是——
1、 觀眾愿不愿意把春晚只回歸于一臺普通的晚會來看待?
2、 既然眾口難調,春晚的決策群與高管敢不敢順應時代,搞審美分流,將春晚“化整為零”,針對不同收視年齡段和群體,打造不同的除夕晚會,以維系自己在晚會市場的優勢?或是繼續在保持綜合性的同時,勇于舍棄掉它原先兼容的一些功能,突顯出更純粹的娛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