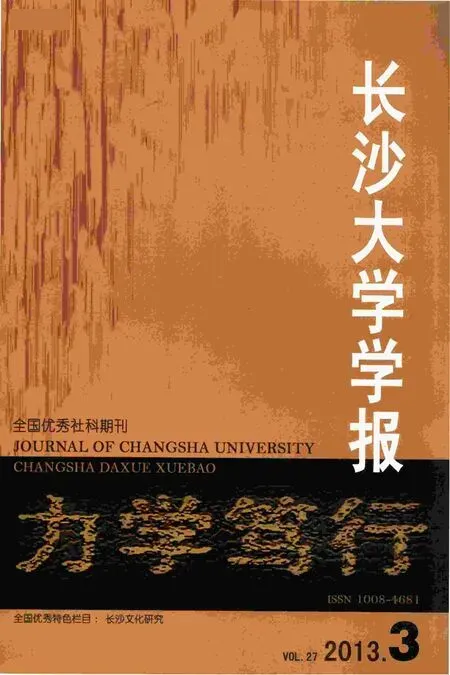論“調富”稅制結構的失衡與優化
詹 博
(湖南第一師范學院經濟管理系,湖南長沙410205)
收入分配差距的擴大迫切需要加以調節,稅收是調節收入分配的重要手段。然而,我國現有稅制下,稅收不但沒有縮小收入分配差距,反而存在逆向調節。稅收調節收入分配的失靈,源于稅制結構的失衡。要縮小收入分配差距,必須盡快完善稅制結構。
一 “調富”稅制結構的失衡
稅制結構是指構成稅制的各稅種的分布狀況及相互之間的比重關系。1994年分稅制改革以來,我國的稅制結構在不斷優化,然而從經濟社會發展特別是從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的需要來看,還存在諸多的結構失衡。
(一)直接稅與間接稅的失衡
構建流轉稅和所得稅“雙主體”的稅制結構模式,是我國稅制改革的目標。從稅制改革實踐來看,1994年后直接稅(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財產稅等)的比重在增大,間接稅(增值稅、營業稅、消費稅、關稅等)的比重在縮小。從表1可知,1994年我國間接稅比重為76.4%,直接稅比重為23.6%,2011年間接稅比重為 68.6%,直接稅比重為31.4%,2011年與 1994年相比,稅制結構在優化[1]。西方國家的間接稅與直接稅比重為 1∶2.1,發展中國家為1.5∶1。然而,我國間接稅或流轉稅占我國稅收總額的比重仍然畸高,而直接稅或所得稅比重偏低。2011年,流轉稅占稅收總額的比重高達67.9%,所得稅占比25.4%,二者之間的比值為2.67∶1;間接稅占 68.6%,直接稅為 31.4%,二者之間的比值為 2.18∶1[2]。以間接稅為主體稅種的稅制,難以有效調節收入分配差距。

表1 中國的直接稅和間接稅
(二)個人所得稅與企業所得稅的失衡
發達國家個人所得稅收入占全部稅收收入的比重一般在40%左右,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為8%,而我國個人所得稅在整個稅收體系乃至所得稅體系中所占比重過低。從圖1和表2可知,個稅占所得稅總額比重最高的2002-2003年也只有32%,大多數年份低于30%[3]。2011年個稅占稅收總額比重為6.87%,占所得稅總額比重為24.99%。我國現階段的個稅比重低,加之納稅人收入監管體系的缺失,個稅對高收入的調節力度還很不夠,甚至存在逆向調節。

圖1 所得稅結構圖
(三)收入流量稅與收入存量稅的失衡
現行稅制雖有調節收入流量的個人所得稅,但調節收入存量的財產稅制很不完善。一是現有的房產稅、利息稅不合理。房產、金融資產和土地是我國居民最主要的財產,三項合計占居民財產總額的89.02%,其中房產和金融資產兩項合計占財產總額的79.67%[4]。在房地產方面,對城鎮居民用于營業的房產征稅,而對城鄉居民個人擁有的非營業性的房產免稅;在金融資產方面,僅有儲蓄存款利息稅,而其他金融資產幾乎處于無稅狀態。2006至2010年間財產保有環節的稅收比重不足5%,在稅收收入體系中微不足道。如2011年房產稅收入僅1102.36 億元,只占稅收總額的 1.2%[5]。二是遺產稅與贈與稅缺失。西方國家普遍實行了對居民財產有顯著調節作用的遺產稅制,而我國雖在1994年就將遺產稅列入改革計劃,1996年納入“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然而至今仍未出臺。
(四)勞動收入稅與非勞動收入稅的失衡
二戰以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勞動收入份額普遍經歷了一個上升過程。如美國1952年的勞動收入份額是61%,70年代末上升到了68%,之后略有下降,但一直都維持在65%左右[6]。我國勞動收入在GDP、國民收入和居民收入中的份額都在下降,且比重較低。李稻葵等利用省份收入法GDP數據,計算發現中國勞動收入份額從1990年的53%下降到2006年的40%左右[7]。在國民收入中,勞動收入比重較低,然而勞動收入特別是工薪所得卻承擔了較多的稅收。從表2可知,2008-2011年我國工薪所得稅占個稅比重都在60%以上,其他類所得的比重不到40%。

表2 2008-2011年中國所得稅
二 “調富”稅制結構的優化
稅收是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手段。要發揮稅收的“調富”作用,必須推進稅制改革,優化“調富”稅制結構。
(一)優化直接稅與間接稅結構
一般來說,不能轉嫁的是直接稅,而可以轉嫁的是間接稅,從調節收入分配的作用來看直接稅明顯優于間接稅。世界上主要發達國家都是以直接稅為主的國家,OECD國家的直接稅占總稅收收入的比重都超過60%,平均超過70%[8]。要構建“調富”稅制,按照以直接稅為主體稅種的稅制取向優化稅制結構,增加直接稅,減少間接稅。當然,減少間接稅,并不是絕對減稅,而是相對減稅,也不是總量減稅,而是結構減稅。我國現階段,在流轉稅環節進行結構性減稅,必須減輕中低收入者所負擔的增值稅和消費稅。據有關研究,我國最低收入者的增值稅有效稅率是15.11%,接近法定稅率17%,而最高收入者的增值稅有效稅率卻只有8.1%。世界上許多國家規定增值稅對生活必需品實行免稅或優惠稅率,我國雖將增值稅低稅率定為13%,但遠高于歐盟5%-10%的稅率[9]。要發揮增值稅和消費稅的“調富”作用,應考慮對基本生活必需品采取免稅,對一般生活消費品征低稅,而對奢侈品、高檔消費品及高檔消費場所消費行為等征收重稅。
(二)優化個人所得稅與企業所得稅結構
在流轉稅減稅的同時,必須增加所得稅。在所得稅絕對量和相對量增加的同時,必須優化所得稅結構,即減少企業所得稅比重,增加個人所得稅比重。企業所得稅要實現調節收入分配功能,關鍵是減少“小微企業”的所得稅負擔。“小微企業”往往具有創業性、勞動密集性,對勞動力就業意義重大。政府應對“小微企業”給予所得稅優惠減免。個人所得稅要實現調節收入分配功能,關鍵是增加高收入者的個人所得稅。為此,必須完善個人所得稅制。一是稅制模式上,消除分類所得稅模式下低收入者相對稅負重而高收入者稅負重的缺陷,采取綜合和分類相結合的個稅模式。二是免征額確定上,費用扣除應考慮家庭負擔差異、地區基本生活水平差異,并結合CPI的變動而聯動調整。三是稅率設計上,應采取超額累進稅率。四是個稅征管上,應加強征管力度。
(三)優化收入流量稅與收入存量稅結構
居民收入用于消費之外的節余,轉化為存量即財產。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居民財產隨著收入的增加而迅速累積,同時財產差距也在不斷擴大。據中國統計局信息網資料,家庭財產總額占全部居民財產總額的比例,最低收入10%的家庭為1.4%,而最高收入10%的富裕家庭為45%,另外80%的家庭為53.6%,中國家庭資產相差倍數大于美國(104.5倍)達254.5倍[10]。財產差距如不加以調節,必定會惡化收入差距,并產生代際傳遞。因此,政府必須通過財產稅來“調富”。一是完善房產稅。將居民住房納入房產稅范疇,對首套住房或人均居住面積在規定限額以下的住房免稅,其他住房以評估價值為依據累加按超額累進稅率征稅。二要完善利息稅。利息稅以居民利息收益合計值為課稅依據,設計一定的免征額,采用超額累進稅率計征。三要開征特殊財產稅。對金銀、珠寶、文物、古董、字畫等藝術品和收藏品征收特殊財產稅。四要開征遺產稅與贈與稅。遺產與贈與稅的設計應該是使征收對象控制在極少數富人為宜,采取超額累進稅率的總遺產稅制模式。
(四)優化勞動收入稅與非勞動收入稅結構
要改變現行稅制下勞動收入實際稅負重而非勞動收入實際稅負輕的不公平狀態,必須重點抓兩方面。一方面,完善稅制。從現行的個人所得稅的11個稅目看,大量所得采用的是比例稅率,采用累進稅率的僅有3個即工資薪金所得、個體工商戶的生產經營所得和對企事業單位的承包經營、承租經營所得。比例稅率盡管具有計算簡便、便于征管的優點,但它有悖于量能納稅原則,且具有累退性質,不利于調節收入分配。因此,非勞動收入也應綜合后按超額累進稅率計征。另一方面,加強征管。一般來說,勞動收入特別是工薪收入是中低收入者主要甚至唯一的收入來源,而高收入者的收入主要來源于非勞動收入。非勞動收入具有多元性、隱蔽性,加之現有收入監控機制缺陷,致使非勞動收入稅收征收不足,存在較為嚴重的偷逃稅現象。據有關專家估算,富人應繳納的個人所得稅應在8000億元以上,是目前個人所得稅額的2倍多[11]。加強征管,必須加大對偷逃稅的懲罰力度,但關鍵在完善監管機制,在全國范圍內普遍采用納稅人永久單一稅號制度、收入支付方強制性預扣稅款制度、收入與財產實名制度、全國聯網與信息共享制度等,使稅收真正起到“調富”作用。
[1]劉佐.中國直接稅與間接稅比重變化趨勢研究[J].財貿經濟,2010,(7).
[2]安體富,劉翔.促進居民收入合理分配的稅收政策建議[N].中國稅務報,2011-09-07.
[3]郭健.中國稅制結構的累進性評價[J].山東經濟,2011,(6).
[4]趙人偉.我國居民收入分配和財產分布問題分析[J].當代財經,2007,(7).
[5]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課題組.影響收入分配關系的五個問題與八點建議[J].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2,(2).
[6]解決分配問題應注重勞動收入份額提升[EB/OL].http://news.xinhuanet.com/observation/2010-10/21/c_12684942.htm,2010-10-21.
[7]李稻葵,劉霖林,王紅領.GDP中勞動份額演變的U型規律[J].經濟研究,2009,(1).
[8]楊巨.國外稅收結構的收入分配效應研究新進展[J].蘭州學刊,2012,(2).
[9]劉怡,聶海峰.間接稅負擔對收入分配的影響分析[J].經濟研究,2004,(5).
[10]彭騰.論我國的遺產稅缺失[J].蘭州商學院學報,2010,(3).
[11]安體富.完善個人收入監控機制勢在必行[N].中國證券報,2011-0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