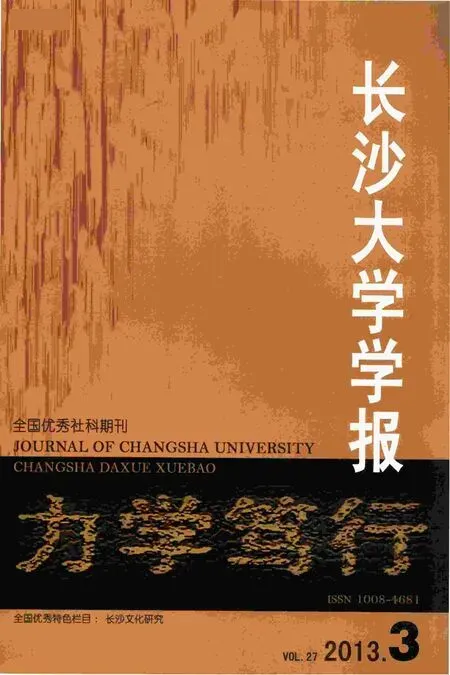舊縣村鄉村旅游紀念品的可持續開發
彭琬琰
(廣東商學院藝術學院,廣東廣州510320)
出于鄉村可持續旅游紀念品開發課題研究的需要,筆者在廣西桂林陽朔舊縣村進行了三次田野考察,對舊縣村現存的傳統工藝、傳統手工藝人的生活狀況以及他們自發的鄉土工藝旅游化實踐進行了深入的調查,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不同于傳統的設計策略和設計思路。
一 舊縣村的鄉村旅游開發
(一)舊縣村鄉村旅游開發的條件
舊縣村位于遇龍河中游,陽朔縣城上游。全村現有人口1100人。村民平均年收入在2萬元左右。當地主要栽種水稻,一年二到三熟;除水稻外,也有一些果樹栽種和養殖業。村民生產規模很小,基本上自給自足,農業收入是他們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村民收入的另一來源是外出打工。由于中青年大多外出打工,留在當地的多是老人、小孩與婦女,社區呈現空心化現象。
舊縣村具有獨特旅游優勢。除了其喀斯特地貌的群山與水田交相輝映,以及遇龍河沿線山水風光外,座落在村邊有著880余年歷史的宋代石拱橋——仙佳橋、明末清初遺留的黎氏老屋等建筑群及一些散落的土夯農舍也深受旅游者喜愛。旅游黃金時間為每年的4月到10月,旅游形式主要有自行車自助游、跟團游、鄉民開車出外接客游覽;游人活動主要是在農家飯店吃飯,參觀古民居,觀賞當地自然風光以及在遇龍河漂流;偶爾也會有生活在喧囂都市的中外游客為了享受鄉村寧靜生活在村中作短暫逗留,食宿于當地的農家。村民參與旅游業的方式主要有做導游、生產并出售手工藝品或土特產、開飯館、古建筑拍照收費等。除飯店和導游外,村民參與旅游業程度非常淺。這部分收入占總收入的比例不足4%。
(二)舊縣村鄉村旅游開發的現狀和前景
按照陽朔縣政府制訂的遇龍河旅游規劃,舊縣村的住宿床位到2010年要新增5至6個家庭旅館,共有床位75張。而直到目前,舊縣村僅有2家旅館,共20張床位,遠遠沒有達到規劃預期。根據陽朔縣政府的統計數據,舊縣村游客瞬時容量為44人,每天周轉4批次,日容量達176人,這個數據估計還在擴大。但總的來說,舊縣村旅游業并沒有按預期發展。這與舊縣村在遇龍河旅游中的地位有很大關系。據觀察,來舊縣村的游人活動主要是吃飯和參觀古民居,停留時間不超過2小時;散客更多的是騎車路過而已。因此,受益的只有飯店,而其他村民獲利可能性很少。要改變現狀除完善交通條件外,更重要的是要改變舊縣村的旅游方式,使游人活動不局限于參觀,更多的是體驗式的旅游。
舊縣村及周邊曾經迎來過好幾撥的外來旅游投資者,其中耗時最長,規劃最大的還是法國人Frederic Coustols及其DAST基金歷時四年的舊縣花園村可持續旅游開發項目。這個項目包括針對短期觀光游客的民居修復與重建,以及農村草藥園的興建;針對長期休閑游客的藝術工作坊、七日游文化周等學習型旅游項目規劃。項目投資人的開發思維十分開放,邀請了大批來自中國院校的師生參與規劃,還邀請了一批海外藝術家參與村中地面景觀的藝術創作。該項目秉承的是可持續原則,希望旅游開發與當地社區形成良好的互動關系。但因溝通不良,官方審批困難等原因,投資人在2010年圣誕節前后一去不返。雖然整個項目沒有最終落實,但卻留下了相當一部分地面建筑和景觀,以及外來投資者與鄉土手藝人合作的成功案例。
隨著外來投資增多和宣傳的加強,舊縣旅游者呈逐年增多趨勢。筆者在第三次到舊縣村做田野考察時,獲聞政府將投資2億元開發從舊縣到觀橋段的遇龍河景區;位于遇龍河中游的舊縣村正好作為景區規劃的起點被納入到開發項目當中。面對大規模的開發進程,舊縣村旅游及他們的鄉土工藝的走向應該是很有前景的。
二 舊縣村鄉土工藝現狀及旅游商品化實踐
(一)傳統鄉土工藝現狀
編織:村中現在最常見的是婦女針對旅游市場編織的麻繩草鞋。原料來自種在農舍前后的黃麻,經過摘料、剖料、風干等工序搓成麻線,配用彩色絨毛線。麻、草等當地原料均沒有使用漂染技術,而是以麻繩為芯纏繞有色的碎布或絨線形成原色麻中間隔或裝飾的彩色肌理,這種鄉土間傳統的處理方式極為智慧地達到了裝飾趣味與生態可持續的平衡。
木工:村中木匠主要有黎師傅和毛師傅。黎師傅看不懂現代家裝的圖紙,但手藝不錯,悟性很高,給他看類似范本就能照著打出來。村中的主要木工還是門窗等建筑構件,針對游人的木工旅游工藝開發品基本上沒有。
篾工:受遇龍河漁業影響,舊縣村最有特色的竹編制品為魚蝦籠等捕魚用具;內墊竹葉的斗笠也是此地的特色竹編。另外還有圈養家禽的各種農家雞籠,編法稀疏,以橫向竹箍的松緊造型,為極具鄉土特色的籠編法。竹編主要使用毛竹或長壽竹;其中長壽竹質地堅硬,適合編織戶外用品;而毛竹則由于植株更粗大,且更加柔韌,適合于編制竹椅、竹床等竹制品。
此外村中還有以本地產出的沙田柚、筍衣等自然材料進行簡易加工的傳統,因而使鄉民自主的旅游工藝品開發有了一定的工藝基礎。
(二)舊縣村鄉土工藝旅游商品化實踐
對村中手工藝人參與鄉土工藝的旅游商品化開發的努力,筆者展開了一系列的調查。下面介紹的三個手工藝人以及他們的旅游工藝品具有較突出的代表性。
毛家的筍衣扇。手藝人:毛師傅,62歲。將筍皮剝落后用石板壓制成平板,而后綁上竹棍可直接用來扇風。毛師傅自繪了舊縣地圖,并畫在自制的筍衣扇上,在村中或到陽朔西街兜售,每個扇子5-7元。
黎大叔的魚骨煙管。手藝人:黎師傅,74歲。黎大叔將魚骨剔肉后曬干,用細竹管將其串連起來粘結成管;利用廢棄冰箱中的銅管粘結于魚骨管上作為煙嘴;再將小竹根或者曬干的小柚子掏空打洞,制作成為裝煙絲的煙袋。整個煙管的成本為20元至30元不等,銷售價格則為50元至70元。
龍師傅的竹篾編織。手藝人:龍師傅,67歲。龍師傅在旅游開發初期,就編織魚蝦籠售賣,但收入并不樂觀。直到旅游投資人F的到來(即Frederic Coustols),他的竹編手藝才得以發揮。F邀請他參與到名為“大地藝術”(land art)的地面景觀群項目開發中。他們合作的第一個試驗作品名為“大蘋果”。這是村中第一座由旅游投資者與本地工匠合作的竹制地面景觀。“大地藝術”系列現代景觀項目試圖營造具有現代藝術氣息的人文景觀以吸引年輕旅游者,而本地工藝人的參與則同時具有人文、社會和藝術試驗等多層內涵,也讓項目成為鄉土工藝人參與旅游開發的成功案例。
(三)舊縣村鄉土手工藝生存空間狹窄的原因分析
雖然村中手藝人以及外來投資者有將傳統手工藝旅游商品化開發的努力與實踐,鄉土手工藝在村中的生存空間還是越來越狹窄。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老手藝人相繼去世,鄉土工藝缺乏年輕的后繼者。如同中國大部分農村現狀一樣,舊縣村的年輕人大多外出打工,村中留下的主要是老人、婦女和兒童。在采訪中接觸到的手工藝人平均年齡超過65歲,其身體已無法支撐工藝生產。除黎木匠大兒子繼承其父手藝,在外承接木工活外,很少有年輕人學習鄉土手藝,更不安心在本土從事這種手工藝。
第二,鄉村個體經營模式逐步為工業化的大型作坊所取代,個體手藝人在商品市場環境中幾乎喪失了競爭力。那些鄰近村鎮竹制工藝廠的產品,無論是機械化加工工藝,還是批發銷售環節,都有鄉土民間手藝人所不能企及的效率及成本優勢。以自然竹材加工成編織用材的過程為例:一個篾匠即使工具齊全,要手工處理相對精細工藝的竹篾的時間往往是編織時間的一半,加工80根長1米寬2毫米的竹篾,需要半天的工時。而大型竹編作坊或竹工藝廠使用破篾機,一根竹子即刻能破為多瓣,長度、篾寬都可隨意調整;除了破篾機,還有織篾機等更多減少人工成本的大型機械設施。因此,村中篾匠基本已經不再進行篾編生產。
第三,鄉土手工藝人對旅游工藝品的開發能力和對游客審美情趣的把握能力較弱,且缺乏主動創新的動力。很多工藝品幾十年如一日,或者依然保留過去農用器具的形制,只是在工藝上更精細一些而已。這只能形成一種偶然性的旅游工藝品消費,而不能形成對消費者的必然性吸引因素。而制作筍衣扇的毛師傅,一直堅信畫了地圖的筍衣扇才有更好的銷售市場,因此花了大量人工在扇面的地圖繪制上,而對扇面、扇柄的處理上卻十分粗糙。繪制并不精致且缺乏美感而又指向功能不明的自繪地圖是否是筍衣扇銷售的主要驅動力,是值得商榷的。
三 舊縣村旅游工藝品開發合作伙伴及設計策略
(一)開發合作伙伴及其開發理念
來自南非的投資人Ian hamlinton,中文名為鷹,和英國朋友合作投資開發舊縣的旅游服務設施。一期工程是名為“神秘花園”(SECRET GARDEN)的鄉村旅館。鷹曾經作為法國人F的助手參與過舊縣花園村的開發項目,在開發中也一直秉承環境可持續、地方工藝參與、社區民眾受益等開發理念。他與舊縣村民簽訂15年到20年的合同租下村中的黎氏老屋,通過外部復原性修繕,以及內部現代化設施改造,將老屋改造成可以接納游客的鄉村旅館和藝術品展覽沙龍。旅館的主要定位是接待外國游客及都市白領,住宿的消費檔次高于村中60元一晚的房間3至4倍。
(二)定制模式的設計策略
針對鄉村個體工藝人缺乏創新能力和動力、其產品缺乏競爭優勢的現狀,筆者與鷹合作設計出一套采用本地材質和工藝,但又具有現代審美情趣的旅館用品及裝飾配置,通過定制模式讓村中的鄉土藝人為旅館加工制作這批用品和裝置。旅館既向外來游客展示、同時也銷售本土工藝品。游客在旅館使用這些工藝品的過程,也是對其欣賞把玩的過程。這在一定程度上激發他們對于本土工藝的消費熱情,并能通過旅館提供的平臺消費這些旅館用品,或者通過旅館的渠道定制具有個性特征的工藝品。定制模式保證了工藝品的質量,而旅館定位的高消費人群為本土手工藝者及旅館經營者都帶來了盈利的可能。在為本土工藝者提供展現平臺的同時,投資者也將本地鄉土手工藝納入旅館的地域特色中,讓游客在旅館的消費過程中有更多體驗,旅館品牌也因此賦予更多人文價值。
而基于投資者藝術品展覽沙龍的建設項目,可以沿用之前法國人F在“大地藝術”項目中藝術家與鄉土手工藝人合作創作的模式,組織發起一系列的藝術家“在地”藝術創作。這方面的創作作品相對大地“藝術”的景觀搭建,更多的考慮沙龍和旅館的室內空間特征,即可作為展示品增加沙龍及旅館的藝術氛圍,又可作為不可復制的地域性藝術創作高價銷售給入住的游客。
在提供展示平臺的同時有效地宣傳自身這一特色,旅館在其網頁上將手工藝作為一個特色板塊進行介紹。這不光為瀏覽者介紹旅館采用本地工藝特別設計的相關用品,也附帶介紹本地的工藝及制作者,展示社區工藝者和旅館形成的長期合作關系,并惠及旅館的品牌宣傳。(見圖1)

圖1 包含工藝品及鄉土手工藝人介紹的鄉村旅店宣傳網頁
這種合作關系還體現在用品的銷售標簽上。消費者如果在旅館中消費了相關的鄉土工藝用品,標簽上將同時蓋有旅館及工藝者的印戳。這種標簽系統旨在同時強調商品所含的開發者品牌價值及工藝者手工價值,以區別市面上其他大工業生產的旅游工藝品。(見圖2)

圖2 兼具酒店與手工藝人標識的旅游工藝品標簽
四 舊縣村旅游工藝品設計方案
(一)設計主題
設計以酒店的名字“神秘花園”為主題,試圖營造出一種鄉村花園情景的高情感使用體驗;產品使用的語言符號不完全來自現實農村,其中使用鳥語花香及音樂等主題進行工藝品外觀及使用方式的創新,更貼近現代都市人對鄉村的理想追求。
將吊燈設計成鳥窩的造型,取材自西方對于葫蘆的鳥窩運用方式。將鳥的原形符號化平面化作為情境提示融入產品。(見圖3)籠中鳥作為一種程式化的語言以一種反差的方式運用在“花籠”這一盆栽設計中,設計為滿足爬藤類植物生長的盆景裝置,在爬藤植物攀爬生長所需的支架上運用鳥籠的造型語言及工藝,鳥的意象在籠之外,通過這一置換產生的反差感正是設計情趣所在。(見圖4)

圖3 取材葫蘆鳥窩的吊燈

圖4 “花籠”盆栽
將沙錘的形態運用到鹽瓶和胡椒瓶設計中,情趣化運用不僅僅在外觀形式層面,也通過使用者由外觀產生的聯想暗示產品的使用方式。從而在產品實現使用功能的同時提供情趣化的使用體驗。設計更切合現代人審美,使用傳統的鄉土工藝制作的西式早餐用品在體現鄉間風情的同時,又避免了一般鄉土農具呈現的粗糙感,從而讓產品無論是功能還是形式都具有了從“在地”的鄉村旅館的使用環境延伸到“異地”都市居家環境的可能,從而增加外地游客對這些工藝品的消費機率。
(二)設計材料與工藝
設計中大量采用葫蘆、竹、筍衣、竹衣、麻、藤等本地材料。葫蘆主要使用切割工藝。作為一種富有有機曲線的天然型材,傳統葫蘆處理的平直切法并不足以讓其曲面的豐富性和趣味性得到展現,設計采用了配合曲面的各種曲線切割,所得造型即是后天挖掘,這種曲線切割方式也基本杜絕了大工業生產的模仿復制。
對村中已有的筍衣扇子進行一定的改良。使用具有弧度的竹片,與切割好的筍衣扇在連接處以包裹的方式結合,以麻繩固定。去掉過去的地圖繪制,保留扇面的單純性及完整性,以突顯筍衣材料獨特肌理效果的魅力。還根據筍衣材料單向彎曲的物理特征進行了一些其他領域的運用創新,發展出相關的杯套等用品。
方案使用的竹編工藝方式保留了當地傳統的籠編技法,但改變傳統的編織形式,與葫蘆光滑的曲面相結合,造成一定的表面材質對比;同時針對不同編織技法的表面肌理,以及不同篾寬帶來的疏密效果的呈現,進行了試驗與討論,從而得到啟發性的試驗結果。
(三)與鄉土手工藝人合作過程
在與當地鄉土手工藝人合作制作的過程中,主要合作的工匠龍師傅最初并沒有理解定制模式下精致工藝及藝術化造型的需求,即使在已經提出篾寬、密度、織法等要求后,依然期許使用最容易達成的工藝方式和竹篾尺寸進行加工;再加上從未接觸過的外觀造型,哪怕使用慣用的籠編織法也需要反復的試驗和推敲,得出產品效果不符合要求的多次返工應予以理解,并計入設計開發的加工計劃內。在一款魚型果籃的編織過程中,手工藝人在已經做出一件產品后主動提出更合形態要求的紋理重新編織,對比一開始對于修改意見和返工要求的不耐煩,讓筆者感受到了工匠在與設計師磨合過程中加工觀念的轉變。而相對當地并不高的生活消費水平,這類旅游工藝品創作所可能帶來的盈利也激發了手工藝人的創作熱情。而在龍師傅的竹編加工期間,不斷有游客停駐龍師傅的店外觀看織篾過程,也有游客詢問編織出來的成品在哪里購買。可見,鄉土工藝并不缺乏旅游商品化開發的空間。